在这章里埋了个小彩蛋。提示是:看到奇怪的东西可以查一下。
找到的人可以通过全网任何sns告诉我!评论区或私信什么的(这个评论区也行)。
奖品是会画个签绘赠送,可以拿去印任何想印的谷和纸片。
「進藤光就是sai」。
倉田厚想起前幾天登上2ch的時候,刷到這樣一個匿名討論串,幾小時內聚集了不少人,連外國人都有。
「sai的賬號昨晚登錄過!」
「可只顯示在線了幾秒鐘。」
「想都知道是他發現之後才點了隱身吧?」
「回來了(我是之前那個學信息工程的)。我查到昨晚sai上網的IP地址在名古屋東區橦木町。」
「那不就是中部棋院?」
「真的假的,那他豈不很可能就是某個職業棋手。」
「喂喂,他會不會其實一直在線,只是隱身了啊?」
「是真的,我也從源代碼查到IP地址了。1.15.86.194。確實就在中部棋院附近。」
「我記得『幽玄之間』四年前的版本更新就加入了隱身和好友功能。」
「這幾天都有誰在中部啊?」
「好像參加富士通盃最終予選的棋手有一部分在那邊?」
「啊,是這樣!進藤本因坊和社九段的對局就是在昨天嘛。」
「這麼強又是秀策流,只能是進藤了吧!畢竟社九段的棋風和sai完全不像。」
「旁友萌,這也就是說⋯⋯?」
「進藤光就是sai吧!」
「What’s happening? Ur talking about sai? :-O」
「Yes. Hikaru Shindou might be sai!! ఠ_ఠ」
「這樣下結論也太草率了。」
「For real? That’s huge! /o\ How did you guys know?」
「其實還有別的證據。有人記得八年前進藤和塔矢行洋大師在新初段聯賽那局嗎?」
「你想說那局是sai下的?怎麼可能,進藤就坐在那裡欸。」
「This translation is crap. Anyone bothers explaining to us?」
「但有幾手明顯就是sai的風格。如果他們是同一個人,不就說得通了?」
「不敢輕易認同『進藤光就是sai』的觀點,但不可否認那局確實很像。」
「Which game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re five here so, please? :-(((((」
「真的。重要的是,那也不像進藤本因坊自己的風格,尤其是開局。」
「正好有那局的錄影帶(我是內部的人[1]),剛重看了下,他第一手就花了二十分鐘來著,記得當年入座的時候也等了好久。不知道有沒有關係,就是覺得很奇怪。有沒有人來一起討論下啊⋯⋯」
出於好奇看了兩眼支持者的發言,結果無非是些主觀臆斷的言論,唯一的事實就是IP地址接近而已。倉田厚關掉了瀏覽器的窗口。
在平成十一年的七月,網名為「sai」的神秘棋手突然出現。一開始和外國人對弈,很快便改為只找日本的網友,但那幾局已經足以引起各國棋手的關注。這是一年後到世界業餘圍棋錦標賽的會場參觀時,聽中國的李臨新說的。
「結束自己的對局後,我觀察了幾乎所有人的棋。現場的選手都不是sai,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他。」
sai不是日本的職業棋手,中國和韓國棋院也沒有人認識他,更沒有人見過他本人。
「森下九段的弟子說跟sai在網上聊過天,推測sai可能是小孩子,還說sai就像是本因坊秀策學了現代的定石。」李臨新笑道:「最後都要演變成討論sai身分的研究會了。」
最後一次在「幽玄之間」見到sai,是平成十三年[2]四月二十一日和塔矢行洋的對局。塔矢名人當時還在醫院,沒有人知道這局棋的約定到底是如何達成的。結局是行洋以半目之差輸給sai,之後宣布引退。而sai再也沒有出現。
那之後,網上又有過幾個假冒的sai,但都下得不怎麼樣,毫無說服力。
和所有想窮極神之一手的人一樣,在看過和塔矢行洋的那局棋譜之後,倉田也想和sai本尊對弈一次。
但不知為何,總覺得sai不會再復出了。
也是僅憑直覺這麼認為而已。
只是沒想到不止棋迷之間,連棋院裡都在傳這個謠言。
甚至桑原老師也在談論這件事——
「緒方君,」老人家站在緒方旁邊,也不看他,幽幽地說,「進藤小子這些天也不來了,真怪啊?」
緒方沒有回答。
「剛才聽他們聊起,好像網路上都在講喔,『進藤就是sai』的傳言。」
咬了一口手裡的總匯三明治,一邊嚼嚼嚼,一邊豎起耳朵。半晌,只聽見「咔」一聲。
轉頭一看,男人把手裡的菸盒都捏皺了——那個向來對物品的整潔程度過分苛求的緒方。
「嘻、嘻、嘻。」桑原大笑起來,「老身是不清楚。不過少了這兩個年輕人,圍棋大會這樣的活動也就無聊了不少啊,是不是?」
這麼說來,的確有段時間沒見到進藤了。塔矢請了個長假;還沒好好祝賀他成為名人呢。他倆都不在,今天又是棋院年初第一次面向公眾的圍棋大會,就難得請來一些資歷更老的棋手。
——不過能同時見到桑原仁、緒方精次和我倉田厚,也算是超值了吧,這次來的人!
「啊!是倉田老師,您也在啊!請幫我簽名可以嗎?」
「當然,當然!」暫且放下手裡的瑪芬,接過扇子,拿起桌上的油性筆,「我看看啊⋯⋯那就寫個『即將成為五冠王 倉田厚』吧!」
「老師,我的簽名板也請⋯⋯」
「想要的人在這邊排隊喔,大家都有~」
真好啊,冷餐會上被粉絲包圍著要簽名什麼的。
說來,進藤也是個奇怪的人。不單單是指罕見的不想要自己簽名這件事。
「⋯⋯因為是我說的,所以我非常確定!」
對本因坊秀策的字跡做出過分自信的鑑定,還為了假簽名逆轉了高段棋手御器曾,贏下了對局。他的執念遠不止普通的「秀策迷」那麼簡單。
sai、進藤、秀策。
sai和進藤的下法確實都是脫胎於秀策流沒錯。再加上那個賬號在進藤逗留的地點登錄、上線後又很快隱身的舉動,憑這些,有人推斷出了「進藤就是sai」的結論。
雖然這個指認本身也有夠離譜就是——算算時間,sai出現的時候進藤還是個小孩吧?連我倉田厚的大名都不知道。
初次對局的一色棋的確讓他冒冷汗,部分原因是輕敵;進藤當時展現出的的專注和潛力,足以讓他打起精神應對。
可要說與sai有多像,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有明顯的差異。只是⋯⋯
想起三年前,在上海,親眼看到進藤拿下了應氏盃的決賽。
當時,從那一招勝負手中,在場的所有人都見到了sai的影子。
「——進藤的事,還是您自己問他比較好。」男人將菸盒展平放回口袋裡,「我的指導棋要開始了,失陪。」
整好領帶,推了下眼鏡,緒方轉身走向指導棋區擺著自己名牌的座位。
呵,老狐狸,又想套話。
亮失憶的事,現在完全知情的應該只有塔矢夫婦、市河、蘆原,棋會所的七位客人以及進藤。
至於那些謠言,純屬無稽之談,無非就是匿名的網絡世界正好迎合了人類作為社會生物對於議論他人的需求,再寄託了一些無法實現的幻想。
可是事關sai⋯⋯
想到平成十三年的五月四日,住在下呂的水明館那夜,還是無法釋懷。
棋院例行的兩日溫泉講習會,第一天晚上本來有慶祝自己取得十段頭銜的酒席,大概是因為老師忽然引退的事,明知已經喝了很多,卻停不下來。
「⋯⋯感覺好像是我害您引退的。您不是想再跟sai對弈嗎,塔矢大師?其實sai也是,所以請您收回那些話吧!」
之前聽到進藤在病房裡是這麼說。
看見自己進來之後,就匆忙跑了。
病房裡的白光,視線外焦急的聲音,進藤驚慌的腳步。老師否定自己的猜測時移開的目光,沈重的口吻。
這些記憶在喝酒之後湧上來,腦子裡填滿了sai的事。
模模糊糊記得那天從酒席回到會場,要求進藤讓sai和自己對弈。進藤沒有答應,可後來好像又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則是被蘆原搖醒的。
「緒方先生!沒事吧!」
別搖了。腰痠背痛,頭也疼,再搖大概要吐了。
「沒事。昨晚喝得有點多。」
斜靠在窗戶旁邊茶室的藤椅裡。看見地上倒著一個空啤酒罐,矮几上的棋盤和棋子都好好地收著。
難道是做夢嗎?
到會場的時候,聽說進藤已經回家了。
去問他那天晚上是否真的和自己對局過,會很奇怪吧?畢竟自己醉得不輕。可確實有這樣的記憶。
自己執白,對方執黑。白棋記不清了,但黑棋熟練的、鋒利的進攻,棋盤右上邊的一手在腦子裡揮之不去。
「蘆原。」
直到三年前,進藤應氏盃決勝第三局獲勝後,從觀戰室出來,終於忍不住。
「你記不記得01年五月的那次講解會,我們兩個住雙人間,第一天晚上我喝醉了?」
蘆原停下腳步,盯著他愣了幾秒。「01年的講解會?我有印象欸。」他猶豫了一下,笑道:「但是緒方先生經常喝醉,我倆也一直拼房,完全記不清哪次是哪次啊。」
「⋯⋯呃,」緒方扶了下眼鏡,「我回房間的時候,好像開燈把你吵醒了。」
「有嗎?」
「進藤跟著我回來的。」
「這樣啊?」
「我還在茶室的椅子裡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是被你叫醒的。不記得嗎?」
「欸,真有這回事嗎,緒方先生?抱歉啊,完全想不起來。」
「好吧,沒關係。」
大概半分鐘之後,蘆原突然說:「可既然當時進藤和你一起,不如去問問他本人?他總該記得吧?」
呵。
「多謝指教。」本月圍棋大會的最後一局指導棋結束,「來復盤一下吧。」
還指望進藤光?
提起這個名字就覺得煩躁。
上週二晚上承諾得那麼好聽,塔矢老師都信了他的花言巧語。週三上午去給車加了油,本以為談過之後每天會更順利才對。
可這人就這麼失蹤了?跑路了?出差也不報備日程,連一聲招呼都不打。
牙尖齒利,巧舌如簧,實際上什麼本事都沒有。還要做出一副深情的樣子。
⋯⋯實在太過分了。
亮的事、sai的事、還有當年無故缺席手合的事⋯⋯早就知道這傢伙靠不住。
張嘴就會騙人,個人主義可不是這樣踐行的。
也不知道小亮看上他哪點,難道還有我不知道的地方?
總不能是臉啊⋯⋯塔矢亮,你的擇偶要求沒這麼原始吧!
「——行不行了,這一個個的。」
「嗯?緒方老師?」
「⋯⋯沒事,是說這些棋子太舊,會有點打滑。」
算了,不能被這傢伙影響了自己分內的事。
不僅是工作,還有對亮的持續觀察也是。
明子夫人很少再開車送亮去棋會所了。如果中午有空閒,緒方就會接下這個任務。
沒有別的日程,便早一些到塔矢邸,一起吃早飯,然後和亮手談一局。
自天元戰以來,和亮的第一局棋。上午斷斷續續地下著細雨,陽光卻從未消失。自那次起,就一直將這些早晨的對局當作本該平安發生的那局棋來對待。
亮的棋和之前一樣敏銳鋒利,至於進藤提到的變化——
「我認輸了。」
「多謝指教。
「呼,緒方先生今天的進攻,感覺像公式戰一樣猛烈呢。」
二月十四日,近一週以來第一個不算冷的、完全的晴天。
到這天為止,一共和亮下過三局,沒有一局相同,而這是緒方第一次輸。
長舒一口氣,像是胸腔裡積聚的煙都散開了。
從那個驚恐的紅色寒夜以來,這是第一次清醒地看見藍天。
亮的棋在前進。即使失去短時記憶,仍無法掩蓋那份光芒。
金色的晨曦穿過庭院,灑滿了和室。好像回到了寄宿在這座房子學棋的那幾年。
太明亮了,刺得眼底發疼。
中午和明子道別,走向停在院裡的車。這幾週雖然陰冷,但玉蘭樹的花苞仍比上次看到時大了一些。
「——塔矢!」
嗯?這個熟悉的聲音是?
有腳步聲從院牆外面跑進來。
「塔矢,生日快樂!」
先看見的是一大捧藍紫色的桔梗,花瓣在陽光下變得透明。
留著雙色頭的青年把誇張的花束遞給亮,幾乎要把他的臉全部蓋住。
「——啊,緒方先生。」見他走近,亮從一片閃爍的藍紫色中抬起眼,「是進藤!進藤他來祝我生日快樂欸。」
低頭嗅了嗅,歎道:「好香⋯⋯」視線透過花莖的間隙,看見光今天穿了一件拼布飛行員皮夾克和毛邊九分褲,配黑色漆皮的高幫馬丁靴。
「謝謝你,真的很漂亮。」
抬起頭,忽然頓了一下,亮望著那些桔梗,眼睛微微睜大,小心地伸手從裡面抽出一片薄薄的、黃色的塑料盒。是一張光碟,盒子上有手寫的字。
「『早安,塔矢』?」他問,「進藤,這是什麼?」
「是給你的生日禮物。」光注視著他,「去看看吧。」
「這樣⋯⋯」
明子聽見動靜,走出來站在玄關,望著亮手裡拿的東西打量了兩秒,莞爾道:「不知道是什麼內容呢?」
「快看吧。」收起剛才過於燦爛的笑臉,光換上一副更堅定的表情,「看了就知道了。」
亮移開視線望向緒方,又看了看碟片。「那我去客廳放一下。」
他坐在和室的矮几前,緒方站在一側,明子和光在遠一些的廊下。
讀碟後,音樂響起。屏幕上出現一張日出的照片。
那是十一月在熱海的沙灘上拍下後傳給光的。
「⬤ 祝塔矢亮生日快樂!◯」一行明體字顯示在中央。
在Mariah Carey柔和的歌聲裡,亮笑起來。
祝福語淡出,下一句是:「我要告訴你一些你錯過的事。」
「十二月十九日,春蘭盃決勝三番勝負第三局,社清春六段對楊海九段中押勝。」
「十二月二十日,『緒方天元三勝二敗,頭銜衛冕成功!塔矢名人第五局不戰而敗。』」
「欸?」盯著螢幕上的標題和緒方接受媒體採訪的影像直起身,亮驚訝地眨了眨眼。
說到「錯過的事」,本以為只是不知道的新聞而已,可這個日期⋯⋯
「一月十二日,一柳棋聖對倉田十段,倉田厚初勝!棋聖戰挑戰手合第三局落幕。」
為什麼已經, 出現了一個月後的報道?難道「錯過」是指⋯⋯
「二月十二日,『第29屆奧林匹克:國際象棋、圍棋等智力比賽項目場地發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體育館。』」
畫面一晃而過,日本隊的預選名單仍和四年前圍棋週報上刊登的一樣。
確實,明年八月⋯⋯還要和進藤他們一起代表日本[3]——
「至於你為什麼會錯過,是因為這件事:」
佔滿整個屏幕的、關於一場車禍的各種新聞標題和現場照片。
「啊——!」
熟悉的紅色跑車。詭異的身臨其境的感覺,卻沒有成形的記憶,如同在看著另一個自己。摀著嘴的手開始發冷。
報導之後是病歷,薄薄的紙下面墊著一個檔案袋。
亮愣住,緩緩抬起手,摸到腦後的傷疤。突兀的實感與未知的事故和疾病一樣,讓他產生同等的恐懼。連自己的記憶都無法相信,當時的痛苦卻清晰得恍如昨日⋯⋯
左下角這時了出現一行字:「另外,緒方先生和那位貨車司機都沒事,你不要擔心。_(:зゝ∠)_ 」
「圍棋以外,國際上也發生了許多大事!」
「一月二十日,『綠色和平組織:日本恢復可恥的捕鯨活動!』」
「二月六日,美國『超級星期二』,總統候選人巴拉克・奧巴馬在閉幕式上堅定地說:『如果一直等待他人、一直等待另一個時機,改變就不會到來。
『人們等待的是他們自己。
『我們,就是我們所尋找的改變。』」
「二月七日,南極昭和基地觀測到南半球日環食。」
「二月九日,抗議者退出南極水域後,日本捕鯨船再次捕殺五條鯨魚,肇事船隊被澳洲政府追蹤。」
回到那張海灘日出的照片,上面寫道:「意外的發生已經是事實,不過你不在的時候,我們都很想你!下面是大家給你錄的留言:)」。
畫面中出現了有些熟悉的榻榻米房間,相機像是被來回拉扯一樣晃得很厲害,掃過了光和伊角,最後定格在和谷臉上。
「哎喲,還是我先來吧啊!塔矢,好久不見!不知道你為什麼請假了但是——」
伊角硬是擠到了鏡頭裡,「塔矢君,還想再次和你對弈,看到你的新棋譜。加油啊!名人的公式戰復出什麼的。」
「我的研討會也總欠個人,所以,要趕緊好起來啊你這傢伙!」
和谷君,伊角さん⋯⋯
相機挪到奈瀨手上,「吶,塔矢不在棋院的時候大家都在念叨你欸。而且,還有個超好的消息——」福井拿著一瓶汽水從右邊拱進畫面,「阿福他今年終於考上職業了喔!」
記得奈瀨有提過今年在備戰女流名人。她好像也是在院生的年限之際才考上,所以對福井君的經歷會很感同身受吧?
「哈哈,一直覺得我就是很擅長在最後關頭吊上車尾,」他對著鏡頭揮了揮手,「是希望這樣的好運也能分給塔矢啦。」
話音剛落,突然出現滿屏模糊的白色毛絨絨的東西,鏡頭拉遠一點,緩緩下移到社的臉,「塔矢,你都不知道你錯過了什麼!跟你說,我已經轉籍到東京本院啦,嘿嘿!既然你不在,以後這裡的頭銜我就全部笑納⋯⋯哎喲喂你幹什麼!」
被一隻手捶了一下腦袋,社將相機放到桌上,背景像是一家餐廳。一側聲道傳來越智略帶嫌棄的聲音:「別聽他瞎講,這人只是年前剛跟關西棋院遞申請而已,離轉籍還早著。」
這麼說來,社在十九日——應該說是去年的十二月十九日,贏下了第一個頭銜春蘭盃,現在他也已經榮升了關西棋院的九段棋士才對。
「喂喂,反正我是遲早要轉來,早說晚說都一樣吧。」社不滿地反駁,「就讓我一次說到位不行嗎,不然以後還要讓進藤重新錄一遍。」
音像在這裡切掉了,幾秒的亂碼色條過後,出現一間酒店房間的穩定畫面,光站在相機前。
「塔矢,你已經了解了吧,病情也是,大家的關心也是。話說我又上圍棋世界的封面了喔!這次古瀨村先生拍得可真不錯。」從畫外掏出一本雜誌對準鏡頭,「𠴲噠——給你看,新鮮出爐的08年二月號——」
封面上光的臉部特寫靜止地停在屏幕中央,陽光正好照到他金色的瀏海,在眼底投下一片陰影,垂眼凝視著棋盤的目光明亮而深邃。
沒有任何其他圖像、文字、聲音或特效。
一秒。兩秒。三秒。四秒。
「這碟怕不是卡帶了吧。」佇立在一旁的緒方忍不住插話道。
六秒過去。
「而且剛才的國際新聞為什麼全是鯨魚鯨魚的。」
這麼說來,進藤他⋯⋯居然還記得。
九月一起去關西旅行,參觀了大阪海遊館。站在巨大的弧形玻璃前面,仰望著幽藍的海水裡大大小小的魚類徘徊的身影,光線透過波紋在他們身上流淌。有一頭虎鯨忽然側身游過來,黑色的背鳍划過海水,朝他們露出白色的腹部。
之前有看到幾起,在美國被飼養用於演出的虎鯨傷人的新聞。
怎麼會這樣呢?
明明牠們也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野生的虎鯨並不輕易攻擊人類,甚至還會協助漁民捕魚。
那時,他就對光說自己很喜歡這些生物。
只希望牠們都能在海洋裡自由自在地生活⋯⋯
寫真照終於移開,光將焦點重新調整到自己臉上,「嘛,差不多就這些事。」
將畫面擺正一點,深吸一口氣,繼續道:「塔矢,大家都很在乎你。塔矢老師和明子夫人,還有緒方先生、市河小姐,大家都是。」
看著鏡頭沉默了一陣,光忽然沉下聲音,用很是認真的口吻說,「可以的話,也多來和我聊聊吧?
「我會回答你任何問題,只要是你想知道的。
「那,如果已經準備好,就去吃早飯怎麼樣?」微笑地說著,將相機舉起來,拉開房間的窗簾,清晨的陽光霎時灑進來。
「今天,以及之後的每一天,我都期待和你相見。
「等你喔。」
光的嗓音混合著電流聲殘留在聽覺裡。
電視屏幕暗下去,才發覺手背已經濕了。
溫熱的淚水慢慢地滑過臉頰,落下去。
用指尖擦了擦眼角。「我⋯⋯是第幾次看這個了?」
「哼,到目前為止還是第一次呢。」
「緒方先生⋯⋯」亮捂住了臉。
半晌,透過指縫看向緒方,他輕輕地開口,「您的跑車,保險公司有賠嗎?」
「有喔,」男人把手伸進平時放菸盒的口袋,「一千九百六十一萬,已經在走程序了。」
「⋯⋯欸!塔矢的重點居然是這個嗎?」光扶著和居廊下的圓柱。
「呵呵,因為視頻裡已經提到,事發當時的其他人都沒有大礙吧?」明子轉頭掩著嘴唇對光說。
「進藤君很清楚呢,小亮會在意的事情。」
即使沒有生日那天的約定,聽說了市河小姐他們一直以來的照顧之後,亮還是想去棋會所見一下大家。
「——真的?!進藤君是怎麼做到的?居然直接讓小亮知道了這件事。」
得知上午的情況之後,市河驚奇地問道。
「欸嘿嘿,就是學著做了個影片而已。」
「真是的,也可以好好和大家商量的吧,之前突然不見的那幾天我還擔心你會不會⋯⋯」她搖搖頭,雙手撐著櫃檯直起身,「唉,比起這個,大好消息,北島先生已經回來了!」
回到矮松盆景旁邊的老位置,沒有拉起屏風。廣瀨和北島在鄰座,一場對局剛結束。
「那天先是頭疼,沒過多久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北島激動地回憶著,「醒來的時候戴著呼吸器,頭上纏著繃帶,手上在掛點滴,才知道已經昏迷兩天。這個縫合的疤現在還在這裡咧!」他指了指頭頂側面的位置,「一開始手腳還不太聽使喚,話也說不利索,以為自己要癱瘓了⋯⋯」
「哎呀,」廣瀨拍了拍老棋友的肩膀,「就不要說這麼晦氣的話了。」
「你們還年輕,沒有這個感覺啊。」北島面對鄰桌的二人,說著說著開始抹眼睛,「真的害怕再也見不到小老師,再也見不到廣瀨你了。」
「這不是已經沒事了嘛⋯⋯」廣瀨嘴上這麼講,卻也拿出紙巾,摘了眼鏡,跟著一起哭。
記憶裡還是幾天前才見過的老熟人,面對他們噴湧而出經歷過生離死別的強烈情緒,亮有些不知如何應對。
只是對於永遠無法回到熟悉的世界、見到親近的人的恐懼,莫名地有著同等鮮明的印象。
早上看著光碟,似乎也有過一樣的感覺——在看到自己不戰敗的時候、和看到腦部掃描圖像的時候⋯⋯
「我認輸了。」
好像已經無路可走,便拿起兩顆白子放在盤上。
「多謝指教。來復盤一下嗎?」
進藤他,果然比記憶裡又強了一些。這樣想著,便會意識到「記憶」缺失了整整兩個月。並不是進藤在一夜之間變強,而是自己無法記住他每天細微的變化。
也不知是不是因為早上和緒方先生的那一局消耗了太多精力的關係。
「塔矢?」
得知了自己錯過那麼多圍棋界的事,又了解到背後的原因,那時的第一個念頭就是——
再也不能和他,像以前一樣下棋了。
「——塔矢?塔矢,你沒事吧?」
「嗯?抱歉,剛才走神了。」抬頭,盡力地彎起嘴角看向光。這才想起收拾盤上散亂的白子,「我們來復盤。」
「等等。」光突然站起來,握住亮的手腕。
「呃?」
「還是別了吧,你看,難得今天天氣這麼好。」
在北島先生困惑的指責聲中,光拉著亮大步走出放置桌椅的區域,一路經過前台。
「市河小姐!今天我們就先撤退了!回見!」
「欸?你們兩個⋯⋯」不顧市河的呼喊,光從衣帽架上一把撈走了亮的格紋圍巾。
自動門一打開就衝了出去,光又加快了腳步,跑過了七樓空曠明亮的走廊。
「進藤?進藤,你幹什麼?!——喂!」
突然停住腳步轉身,亮撞到他肩上。
「你——」
剛想責問,脖子周圍卻忽然暖和起來。
仔細裹好圍巾,撩出被壓住的髮尾,光抬眼看他。
「噓,拜託啦,我實在有個很想帶你去的地方。」
光將手指放在嘴唇中間做出噤聲的動作,對亮笑著眨了眨眼。
長長的睫毛掀動,寶石一樣的眼睛裡流光閃爍。
面對這樣無理取鬧的語調,鬼使神差地,亮點了點頭。
—————
「呼——乒呤乓啷——」
鄰近商場的保齡球館裡再次傳來歡呼「strike」的聲音。
「哇,又是全倒欸。」看著亮因為過分帥氣的表現而獲得不少女孩的關注,四周的男性還不停投來仇恨的眼光,光站在他身後,覺得心裡十分忐忑。
「真的是第一次打嗎⋯⋯塔矢。」
還想在他面前展示自己高超的保齡球技藝來著。
切,什麼《年輕人的情人節初次約會指南》!完全不管用啊。
「呼~」一局結束,亮轉了轉肩膀,扯掉髮繩放下扎高的馬尾,和光一起退到後面的休息區喝了點水,突然說,「對了,進藤,有件事想問你。」
欸,要來了嗎?這麼快就?
不過關於佐為,經過之前的準備,已經差不多想好要如何回答了。
所以才會在影片的結尾那麼去暗示。
亮皺著眉,似乎在思考措辭。半晌,只聽他慢慢開口:
「——你看過《湯姆和傑利》嗎?」
「啊?」
「是個美國的動畫片。」
「⋯⋯我當然知道!!」
瞪大了眼睛。如果不是在人來人往的球館裡,光大概要直接跳起來。
「你想問的就是這個?!」
「呃⋯⋯其實我自從小時候看了那個動畫,就一直有,」亮沉思片刻,眼神掠過鄰道的一對哥特風情侶,「想要在保齡的滾球道上滑一次。」
「你想從保齡球道上滑過去?」
「對。」
⋯⋯喂喂,這可比你之前那個「麵包超人和超人有什麼區別」的名發言還要驚人吶?
「可以的吧?」亮轉頭看向他,「既然球會滑過去,那麼我們應該也能滑過去。」
「呃,可球它好像不是用滑⋯⋯欸。」
忽然感覺扶在額上的手被握住拉到一旁。
只見亮側頭注視著他,鬢邊修剪整齊的頭髮貼到面頰上。水色的眼眸眨了眨,利落的眉毛顰起,一臉的認真。
「一定,可以的。」
他用力地說著,甚至還輕輕拽住光的袖子。
光忽地從長椅上彈起。
「唔,好吧!那我就來試試。」
哈,沒問題,進藤光,你從小就很擅長體育,滑冰滑雪什麼的也不在話下,所以!
助跑,對準中線,蹬地、起跳、伸直手臂——
「咚!」
全球館的人都轉過來,看著那個穿著入時、挑染金色瀏海的帥哥忽然用力地趴在了滾球道上,像條鹹魚一樣一動不動。
「噗嗤,對不起!」
光的鼻尖蹭著松木製的地面,耳朵貼在地面,朦朧地聽見亮的聲音。
「我沒想到它完全滑不起來!!」
四周響起此起彼伏的驚嘆和笑聲。
天吶。
太遜了。
已經,不想說話了。
「還好吧?」亮急忙走過來,用有些歉疚的口吻說,「應該沒有傷到哪裡?」
「只是有點⋯⋯疼。」光咬著牙回頭,「可惡,一定是這個布料摩擦力太大的問題。」
做出吃痛的表情,藉機握住亮伸過來的手,十指相扣,看見了他眼底的關切。
嘛⋯⋯不過至少亮的心情已經完全好起來了。
看來很奏效嘛,像今天這樣的方式?
製作影片這件事,還是在名古屋出差時收穫的想法。
去中部棋院前曾拜託過社一件事。之前亮在棋院的藏書室要找的那份棋譜的影印件,自己後來也找過。向桑原老師打聽了一下,好像確實存有那麼一份和秀策的棋風相仿的無名棋譜。
然而,問過管理員才得知,影印件在年前被一位職業棋手出於研究目的借走了,逾期未還。
「這位⋯⋯我也不太好催。」管理員看著電腦屏幕,摸著腦袋,面露難色,「如果進藤老師實在需要很快拿到的話,原件就在關西棋院,序列號是這個,」說著,抄寫了一張便簽遞給他,「只能麻煩您自己去一趟。」
於是掏出手機給社發去郵件——正好趕上富士通盃的最終預選在名古屋有對局,就請他順便複印一份帶過來,應該也不費什麼事。
對弈結束,和社交換個眼神,一起來到位於中區的一間牛排餐廳。
「喏,你要的棋譜。」社把一個信封遞給光,轉頭看向一旁的越智:「話說怎麼連你也來名古屋了?你這兩天沒有對局的吧?」
「休假嘛,和爺爺來看J1聯賽,橫濱水手對鹿島鹿角。」
「那爺爺他人呢?」
「大概在隔了兩個街區的另一間拉麵店吃蕎麥?」越智挑眉看了他一眼,「老人家不太喜歡這些油膩的東西。」
「哈?早說你家還開拉麵店,為什麼要約在這裡啊?我明明跟你說過不愛吃這種洋貨。」
「我管你。」提起佐料盅澆了洋蔥醬汁,越智開始切自己面前的肋眼排,「公費出差、今晚還要來白住我家房子的人少提要求。」
「還不是你邀請我去!說什麼『名古屋沒人能下棋好無聊』。」
「我也只發了這一句——」
「好啦好啦,」光一瞬間幻視了以前他和亮常在棋會所鬥嘴的樣子——這兩個人幾歲了,還能吵這麼沒營養的架?「越智他也是好意請客嘛。」
「呵,說到這個,進藤,」社笑起來,瞥了一眼桌上的信封,「你可欠我一個大人情。」
「啊啊。那我請你吃拉麵?」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請。不過拜託他複印個棋譜的事有很「大」嗎?
「不。」
社深吸一口氣,突然抱著雙臂往後一靠,盯著光正色道:
「——我要你告訴我,塔矢亮他到底怎麼了?」
越智在這時也停下了刀叉瞥向光。
兩人銳利的視線齊刷刷地投來,好像很篤定他會知道亮的下落。
在光成為職業和亮的第一次對局之前,越智就已經在若獅子戰上和他交過手,還在考試期間請他專門指導。不過莫名地,兩人的相處很難說是融洽;跟和谷一樣,越智曾說過亮很「傲慢」。之後的關係也是不鹹不淡,工作之外,似乎只有一起合宿或參加研討會之類的場合才會說上話。
至於社,從第一屆北斗盃開始,作為同年齡段實力名列前茅的棋手,也一直將亮視為戰友和對手,可也僅此而已——畢竟還有地域上的隔閡吧,個性好像也不是很對盤?增加了額外的溝通成本。
但無論如何,光都知道他們絕不會對亮心懷惡意。
他和亮也是同樣——那個不期而遇的冬天,和後來幾年的互相追逐——即使一開始有過口角和衝突,彼此說過冒犯的、不留情面的話,也無非是出於一些少年意氣、爭勝之心和棋手的尊嚴。
鋒芒相見的年紀過去,那些躁動的情緒沈澱下來,會意識到棋逢對手的難得。彼此的惺惺相惜軟化了他們的稜角。
何況以亮在圍棋界的存在感,即使棋院只是有選擇地公開部分棋手公共活動的日程,「塔矢亮」這個名字無端消失了這麼久,總會讓人生疑。如果至今仍不知道亮的下落,換了他,絕對要發瘋;不,即便現在了解到實情,也還是坐立不安。
他最重要的秘密,只有亮能明白。
「你的體內⋯⋯還有另一個人。
「不,你下的棋就是你的全部。
「這個事實不會改變,所以對我來說,就已經足夠。」
七年前那天,正午的陽光落進空蕩蕩的對局室裡,灑在亮身上;當晚的夢,也是在這樣通透、溫暖的世界裡,最後一次見到佐為,見到他令人懷念的笑容。
心裡一直緊鎖的、連自己都不再去觸碰的一扇門,就這樣輕巧地被打開了。
亮是唯一接納了現在的他和他的棋,如此接近佐為存在的真相,又仍能將他與佐為的存在區分看待的人。
所以才無法接受和亮的關係停滯不前的狀態,無法接受將來的路上孤身一人的命運。
對亮萌生了特殊的依賴,一直以來也僅僅是埋在心底。放任這份感情日漸發酵成內化而矛盾、甚至可以說是危險的心意。
只是,如果亮也對他抱有同樣的想法的話⋯⋯
「不要讓我們的時間只停留在過去!」
這便是兩個人共同的「願望」,使一切變得恰到好處。
光垂下頭,額髮微微遮住眼睛。
一晃眼已經過去多久了?
和佐為形影不離的日子裡,他是最自然、完美的傾訴對象。那之後,身邊再也沒有那麼一個人,什麼都能與他說。
他看向眼前這兩個值得信賴的友人。
不如就在這裡,試著轉變僵持的局勢吧——
—————
晚上回到酒店房間,在檯燈的暖色光線下打開信封,光將紙張抽出來。
棋譜背面還用回形針別著一張手寫的研究報告書的影印件,最早的記錄在昭和四十三年[4]。
「存在座子制和比目法,若是真跡,則是先於安土桃山時代的棋局。」
「筆跡和書道風格屬於平安或鎌倉時代。」
「紙張為上穀紙[5],平安時代後期工藝。」後面附有鑑定人員的簽字和神戶市立博物館的印章。
然而最下方的結論仍是「無法確定真偽」——協助鑑定的三位職業棋手一致認為白子的行棋風格與本因坊秀策過分相仿,平安時代又無據可考,不能排除後人偽作的可能性。
翻到正面——棋譜上執白的人,除去古代規則造成的圈地方法不同,確實能在一些定石中窺見秀策流的雛形。
秀策現今流傳下來的名局,以執黑的居多;而這個白棋的手筋,則是他再熟悉不過的下法。
「佐為⋯⋯」
手指撫摸過反光的油墨,腦海裡浮現出合起的折扇點在棋盤上的樣子。
兩人對弈的時候,佐為多是讓他執黑先行。
那是在這個世上,只有他才知道的「秀策」——
不,還有一個人。上次在藏書室裡急切地打斷了他的話,當時亮要找的就是這張棋譜⋯⋯
看著這局棋,亮也曾有相同的異樣感吧?
明明是親眼所見,切身的體會卻無從證明。
想起亮和佐為在「幽玄之間」的唯一一次對局,以Akira和sai的身分。
那時的他還不能參透他們每一手的用意,因此記不下完整的棋局。如果能夠找回來的話,或許會讓佐為附身自己的事實顯得更有說服力才對?
光看向房間書桌上的電腦。
sai的帳號七年來一直沒有登錄過,密碼還記得。
後來都用自己的ID來下網棋,也試過隱身的功能,隱身時的任何活動都不會被人看見。
打開IE,來到「幽玄之間」的頁面。
輸入那串數字,指尖的肌肉記憶恍若隔世。
記得那局是在九九年八月的一個週日⋯⋯八月十五日,上午十點。找到了。
話說這個酒店的寬帶網速很不錯的樣子?這麼多棋譜一下就都加載出來了。既然已經開了電腦,不如看完就下載那個剪輯影片的軟件試試?
向越智和社講了塔矢的病情之後,順便提起自己想到的「辦法」。
「社,你年前贏了春蘭盃,回來後在棋院辦了升段手續吧。有沒有留當時的報導?可以拿來做剪報的那種。」
「剪報?」社一臉驚喜,「你要做我的剪報啊?」
「傻啊你。」越智用胳膊肘懟了他一下,「想都知道是為了拿給塔矢亮看,他這不是記不住嘛。」
「喔⋯⋯那你要多少啊?」社摸了摸頭髮,「我之前的升段賽也要嗎?」
「唉!」在眼鏡後面恨鐵不成鋼地翻了個白眼。「我說進藤,這樣也太費事。不如就讓當事人親自對他講,還能顯得你比較體貼。」
「體貼?」光眉頭一皺。
「喔,原來你們還沒到那種程度啊?」越智喝了口佐餐的黑摩卡,「那當我沒說。」
「進藤和塔矢?什麼『程度』?」
「等等,你說的『親自』,具體是指怎麼做?」
「就是,你有DV機嗎?」越智放下杯子,用餐巾擦了擦嘴,「我爺爺平時喜歡拍影片日誌,看棒球比賽也會錄下來刻成光盤,時不時拿出來放放。
「見到有聲音的動態圖像,更能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吧?」
要給亮錄影片啊⋯⋯那麼在最新的圍棋新聞、近期時事之外,除了社和越智的份,還要再讓其他人各錄一段祝福的話剪輯在一起。
「這麼說來我也要出鏡喔。」看向旅行箱裡的衣物,「應該穿什麼比較好⋯⋯」
以及最新一期的《圍棋世界》封面好像照得還挺帥的,明天順便去買一份再來拍吧。
——咦,怎麼有對局請求?
啊,忘開隱身了。
連忙點下鼠標把在線狀態切換過來。
記完亮和佐為的棋譜,沒再看到其他新消息,只是收件匣上顯示99+,應該都是之前積攢的站內信。
又看了一眼帳號的名字,光點擊登出,刪除Cookie和歷史記錄,這才關掉了頁面。
——只有那一個人看到,應該沒事的吧⋯⋯?
—————
二月十四日傍晚,打完保齡球出來,和亮逛起男裝的樓層。
「麻煩這套也請包一下。」
光坐在第四家店的沙發上,接過店員送來的氣泡水,嘴角彎出一個大大的笑容。
看到亮穿著他挑選的衣服從試衣間走出來,就會由衷地感謝這些天通宵學習Premiere Pro做影片的自己。
寬鬆的版型、不規則的剪裁、強對比材質的拼接⋯⋯慵懶的感覺果然和冬天的塔矢很相配。
「——進藤,會不會買太多?馬上就要開春了。」亮站在鏡子前回頭看他,有些猶豫。
「今天打折嘛!以後也都能穿。」
唉,總算知道為什麼那些一成不變的日子那麼難以忍受了。
怎麼能讓亮每天都穿相同的一身衣服,簡直是暴殄天物!
商場裡播放著流行情歌,天花板上掛著愛心形狀的促銷牌子,電梯口有粉色愛心氣球,店家的櫃檯上也擺了成對的小熊。
男裝層平時就沒有多少人,在情人節這種時候,男人們也是陪女伴買衣服的居多。接過店員裝好的兩個大袋子,加上之前買的一起,光的腳步輕快起來,心思也變成一團輕飄飄的氣球。
——現在的他和亮,是不是看著也和那些戀人一樣?
原本還在想能不能一起吃晚飯,這裡離常去的那家中華拉麵並不遠。不過,義理上來說,果然還是該讓亮回去和家人一起度過這個愉快的晚上。
今天開始,有了那張光碟,差不多可以恢復到以前那樣的生活狀態吧。
走出中央供暖的建築物,光暢快地從鼻子裡呵出白汽。
不急不急。來日方長!
從地鐵站出來,慢慢走在燈火點綴的夜空下。逐漸遠離了繁忙的主路,路燈照亮的晚風裡似乎還留著晴朗白晝的氣息。
「進藤,剛才那個動畫電影,有時間的話,一起去看吧?」
「嗯?」聽到亮的問話,光向他靠近了一點,「哪個哪個?」
「皮克斯工作室的那個?商場外面的屏幕上在放預告,過馬路的時候有看見⋯⋯」又好像意識到了什麼,頓了一下,「不過十二月才上映。和你約定這麼久之後的事,很難講吧。」
「唔——」光想了一下,朝他笑起來,「不如就在今年你生日的時候去?是那天的話,一定能騰出時間的。」
「嗯,好。」
其實剛說出口就後悔了。這麼遙遠的期待,現在的他無法再掌控。
想起預告片裡又髒又破的小機器人拾起地球上人類的遺物,看著幾百年前的老舊電影,明明是這個年代再也觸碰不到的東西,還是會為那些故事落淚[6]。
身處空曠的廢棄星球,對未來不再有概念,當下的經歷也留不下回憶,好像只有過去成為了真實。
在去年生日之前,每一天做的事和追尋「神之一手」的目標都是一致的,亮也不曾刻意思考過未來。而現在,所有「當下」都與他的認知割裂,任何悲歡笑淚都過不了夜。
今天好像確實,過得太恣意了點。腦袋一熱,僅憑兒時一個幼稚的念頭就唆使光做出那種事,當著這麼多人的面⋯⋯現在想想還是很抱歉。
以後不能,不能再這麼胡鬧了。
只是,他們共同擁有的往事,仍會像雜物堆裡那臺電視機上兀自播放的褪色老電影一樣。
「你說,機器人也會和人類一樣緬懷過去嗎?」
住家的燈火從餘光掠過。
「不知道欸⋯⋯」光眨了眨眼,望向一直跟隨他們的半輪明月,「不過,人確實總會美化記憶裡的東西。
「我們懷念的其實是年輕的自己吧。那時候的愛是本能,不需要技巧。」
琥珀般的雙眸裡盛滿了溫柔,他的笑容映入亮的眼底。
「——因為是第一次。」
⋯⋯第一次?
心裡忽然積聚起一股焦灼的衝動,像熱泉從海底的裂縫噴湧而出,全身的血液都充滿了無望的勇氣。
今天快要結束了。
好像不做點什麼來把這一刻的進藤留住,就不再有這樣的機會。
好害怕,會連「第一次的本能」都忘記⋯⋯
亮的腳步變得更用力。
光看見身邊的人突然向前跑了兩步,站在路中央,又轉身面對著他。
路燈的白光從亮的頭頂灑在身後,順著烏黑的髮絲淌下來,在亮的眼睛裡閃爍。
「進藤!」他突然喊道,「其實,我一直都有想跟你說的話,想要你做的事。」
等等,這話聽著怎麼有點耳熟?
「我知道⋯⋯你一直都,喜歡我吧。」
呼出的白氣模糊了半邊臉。
疑問的句式,肯定的語氣,看破一切的眼神。
突然很緊張,光感到背後寒毛豎起,頭腦卻在發熱,心跳得像暴雨前的悶雷。
「是說⋯⋯像情侶間一樣的,那種『喜歡』。」見他不接茬,亮又生硬地補充道。
怎麼會突然提起這個!是不是剛才講錯了什麼話?
打算勸退?亮要拒絕嗎?還是在警告?
看到亮移開了視線,眼神藏在瀏海的陰影後面,眉頭微微顰起,嘴唇緊繃。
「總之,今天又是情人節,所以我可以允許你⋯⋯
「親我。」
「欸?」
晚上七點,遠處的教堂敲響悠長的鐘聲。
像被閃電劈中了。
明明是動聽的話語,為什麼!為什麼要擺出一副絕交的表情來說!
⋯⋯等等,好像亮也不完全是在生氣。乍一看不太溫柔的臉有點紅,鋒銳的視線投過來,眼神卻在躲閃。髮絲被風吹起,落在倔強的嘴角。
啊,剛才從這玫瑰色的嘴唇間吐出的句子,是什麼來著?
「親」?聽到了「親」字吧!!
腦子好像燒壞了⋯⋯
下一秒,胸口被推了下,倒退一步,後背碰到路旁的燈柱。
面前的人將一側鬢髮撥到耳後,靠近,輕輕閉上眼。
光感到臉頰被一雙手攏住。
——沒什麼比得過初吻。
亮柔軟的雙唇附上他的,比任何一個肖想過的場景和精心計畫的時機都要顯得自然。
溫熱的觸感就這樣停在那裡,不再動作。
光等了兩秒,忍不住動了動嘴角,試著用自己的唇瓣包裹住亮的下唇,淺淺地吮吸。
收到了試探的、生澀的回應,逐漸變得熱切。亮的手環住他的脖子,身體貼在一起。
「唔——」
這裡是⋯⋯隨時會有人經過的住宅區的小路吧。
正好站在明晃晃的路燈下,兩個男人,也太張揚了。
可是不想去在意,不想分心給這種事。
手裡的紙袋落到地上,響動被衣物摩擦聲掩蓋過去。喉嚨裡發出情不自禁的呻吟,在腦海裡迴盪。銀白的光線漏進顫動的睫毛,忽明忽暗,思緒亂成一團又空白一片,像雲層裡時隱時現的月。
終於,各自掩飾著混亂的呼吸,糾纏的溫度才不捨地分開。
寒冷的風從二人中間穿過,只有嘴唇的皮膚,濕漉漉的地方感覺涼涼的。
⋯⋯眼前的景象,好美。
亮側過滿是紅暈的臉,柔順的髮絲在耳旁分開,露出泛紅的耳朵。
放下踮起的腳尖,盯著被自己抓著的光的外衣領子。
「⋯⋯笨蛋。」嗔怪地瞟了他一眼,「穿了有跟的鞋,就不會低一下頭嗎。
「明天,也想像這樣⋯⋯」
亮用只有兩個人能聽見的聲音埋在胸口說。
一張一合的,是剛和他接過吻的嘴唇。致使他腦子裡閃過了一些很過分的畫面。
——進藤光,控制一下你自己!
「再給我講講你下的棋,」亮抬起頭看著他,「一起做點有趣的事吧。」
停頓一下,又移開視線,「當然,如果你有空的話。」
「有空有空,絕對有空。」
在心裡為剛才的妄想道了歉,光點頭如搗蒜。
「⋯⋯那麼,塔矢,我也有一個請求。」
亮感到光握住自己的肩膀,有力的溫度隔著衣料傳到皮膚。
第一次見面時比他還矮半個頭的小鬼,已經變成這麼有魅力、舉手投足都很有氣勢、僅僅是稍微靠近就讓他心動不已的人。
而他的戀心只屬於自己。
他說,那是出於本能的、第一次的愛⋯⋯
不知道從這對令他留戀的豐潤的唇間,還會說出怎樣的情真意切的告白——
「嗚嗚,拜託了!」光忽然拉著他的手晃了晃,做出委屈的表情,甚至誇張地抽了抽鼻子。「明天也要,再親我一次吧!就像剛才那樣。」
「啊?」
順勢抱住他的腰,光把頭埋在肩窩裡,「求求了,塔矢!你一定要寫下來啊!」
「欸⋯⋯」
「如果以後沒有這個的話,我會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
「呃。」
緩緩抬起無處安放的手。
總覺得此時的光,很像某種熟悉的動物?
剛才張嘴就是觸動人心的愛語、散發著成熟荷爾蒙的那個進藤去哪了?
⋯⋯順著光的背和脖頸,揉了揉這顆挑染的腦袋。
欸?這手感,居然還有點好摸。
要不今天,暫且先這樣吧。
來日方長。
和父母吃完飯,已經接近九點。回到房間,亮取出平時記日程和雜事用的手帳,在封面上貼了一張「醒了就去看光碟」的便簽,想了想,又加了一條「記得穿情人節新買的衣服」,然後翻開前面的日曆,把十二月十四日至二月十三日全都劃掉,在二月十四日寫上:「和進藤在一起的日子」,畫了一顆五角星。
盡量考慮著使用明天的自己更容易理解的措辭,詳實地記下了今天發生的事。
這樣的話,就不會讓光對他們的關係感到有壓力了吧?
而且能選擇想要記住和忘掉的事。今天和進藤的那局棋⋯⋯就不寫了。還是記一下和緒方先生的對局吧,會比較有動力?
不對。怎麼會這麼想!也太自欺欺人了。
把早晚要面對的問題壓在枕頭底下,總有哪天會睡不著覺。
最終還是把兩局都寫下來,分別加上了批注。
不過這樣一來,每天要看的棋譜又會與日俱增?
遲早有一天,會落得離他們太遠的。
⋯⋯應該先睡覺,等到早上腦子比較空的時候,再來想這些。
但一闔上眼,今天經歷過的一切就消失了——簡直像只有一天的生命一樣。
如果能夠一整夜保持清醒,是不是就不會忘了?還是會親身體會到一點點遺忘的感覺呢⋯⋯那樣更可怕吧。
現在去想這些事好像也很徒勞。
好好地休息,醒來之後才能以最佳的狀態面對新的一天,面對進藤。
把手帳合起來,放在枕邊,不自覺地將掌心覆在封面的便簽上。
拜託了,明天的我。請一定要看到這些美好的「回憶」。
tbc.
[1] 古瀨村沉迷在各種場合稱自己為日本棋院「內部的人」。
[2] 西曆二〇〇一年。
[3] 本文內沿用了公式書裡圍棋成為二〇〇八年北京夏季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的整活設定(小畑健画的那張亮長髮及肩的見報知名靈異寫真則是他們二〇〇四年十七歲時的樣子),覺得這樣的劇情還挺熱血的!不過現實是圍棋等智力項目都併入智運會了,至今舉辦過兩屆,現有的參賽項目為橋牌、西洋棋、西洋跳棋、圍棋、中國象棋和麻將。
[4] 西曆一九六八年。
[5] 宮廷用紙。
[6] 《瓦力》。
彩蛋已经有人找到了!居然这么快🆘
是2ch讨论串里出现的ip地址,就是我们家光亮个站的外网ip,输入地址栏可以直接等同hikaaki.top的域名来访问。
2022-01-14更新:点图已经画完了!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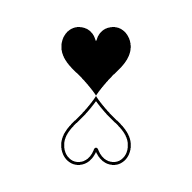
2ch真是好经典的社区了啊……虽然是匿名版,但是你们开盒是不是有点太熟练了!!!光给亮做的这个影片真的是很棒的想法,每天早晨看完这个影片,就能知道今天不再是十二月十四日了。
看着这么直率地表达自己心意的亮,真的是又喜欢又心疼,但是果然又会说情话,又会撒娇的光就是好命啊~偶尔也会想如果他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意外,肯定能谈得更顺利吧,毕竟是一直一直喜欢着对方的。但是一起去面对这样的困境,也会让他们更坚定地爱着对方吧,因为更需要勇气……
ps:社和越智的关系也很好呢,虽然看起来是在吵架,但是内容全是关注对方的对局,默认对方熟知自己的饮食习惯,白住房子,etc~
表白太太!好喜欢这个章节!录碟片这个构思太赞了,想起了151话扉页摆弄相机的阿光,很勇敢,很美好。最近工作上事太多了,整个人如同行尸走肉。中午看到太太的文感觉又活过来了。下午没那么忙了,虽说算算日子也该告一段落了,但我宁愿相信是太太和光亮酱带给我的好运。给宁比个超——大的心!
感謝您的喜歡,比心!希望您生活工作都開開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