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24歲的光和亮。關於在一起後第一個沒有共同度過的新年,以及某種程度上不在計劃之內的補償。
一月末的寒風像是覬覦室內的溫暖一樣拍打著窗戶,拉上一半的米色窗簾背後是沈沈的夜幕。
一手將行李撂在門口,另一手扯鬆領帶,進藤光坐在床沿調暗了室內的燈光,發自內心地譴責著總務科安排的航班——北海道的一場大雪導致從他那趟機往後所有的班次全部延誤;其實哪怕再早訂一班都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深更半夜才降落在成田機場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被迫要在附近的酒店住宿一晚。
「⋯⋯所以,應該要明天早上才能到東京了。我會盡早趕回來的。」
鄰近年末的時候,兩人都因棋院的工作忙得廢寢忘食;十七天連休剛開始,塔矢便依照計劃飛去中國和父母一起過年;而假期還沒結束,自己又被通知年後要去札幌出差一週——這一通下來,他和戀人已經一個月沒有見面了。
『這樣⋯⋯』隔着电话,聽見塔矢輕輕地歎了口氣。
「啊,不過,帶了很多有趣零食喔。贊助商的千秋庵這回也算出手大方,活動之後就一直在應酬;那邊有一家料亭的炭烤肉很美味、海鮮也是⋯⋯」
『——話說,現在是在棋院一直安排的成田機場旁邊那個能看到櫻之山公園的酒店吧?』
「嗯?是,你別擔心啦。」瞥到牆上的鐘,時針指在零點的地方。「現在時間也不早了,記得早點休息。明天見喔~チュッ(^з^)-☆」
互道了晚安,掛斷電話之後,進藤光回想著這一個月以來形影相弔的寂寞生活,每天只能互相發郵件,講講當天的事情,加點肉麻的很想念對方之類的話,基本是當成日記一樣寫,第二天有空的時候再去讀對方同樣洋洋灑灑幾百字的回信。
睡一覺醒來,搭上最早一班的京成線回到家裡,就能和塔矢重聚了——想看見他的臉,聽到他在自己耳邊的聲音,能夠真實地觸摸到彼此,感受到相互的體溫和心跳——想吻他。這個想法在他的腦子裡像個陀螺一樣轉著,擾亂了他的思考能力。以前不覺得,一個月果然是很長啊,他想。
盯著天花板躺了一會兒,進藤光迫切地覺得需要給自己找點有意義的事情做。他從床上彈起來,脫下衣服隨手扔在椅子靠背上,從箱子裡翻出洗漱用品,趿拉著酒店的一次性拖鞋,推開浴室的門。
鏡子裡的人眼神疲倦,連續的酒席在眼底留下暗色,胡亂翹起的頭髮在黃色的燈光下越發像一團麥桿。讓溫暖柔和的水流洗去長久圍繞在身邊的舟車勞頓的氣味,沖過澡後放了一池熱水,他閉上眼半躺在浴缸裡,長長地出了一口氣。雙手緩慢地來回感受著水流的阻力,氤氳的霧汽裡,無法控制地回想起沾水肌膚的觸感,浸濕的長髮那綢緞般的光澤,斷線的珠簾似的水花在起身時飛濺,單手擋在溫暖的脊背與濕涼的瓷磚壁之間,耳畔黏稠的聲音在唇之間顫動⋯⋯在鏡前擁吻,偶然地睜開眼睛,越過對方的肩膀與自己的視線相對;不知什麼時候交換了位置,相互推搡著,後背碰到牆上的開關——於是燈光熄滅,身體的輪廓在不完全的黑暗中流動般地若隱若現,濕潤的聲音在這潭濃墨中迴盪、交融;一切都變得緩慢,甚至產生了時間會站在他們一邊、為他們而靜止的錯覺,呼吸和心跳卻如同定時炸彈的倒數。那天他們早已無暇顧及地上、牆上和彼此身上的痕跡,記憶清晰得恍如昨日,卻總像隔著一層霧汽,讓他想起那一夜過後醒來時的清晨溫存的時光。
但話說回來,在浴室裡做真的很累。除了浴缸之外沒有可以躺下的地方,所有東西都又冷又硬,水會流進眼睛,而且會把潤滑用的隨便什麼東西都沖淡。
他將下半張臉也沈入溫熱的水中,看著自己呼出的氣體變成一串泡泡,百無聊賴地重複著用手指圈住一點水再擠出來的動作。明知道已經過了午夜,早上還要趕電車,腦子卻越來越興奮。他克制著自己的手不去做除了玩水之外的事情——堅持了一個月了,只剩這麼幾個小時而已。
終於磨到水開始變涼、不得不裹著浴袍出來的時候,忽然聽到敲門聲。他愣了一下,並沒有動——大半夜的,誰知道是什麼呢。
安靜了幾秒,對方再次輕輕叩了幾下。
「進藤,是我。」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
他衝到門口。「塔矢?」
眼前確實是思念了一個月的人,用溫柔的黑玉一般的眼睛望著他,雙頰由於深夜的寒氣而泛紅。他拍了拍自己的臉,不是在做夢也不是幻覺。
「進藤⋯⋯」話音未落就被用力抱住,險些撞上門框,塔矢愣了一下,隨即抬起手摸了摸他湿漉漉的头发。
「你怎麼來——不是,你怎麼知道我在哪間的?」一邊將塔矢拉進室內一邊問道。
「啊,我也覺得奇怪,」塔矢將圍巾和大衣掛在架子上,「和前台值班的女士說明是來找你之後,就直接得到房間號了。」
「欸?這樣都可以?!——啊,你來了我當然很開心,所以這一次可以另當別論,但是這麼簡單就能知道客人的房間,怎麼想也不是很好吧!」
「⋯⋯對方應該也只是好心。這麼晚了,連願意來這邊的計程車司機都很少。」
「啊,是打車來的嗎?」這得多貴啊!都可以再買一張機票了——一向舉止有度的戀人,偶發的超出常識的行為總令人驚奇。
「嗯,因為實在很想見到你,所以⋯⋯」
「吶,這樣的話,今晚就一起睡吧。」進藤輕快地說,隨後轉身去拉上窗簾。「你要用浴室嗎?」
「不用,」塔矢瞥了一眼他的浴袍——交領處露出的鎖骨在皮膚上投下陰影,喉結上還掛著水滴,「這個時間當然已經洗過澡了。」
房間不算大,地上敞開的行李箱裡有些東西掉了出來,衣服、生活用品和五顏六色的零食包裝袋混在一起,佔了床邊大半的空地。塔矢在心裡翻了個白眼。走過去正準備俯身整理,卻感到肩膀忽然被一股力氣向後推,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仰面倒在厚實的床褥上。進藤的雙手撐在他肩膀兩側,髮梢掛著的水珠映出紫色耳釘的倒影,滴落在米色的布料上洇開一小片深色;原本就隨便繫上的浴袍從身前垂下,能看到繃緊的胸肌與線條分明的腰腹——他有些心虛地移開了視線。
「話說⋯⋯這麼晚了,」進藤將塔矢臉頰旁的碎髮別到耳後,「大費周章地跑過來,只是因為想『見到』我嗎?然後呢?」
進藤的眼神背著燈光,像窗外的夜色一樣難以看透,卻似乎散發著太陽般的熱;塔矢越過他的肩膀看向天花板的邊緣。「別開玩笑了,真是沒點正經。只是想你了——一個月沒見,想和你下棋而已。」
「這樣啊⋯⋯」進藤歪了歪頭,湊得更近,「我也是,不過你看這裏也沒有棋盤——就先下盲棋忍耐一下吧?我先來,十七之四。」
塔矢從他和以往對局時相似的認真神情裡看出了一些別的東西。「嗯⋯⋯四之四。」果然,這人嘴上說著要下棋,手卻開始在他身上亂動。
「十六之十六。」進藤的指尖突然探入襯衫的下擺,從背後摸上他的腰,「說起來,在想我的話,最近有自己解決過嗎?」
「啊⋯⋯解決、什麼。」塔矢裝作沒聽懂他話裡的意思,身體卻無法掩飾地隨著在皮膚上久違的觸碰而顫抖,「⋯⋯四之十六。」
「那就是沒有咯?可是要忍一個月,不會很難受嗎⋯⋯六之十七。」說著,他離開了腰際的皮膚,轉而來到胸前揉弄起那裡已然挺立的兩點。「看吧,一碰你就有反應了,不只是這裡,下面也⋯⋯」
「呃⋯⋯三之十四。進藤!唔——」下意識地握住進藤的手腕阻止越來越過分的動作,對方卻在他出聲的時候俯身吻住了他,舌頭沒有猶豫地直接探入,重重滑過上顎和齒列,抵著舌根處的軟肉與之交纏。這樣粗暴的親吻令他難以呼吸,耳邊只剩下清晰的水聲;闊別許久的綿密觸覺使意識蒙上一層霧氣,不禁放任自己被熟悉的肉體渴望支配,他弓起身扭動著腰來緩解下腹竄上來的火,於是這火的源頭又與對方相貼。他不住地從喘息間隙發出含糊的呻吟,喉結滾動著吞下渡來的津液。待離開時,進藤還意猶未盡地吮吸著他的舌尖,隨後終於從口腔退出,唇間牽出的銀絲隨之拉長、變得彎曲,又落回他張開的口中。
「呼⋯⋯」光抬起頭,視線無法從自己剛才銜住的那兩片嘴唇上移開,濕潤的唇瓣泛著水光,舌頭被輕輕咬在齒間——亮的臉上滿是親吻過後的情動之色,眼瞼微闔,睫毛隨著凌亂的呼吸不住地顫動,眸中朦朧地含著他的影子。
「塔矢,很想要吧。」跪在亮的雙腿之間,膝蓋隔著外褲若有若無地碰著他,「我也是,這一個月裡每天都會想起跟你做愛的感覺⋯⋯」光抓住他搭在自己肩上的手來到二人緊貼的下身,「這裡都是因為你,才變成這樣。」
手指撥開浴袍的前襟,碰到那個熟悉的地方時,腫脹硬挺的觸感讓塔矢的動作停頓了一下;條件反射地用手掌握住上下套弄,又不可避免地碰到自己長褲下的敏感之處,進藤逐漸變重的喘息隨著他撫摸的節奏灑在他臉側,髮絲被溫熱的呼吸輕輕吹起。
這幾日,每每夜晚躺在酒店的雙人床上望著漆黑的天花板時,就會回憶起塔矢的手在自己身上的感覺,然所有的記憶加起來都不及這一刻真實的刺激;分明都是下棋的手,塔矢柔軟的掌心、指尖恰到好處的棋繭、指腹按在跳動的血管上的力度,都能夠帶來他自己永遠無法實現的強烈感受,像是火花從肌膚相碰的地方爆炸開來,在全身的血液流竄。他的額角流下一滴汗,混入髮際的水珠裡,「——呃、亮,不愧是⋯⋯」
「進藤⋯⋯你也、不要停啊。」
「?」他望進塔矢濕潤的眼睛。
「三之十四之後,你的下一手呢?」
「——欸?那種事情早忘了吧!虧你這種時候還能想那麼多⋯⋯我投子了啦!」看著塔矢潮紅的面頬,浮著水光的眼睛恣情而真切地望著他,心裏一陣悸動;他暗自腹誹道,當初說不能把下棋和這種事情相提並論的是他,現在一邊做一邊想著下棋的也是他,有什麼毒,看來是自己還不夠努力啊!
單手解開塔矢長褲的扣子和拉鍊,白色底褲上果然已經暈開一片水漬。
「才第七手就投了,看來進藤本因坊最近是太過鬆懈、呃——」
「對我用這種盤外戰手段的塔矢名人也不光彩嘛。」光拽下他的內褲,手掌利落地握住彈出來的肉莖,「鬆不鬆懈,試一下就知道了。」
「唔⋯⋯說什麼盤外戰。」亮因為他在敏感處的撫弄而顫抖,咬了咬下唇抑制住呻吟,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隨後也握緊他的性器,「是你自己,居然連下到哪都忘了——」
「嗯——」復被包裹住的感覺讓他頭皮發緊,想要在那舒適的掌心裡直接衝刺起來,但瞥見戀人頗有惡作劇意味的眼神,又不甘心如他的願落了下風,遂想尋求一些餘裕,他便道,「話說這種時候,該把衣服脫掉吧。」
塔矢愣了一下,有些不情願地收回手,猶豫著將襯衫的釦子一顆一顆解開,露出白皙的胸膛和腰腹。看進藤一瞬不瞬地盯著他,也準備褪下浴袍時,卻說:「那個,你穿著就好。」——自從有一次看過進藤穿羽織的樣子,總覺得這種不同於平時的、東洋風的衣著也很適合他,而且莫名地十分⋯⋯性感。二十四歲的年紀,雖然頂著一雙沒什麼年齡感的、清澈的圓眼睛,臉上還是稚氣未脫的樣子,肩膀卻已經成長得宽阔可靠,和服硬質而有垂感的布料亦比現代的立裁更能襯托出年輕結實的肉體有張力的線條——這種私下裡會見到的、他偶爾流露出的端正的男性氣質,對自己也能有如此的吸引力。明明剛認識的時候還是個完全沒長開的毛躁的小孩,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思緒被眼前人接下來的動作打斷,進藤忽然跪到他枕邊,嘴角掛著一抹戏谑的笑,「一直盯著我的胸口看,在想什麼呢?」不知何時湊過來的慾望正貼在他胸前輕輕蹭著,前端冒出的液體在皮膚上拖出晶瑩的痕跡,「來吧,摸一下這個,亮,是你想要的吧?」
塔矢眨了眨眼,過近的距離讓他一時之間難以聚焦起視線看清那個形狀。而手指覆上柱身的時候,記起它在自己體內的感覺、衝撞時帶來的快感,讓他喉嚨有些發乾;龜頭從圈起的手裡頂出,碾過挺立的乳珠來回肏弄著,下面也被握住撫摸,不禁從唇間漏出一聲呻吟。性器的熱度和液體接觸空氣的微涼交織著貼在那處敏感的皮膚上,致使胸前泛起奇特的酥麻,明明不該是性感帶的地方,卻被褻狎的動作調動起官能,肌肉戰慄著,仿佛乳孔都張開了——不止一次在自己身體的各個部位做出過分的事,即使覺得有些不可理喻,仍是逐漸習慣了跟這種羞恥感共處;只因每每看到進藤認真的表情、直白而坦然的視線,明白他在渴望自己,得到這樣的反饋便會不自覺地沉浸在這份愛意裡,心中泛起波動的漣漪。
——已經,變得這麼奇怪了嗎。
進藤望著他迷離的眼睛,手的套弄不由地從綿長變為粗重,看到他隨著自己的動作扭動身體,微張的唇瓣之間毫無克制地溢出顫抖的喘息,凌亂的襯衫壓在身下,衣袖纏著手臂,青絲在這一片淺色上散開,有幾縷貼在汗濕的臉和脖子上,他突然記起曾經閃過腦海的一個想法——
「哈啊⋯⋯能不能稍微借用一下⋯⋯」說著牽起塔矢肩頭一束長髮放在他指尖,「這個。」
「欸?什麼⋯⋯」話音未落,手被進藤握住,捲著自己的髮絲一起在性器上來回摩擦。
「——嘶、真是,很久以前就想要這樣了,」柳絲般的黑髮不論什麼時候都梳理得順滑柔軟、髮梢如本人一樣平直得一絲不苟,在光線下總是流淌著綢緞一樣的色澤,低下頭時順遂地分開露出秀雅的後頸,也把那處肌膚映襯得更加白淨;躺下的時候就在身後散開,像海水的細浪一般隨著身體的動作輕顫;坐在他身上時則會垂落在周身,夾著優美的喘息聲拂過他的臉,如春日的旭風撩撥起他的心弦,叫人心癢難耐⋯⋯「一直、想用你的頭髮做做看什麼的。」
「啊、嗯。」雖然沒什麼可拒絕的,畢竟以現在看來,不管怎麼樣都要再洗一次澡了——但這都是從哪學來的東西,認真追究起來已經屬於戀物癖範疇了吧⋯⋯可抬起眼便看到進藤咬著牙、期待又有些緊張的神色,還是順著他的意思用手指捲起一綹直髮,嘗試著從頂端纏繞著向下撫弄。
「唔嗯⋯⋯果然、好厲害——」上下動作的阻力變大,被緊緊纏繞的膨脹感也比手指的觸摸多了一種電流般麻癢的感覺。
進藤向後仰起頭,喉結上下滾動,向前頂著胯將慾望在塔矢手裡前後抽插,塔矢不得不用雙手握住那衝撞的肉柱才不至於讓它滑出去;那件浴衣由於激烈的動作從一側肩上滑落,露出形狀好看的手臂肌肉。
他聽到進藤粗重的喘息,「好厲害啊,亮——」
真的會這麼舒服嗎⋯⋯儘管不太能共情這樣的喜好,但看著進藤這麼激烈的反應,用燃燒著情慾的視線望著自己,竟生出一種奇異的滿足感,手指也握得更緊;盯著手中圈住的性器,看到前端在虎口處進出,儼然像是交合時在自己體內的視角一樣——無法控制地胡思亂想著,他面上全是赧色,而光頂弄的動作也隨之變得粗礪。
「呃、你慢一點、唔——」陰莖突破虎口撞到他的臉頰,在唇邊留下一點粘膩的液體,卻沒辦法抬手去擦,只得伸出舌尖,卷著那一點晶瑩放入口中,又急喘著舔了舔乾澀的嘴唇,隨後便感到手裡的東西脹大了一圈。
看著下意識做出這種行為的亮,光顯然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忍住想要再一次頂到亮的嘴的衝動,他緊咬著牙,報復性地用左手掌心旋轉著壓迫冠狀溝,包裹住龜頭旋轉,一直捋至他性器的根部,看著身下人兩條長腿不自覺地顫抖著分開,正扭著胯不知是要向自己手裡送還是要逃離,視線落在自己在他手心的動作,雙目卻失焦——又在自顧自地想色色的事了吧;從第一次性愛開始就察覺到了,有著跟清冷外表並不相配的、這種体质的戀人,總是耽溺於快樂的絕妙肉體在被逼迫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出現一系列不得了的反應,甚至能够享受些微的痛觉带来的快感,而這時呈現在臉上的也淨是令人血脈賁張的表情——眉頭微蹙,汗濕的瀏海斜著貼在額前,淚水含在泛紅的眼眶,被打濕的睫毛沾在一起像瀕死蝴蝶的翅膀般顫動,軟舌微微探出齒間,略顯沙啞的嚶嚀混合著短促的抽息和吞嚥聲從雙唇洩出。
「進藤、別——至少、慢一點⋯⋯啊、嗯⋯⋯」
真是的,都什麼時候了,說什麼「慢一點」,光想,更何況之前的教訓告訴他,現在如果真的慢下來一會兒就要被責怪為什麼突然停下,在這種事情上發少爺脾氣又不能說什麼,吃一塹長一智,他再也不會上當了!——而且做出這種樣子,只會讓人更想欺負吧,什麼叫口是心非,什麼叫強人所難——看到亮弓起後背,仰著頭露出脆弱的喉結,好看的鳳眼因為被過多的快感衝擊而微微吊起雙眸,仿佛快要到達頂點的樣子,光忿忿然用手指按住了他陰莖的繫帶處,隨後如願地看到眼前人因為射精慾望驟然消退而愕然地瞪大了眼睛,便又收緊手指捋動起來,並刻意用指甲和掌心的繭反覆擦過尿道口與鈴口。
釋放的渴望被毫無徵兆地截斷,復而飛快地繼續攀升,這種失重般的體驗意外地帶來了嶄新的刺激;他對光不可預料的動作感到害怕,被掌控著射精慾望的不安全感又讓高潮的到來變得更加清晰而強烈。
「嗚嗯、不⋯⋯啊、進藤——!」
亮帶著哭腔不斷地叫著他的名字,張開的大腿內側肌肉痙攣著,腹部收緊後漸漸舒展開來,清淚積聚在眼角,雙手從光的性器上滑落到腹股溝,伴隨著不應期而湧上的羞恥感讓他想要將腿合攏,卻被胯間的手阻止;光用兩指捋著繫帶處,看他呻吟著射出最後一點白液。
而他回過神來聽到的第一句話是:「吶,亮,能不能、稍微張嘴?」
進藤的手在他臉頰旁邊慢慢擼動著依然挺立的慾望,上面還纏著自己的幾束頭髮,濕潤的前端透著紫紅;半乾的金髮散落進琥珀色的眼睛裡,眼底的渴求毫不遮掩,眉頭難耐地皺起,嘴角卻微揚著。
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是,塔矢亮有著恪守傳統的原則性的一面,譬如對禮儀的要求、對圍棋的認真;但只有進藤光清楚,和絕大多數包括自己在內的道貌岸然的日本人一樣,亮在床上對性並沒有什麼道德感。他記得自己第一次準備跟亮做到最後時專門找了同性戀色情片來補習,看著兩個男人在屏幕裡翻滾卻只覺得奇怪,兩具肉體激烈地碰撞著彷彿在摔角,堪稱毫無美感的畫面令他尷尬不已,但真正嘗試過後便覺得因為是和亮,才能做什麼都樂在其中。再加上亮在這方面是名副其實的「天才」——即使缺少經驗,善於享樂的身體和精神上的韌性仍使他在床上能夠做到非常不可思議的程度,比如震驚於亮第一次口交就能成功深喉——這也很嚴重地慣壞了自己,明知道很過分,卻又非常享受這個過程,甚至後來逐漸演變成事後偶爾會再在他嘴裡紓解晨間的反應——好像只要時間允許就不會被拒絕呢。而一想到平時在他喉管裡那種濕熱緊窄的感覺——形狀姣好的嘴唇被性器撐開捅進深處、眼角被淚水浸得嫣紅卻還是認真地一下一下嘬吸著、壓在肉棒下面的舌頭竭力地動、原本纖細的頸間被肏弄得鼓脹起來的樣子,進藤光只覺得頭腦越發混沌,除了想要一直看著這樣的亮,已經無法容下其他的意識。
亮以為他想像往常那樣在自己的喉嚨裡解決,便輕啓雙唇含住了性器的頭部,舌頭繞著圈舔弄,收起牙齒,並沉下了舌根將肉莖納入深處,讓龜頭頂在會厭處的同時做出吞嚥的動作;但進藤卻沒有像以往一樣配合著頂入——塔矢疑惑地抬起眼,透過散亂的瀏海有些吃力地望著他。
進藤看著他睜大的濕潤雙目中驚訝的神情,小幅地擺動腰腹讓小半截陰莖在亮的口中抽插,手指則纏繞著黑髮以相同的節律套弄著根部,赤裸的視線在亮的眼睛和嘴唇之間移動——褻瀆戀人這張漂亮的臉,看著他為取悅自己而努力的樣子,便會萌生出一種罪惡的成就感;能夠獨佔這樣的亮,這種認知讓他的血液幾乎都沸騰起來,粗重的喘息和著水聲在充滿情色味道的房間裡迴盪。
不清楚他為什麼沒有配合,塔矢試圖將頭向前傾,以讓他的慾望更加深入,卻聽到對方在愈發急促的吐息間低聲說:「等一下、別動,稍微⋯⋯我就要、呃!」
厚重的液體忽然噴濺在舌苔上,一股接著一股順著舌面流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被直接射在「嘴裡」,感受著濃稠一波一波地灌入,強烈的酸苦味道衝擊著他的味蕾,而陰莖還未退出去,僅僅是前端放入塞滿口腔,迫使他松著下頜,舌頭艱難地舔舐輕輕頂弄上顎的龜頭;因為平躺著側過臉的姿勢,來不及吞嚥的白濁從嘴角流下,滴落到米色的床單上。
光用拇指抹去亮唇邊的精液放到嘴邊,「呃、果然很濃吧⋯⋯畢竟我可是、等了一個月——」他的左手擠壓著性器根部,亮感到口中的東西還在跳動,「哈⋯⋯現在、全都、交給你了。」
他們維持了一會這個姿勢,精液的量比平時大些;而終於從亮嘴裡抽出時,龜頭帶出了一串半透明的黏液。「唔,」亮用指腹擦掉嘴邊流下的液體,又抬起手重新抓住光的慾望。「——也太多了吧,」他側過頭舔了舔肉柱上的殘餘,「而且為什麼非要射在嘴裡?真的很過分⋯⋯這麼想要我吃下去的話,」換了一個角度繼續著,讓柱身蹭過鼻尖,「和以前一樣在喉嚨裡射就好——」
喂喂,一般人的常識裡單就這兩者來說,明顯是深喉更過分吧!為什麼你這裡會反過來啊?在奇怪的地方被追責,見他微蹙著眉用一種不滿的眼神盯著自己,又分明在認真地伺候那個地方,光心裏昇起一種不好的預感。
「哈、因為這樣就不用嚐到那種味道了,」仿佛知道他在想什麼並做出回答一樣,亮一面說著,又舔過下方的囊袋,把方才順著肉莖流下掛在那裡的精液也捲入口中,「很難吃,味道太重了⋯⋯而且溢出來的話會黏得到處都是吧。不過比起這個,進藤——」重新從根部向上舔到前端,舌頭在那裡的小孔上打著圈,清理乾淨裡面的濁液後,他看了光一眼,隨即緩慢地垂下視線輕輕吮吻了一下龜頭,「忘記跟你說了,歡迎回來。」
完了,太超過了,光想,原本打算這之後去清洗一下就可以睡覺的,但這一刻看到亮這樣的眼神、水盈盈的雙眸,視線越過上挑的眼角看著他、凌亂的長髮粘在他的臉和自己的性器上、粉紅的舌尖掛著那些液體的樣子,臉上身上全是情慾的痕跡卻說著這種游刃有餘的話,便覺得下身的火又要燃燒起來。
「不好吃⋯⋯嗎?可是這裏,」低下頭,上半張臉被汗濕的金色額髮蓋住,他鬆鬆地圈住亮再次抬頭的慾望,浴袍的袖子掃過大腿,「不是覺得很喜歡的意思嗎?」
「唔——要有這種廢話的時間,是不是、也該進來了。」亮瞇起眼睛盯著他,抬腿碰了碰他胯間的硬挺。
雖然這樣的催促是很讓人心動沒錯,「——可是你有帶套嗎?」
「嗯?這種東西平時不都是你在準備⋯⋯」
「可我去出差欸!又不是和你一起去,當然不會帶吧。」帶了能幹嘛啊。
「那就直接進來,反正⋯⋯」反正大家都是男人。
——什麼「直接進來」,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突然發出這種奇怪的邀請——進藤光腦中登時浮現出曾經看過的AV片名,什麼「ムチムチ美人といつでも中出しして孕ませOKの夜」之類、色情的吸睛標題——不過還好潤滑的東西勉強是有的——歹勢,他還只是個二十出頭的小年輕,根本經不起這樣的考驗。心中默念幾遍「進藤光你真是個混蛋」,抱著一定程度的負罪感,他俯身從床邊一團衣服中間的一個小旅行袋裡翻出一瓶資生堂的滋潤乳。身後傳來皮膚與床單摩擦的聲音,停頓了片刻之後,又聽到一點細微的喘息。
再次轉過身的時候,眼前的景象變得非常⋯⋯難以言喻。亮背對著他趴跪在床上,雙手抱著枕頭,臀部翹起露出私處,從肩膀到後腰彎成一個圓潤的弧度,分開的大腿內側繃緊,性器沈甸甸地下垂,頭部在一片狼藉的床單上輕輕磨蹭。感受到床上壓力的變化,亮越過肩膀回頭看他,黑髮從背上順著肩頭滑落,露出泛起粉色的皮膚和脊柱與肩胛的淺淺的陰影。
進藤光感到自己腦袋裡有什麼東西「嗡」地一聲碎裂。他把手裡的瓶子連著按壓泵一起打開,胡亂倒了一大堆乳液在亮的臀縫間,看著透明的液滴流過後穴,順著會陰處和漲紅的肉柱落到身下匯聚成一灘。
亮瑟縮了一下,本能地向前躲開,「喂、好涼⋯⋯」
把瓶子扔在一邊,他掐住亮的腰側把人拉回來,前端藉著潤滑頂開穴口,就這樣整個沒入。
「嗯、嗯啊,進藤——」
濕熱的內裏像是記得他的形狀一樣緊緊吸附著,臀肉被頂撞得一下下顫動,皮膚很快染上一片殷紅。粗暴的進入卻意外地順遂,內壁層層疊疊地纏上來把他包裹住,未曾料想的溫軟觸覺讓光倒抽了一口涼氣——這樣的體感,如果不是這段時間裡自己玩過,至少也是今晚來之前就有做準備;而無論怎样都太糟糕了,却從一開始就裝出一副無辜的樣子。想到這,他有些負氣地加快頻率頂撞起那處只有自己知道的弱點,從齒縫裡擠出一句:「這種時候,嘶——該叫、『光』、吧。」
亮將臉埋在枕頭裡,長髮隨著身後的撞擊而晃動;斷斷續續的聲音無法分清是想要說話還是呻吟,卻逐漸變得密集、婉轉,像是某種閥門被打開一樣不受控制。光感到手指下的肌肉在抽搐,腰臀迎合他擺動,穴口越夾越緊。
「哈⋯⋯真是狡猾啊。你這樣、讓我⋯⋯」他用力碾過深處微微凸起的那個地方,「讓我、呃、根本不能跟、其他的⋯⋯做、」進出的時候都像是被吸著一樣,手指在身下人腰間柔嫩的皮膚上施力留下發白的痕跡,「再也沒法喜歡上、除你以外的人了——」
亮搖著頭,幾乎要被沖散的意識依然一字不差地接收到了進藤的話語,儘管不想承認,對方這種彆扭地暗示只鍾情於自己的表達真實地給予他一種躁動著、從脊柱直衝到下腹的愉悅感。「⋯⋯唔、呃、在胡說什麼——到底是誰更狡猾,還說什麼把、嗯、一個月的都、啊、都射給我⋯⋯哈啊——」字和詞粘連在一起,本人好像對覆述的這句話有很大的反應——腸肉忽然痙攣著絞緊,他的身體不住地顫抖,連腳趾都蜷起來,「啊、光——!」
白色的濁液混入不久前滴落的潤滑劑,亮微仰起頭,下沉的腰肢不自覺地輕微擺動來讓體內的東西在那一點上更重地摩擦,試圖延長高潮的餘韻。
「嘖,真是⋯⋯」他模糊地聽到光的聲音,「自己的手指能夠到這裏嗎?」
還未來得及適應,身後的衝撞就變得越來越快,每一下都刺激著同一處;不知是淚水還是什麼的液體浸濕了枕頭的布料,微涼地貼在臉上。
「少囉嗦,你倒是⋯⋯」溫潤的嗓音已經有些沙啞,說出責備的話聽起來也更像是在誘惑,「嗚、快點——」
「哈,馬上就⋯⋯」誤打誤撞地,對於內射的臆想將要變成現實;沒有那層硅膠的阻隔,陰莖直接貼著腸壁的黏膜,未曾有過的濕軟觸感讓他下腹發熱,肌肉隨著抽插的動作有節奏地顫動,光不耐地壓低了聲音沈吟道,「給我、接好了——」
龜頭捅過狹窄的結腸口,在這個逼仄的湫隘來回肆掠,身下人的腰沉了沉,甬道深處再次輕輕收縮起來,唇間溢出破碎的哭叫。
「唔、嗯啊⋯⋯光——」從下腹到腿都變得麻木,身體也使不上力氣,宛如隨著潮水漂浮,口中不由地像囈語一樣呼喚著愛人的名字,綿密而持續的快感如同海浪般一波接著一波襲來,用後穴高潮的體驗顯得緩慢而悠長,似乎時間都靜止下來,這讓他想起醉酒的感覺。
恢復過來之後,像是從海面之下浮上來睜開了眼睛一樣。陰莖已經退出去,腸道裡黏膩的感受開始變得清晰,亮翻過身來仰躺在枕頭上,小心地避開床單被弄濕的地方,努力平復著躁動的呼吸。
光跪在他腿間,手肘撐在他肩膀兩側,敞開的浴袍落在他身上。嘴唇被輕輕含住,緩慢地舔舐、吮吸,舌尖相觸,隨後交纏在一起;光的額髮撫到他的臉頰,手攀上胸口看似漫不經心地摩挲,卻總是刮到立起的乳珠。
他抬手捧著光的臉,指尖滑過對方耳垂上那枚紫色的圓石,望進那雙睜大的琥珀色眼睛裏。「所以,結束了嗎?」說著環住他的脖子,雙腿纏上他的腰,用臀間沾有濕液的肌膚蹭了蹭他仍然半硬的性器。
身上的人半瞇起眼睛輕笑了一聲,「結束?」腳腕被提起,膝窩掛在光的肩上,「你覺得呢?」
冬天的長夜總是讓人錯覺晚上的時間是用不完的,直到忽然發現天邊的顏色變淡,而日出似乎又是一瞬間的事情。新年共度的第一天,清晨的陽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灑在相擁著熟睡的兩個人身上——他們顯然沒有趕上第二天早上的京成線,但是又有什麼關係呢。
終わり。
End Notes
寫到亮被問「自己的手指能不能夠到」然後回復「少囉嗦」這句的時候,本來想讓他說「就知道說話你行不行」之類的,雖然最終沒有這樣說(白:亮老师说话没有这么俏皮啦,这种毒舌的发言怎么更像是越智的台词⋯),但是產生了以下的沙雕。是社x越智。
越智和社下棋,社輸了。
越智:你到底行不行,你是不是只有嘴上行啊,不你嘴上都沒有我行。
社:我這就告訴你什麼叫嘴上行。
片刻之後,棋院的路人聽到一個房間裡倆小孩吵架,什麼「太粗了太長了」「嘴上行不行」之類的,覺得不太好就去看。一推門。
社:我這就吃給你看。
說著拿起一個惠方卷熟練的吃了起來。
為什麼就變成這樣了呢。最早只是覺得「不行」三連很適合讓越智說而已。已經不認識「行」這個字了快要。(不過社和越智是很可愛啊隨便什麼順序都行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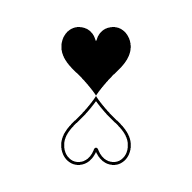
我又彳亍了
光崽的情话是曲里拐弯的,xp也是花样翻新的,相比之下,亮宝都是打直球的,耐受力也是max的……
ps:我就想问第二天退房是不是又得赔床单钱了🥳🥳🥳🥳
床單讓棋院報銷了!(bu
光嘛就是覺得看著很straightforward但是有時候就很彆扭(?然後亮就看著很彆扭其實有時候很straightforward
然後如果做出沒有自覺的直球行為就更好了就很有意思kkkkkk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