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快樂!小亮。」
棋會所的自動門打開,市河晴美倚著櫃檯,微笑著輕聲道。
「謝謝妳,市河小姐。」他將包遞出去,把大衣和圍巾掛在門口的衣帽架上,「今天也麻煩妳了。」
「哪裡。吶,這個給你!」
亮從市河手裡接過一張對折的小賀卡,淺黃色封面上印有白鶴和櫻花的圖案,裡面工整地寫著:「小亮,生日快樂!天氣變冷了,要注意保暖喔~」句末一個簡筆畫的戴著毛線帽和圍巾的小雪人。
「啊,太可愛了!真的很感謝。」
21歲了啊,父親今晚回家,待下週四他和緒方先生的天元戰第五番勝負後,會留在日本一起度過聖誕新年假期。有許多想要和父親討論的近期的棋譜,也很期待看到父親在中國和韓國的對局⋯⋯
這麼想著,亮走到矮松盆景旁邊的位置。這裡沒有開燈,擺放盆景的展櫃裡溢出淡藍的螢光。相鄰的棋盤前坐著一個人。
廣瀨幸雄[1]這些年來都是棋會所的常客,與這裡的諸多老伯一樣看著亮長大。平日裡,他都會在亮進門時和藹地打招呼;然而今天他似乎沒注意到來者,正獨自打著譜,盤上的黑與白仿佛滴落的雨聲。
「日安,廣瀨先生。」
直到亮來到座位旁,中年男人才從那聲音裡抬起頭。
「小老師。」又補充道:「生日快樂。」
「謝謝您。」
亮落座後整理了適才被圍巾壓住的衣領。市河小姐端來茶,又拉上一旁的屏風,四面的視線都被遮住,恰好讓他無法看到門口,外面的聲音也變得含糊。
「市河小姐,這是⋯⋯?」
亮扶著茶杯。
從前沒有注意到這扇屏風;是什麼時候放在這裡的。
「啊,這樣就可以擋住冷風了。」
「可這裡有暖氣⋯⋯其他的客人不要緊嗎?」
「因為這裡正對著門嘛。」
她又將聲音壓低了一些,「而且阿亮你約了進藤君下棋吧?這樣你們就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了。」
這麼說來,今年的生日確實比以往的十二月要冷一些,是因為聖嬰現象嗎。
從天亮起就覺得天空灰白潮濕,似乎一下子入了深冬。早上排棋譜的時候偶然出現了陽光,午後便藏到雲層後面,還起了風。
母親或許是因為這樣的天氣才選擇開車出行順路載自己來棋會所的吧?進藤應該也不會騎單車出門。
說起進藤⋯⋯前幾週,他忙於天元的挑戰,進藤也一直有自己的賽事,甚至見面的次數都屈指可數。繁瑣的日程讓他仿佛快要忘記與進藤對弈的感覺;指導棋、出差、一些賽事伴隨的社交活動,在這些場合裡他總覺得像個舞台上的道具,得不到真切的交流。
直到此刻,在約定好的時間,熟悉的地點,等候想見的人。
看著眼前十九路的棋盤,揭開棋盒;室內的空氣散發出溫暖柔和的香味。棋子的觸感讓他不禁期待起要與那個人發生的對話⋯⋯亮搖了搖頭,像是在掩蓋什麼似的伸手整理瀏海。
進藤將要見到自己的時候,大概也會是類似的心情?
亮記起那時他眼睛裡閃爍的陽光。
那是三個月前,穿著薄風衣不會冷的晴天,他們離開棋會所的時候,進藤忽然說:「下週四有空嗎?要不要一起吃晚飯?」
「欸,就我們兩個嗎?」
當時有些驚訝;印象裡,往年進藤都會叫一大堆朋友一起聚會,「你沒有叫別人?」
「笨蛋!」進藤的聲音高了一些,又小心地落回去,「就是想單獨跟你去才會約你啊。」
他有些窘迫地摸了摸頭髮,眼神從建築的牆壁飄向腳尖,停了下來,抬起頭看著亮,「要來喔。」
在害羞?語氣卻還是很認真。
「⋯⋯那,如果那天沒有手合的話。」
下週四就是九月二十日——是光的生日。
亮很清楚自己當日確實沒有對局。然而,週初去總務科進行交接時,又突然被安排了二十日下午公開賽的講解工作。
說是每一季度的「公開賽」,其實是面向大眾推廣圍棋的宣傳活動,對局也更注重表演性。至於講解人員,自然會在賽程輪空的棋手間選擇知名又有親和力的。
「這樣啊,我知道了。」
亮照常接過總務科秘書處工作人員剛寫好的日程通知。
該怎麼告訴進藤呢?是工作的話,他一定會說能夠理解的;可認真的生日邀約原本答應了又被拒絕,這難免有些⋯⋯
原則上不可能因為自己的私事而影響工作,這本來也是自己所重視的職責。
亮從小就理所當然地將圍棋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如今在職業場合與更多的人交流,意識到在當代的日本這是日漸邊緣化的、大眾不常接觸的「古老的」東西。
直到這時,他才真正明白棋士的身分背負了多少重量。
總有一個聲音在心底徘徊著說,能有多一個人,再多一個人對圍棋產生興趣就好了——每次都懷著這樣的心情做著圍棋的宣傳,也很樂於回應棋迷的互動。漸漸地,他在大家的笑容裡獲得了不同於與高手對弈時的另一種滿足。
本應是滿足的啊。現在卻為什麼,會感到失落?
一頓晚飯而已,只因為約定的對象是進藤、時間是進藤的生日,才變得不一樣⋯⋯這種情緒,明明不該被允許。
亮握緊了手,指甲在白紙上留下淺淺的半月形的印痕。
「那個,是有什麼不便之處嗎?」
隔著木製的櫃檯,也許是觀察到他細微的表情,女秘書從眼鏡背後關切地看向他。
「不,沒⋯⋯」
——砰!總務科的門突然被大力推開,門板撞到牆,又緩緩地退回去,生鏽的金屬合頁吱嘎作響。
「喲,我們的塔矢准名人!」
「倉田先生⋯⋯您就別開我玩笑了。」
來者是倉田厚十段,他是今年春天剛從緒方先生手中奪下這個頭銜的,近期狀態也很好;這二位還剛剛一起打入了三星火災盃的準決勝,看來對當下同儕競爭的氛圍十分上頭。
「哈哈哈,就是得這麼稱呼你,才能給緒方多一點壓力嘛。」
他好像心情很不錯,一邊說著一邊踱到櫃檯前,自來熟地在亮身邊站定,看向他手中的紙張。
「——九月,二十日,東京本院2F大堂的⋯⋯公開對局解說會,欸?怎麼這次的講解工作還是塔矢你喔?」大聲讀完,又嘟囔道:「這不一直都是塔矢嗎?再不然就是進藤,連和谷、伊角和冴木都輪到過。即使他們是年輕帥氣的小鮮肉⋯⋯咳咳,但你們可看清楚啊,」
不動聲色地把自己換到了亮的位置,倉田略顯熟練地從西裝的內側掏出一張摺疊整齊的紙,展開來拍在玻璃上。
是編輯部對九月號《圍棋世界》的讀者回執統計。
「我才是這個月的現役來信應援人氣top來著!」對著櫃檯後面的女性大聲道,「這週四的會場,該輪到我負責吧。」
工作人員看了看倉田,扶著眼鏡,皺著眉頭湊過去看倉田手裡的統計書。
雖然多少在意料之外,但簽字的筆跡和責任人印章確實沒有問題。
「⋯⋯既然老師願意的話,」
她端詳著亮的表情,見他點頭後,拿起筆準備重新為倉田寫一份邀請,又對亮說:「麻煩您把紙張放在旁邊的桌子上,一會兒我會拿去銷掉。」
「不用了,您先忙,我自己去就好。」
碎紙機就在一旁不遠處的桌前。看著紙在機器裡慢慢被切成細條,亮暗自鬆了一口氣。
太好了,能有更受歡迎的棋手受任普及活動的工作,自己也得空去赴約。
是啊,不僅有他,還有倉田老師、緒方先生、以及進藤等一眾後來居上的年輕同僚們——今年國際賽日本的成績比往年都要顯著,在大家的努力下,圍棋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
沒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九月二十日黃昏,微風裡昇起金色的雲。和進藤坐在墨田區一座商業中心高層的旋轉餐廳[2],城市的燈火在腳下從漸暗的天色裡浮出。儘管是法式料理的餐廳,裝潢卻以簡潔的木和石為主,用幾尊小瓷像點綴,菜品也並不過分華麗。
一切都很舒適,唯一讓亮有些不解的是圓桌中央一直溫暖地搖曳著的心形蠟燭、小花瓶裡的單枝玫瑰,以及餐前贈送的雞尾酒——
「這是我們為二位特調的『愛神』[3],希望二位喜歡。」
——像樹莓汁一樣的粉紅色,一顆草莓對半切開浮在上面。
「欸?啊,那個,謝謝⋯⋯」
連吸管都是彎成愛心的形狀的那種。進藤拈起來看了看,嘴角仿佛抽了下,透過微顫的燭光小心地瞥了亮一眼。
總之,用過頭盤和主菜,光還是一臉平靜地告知侍者可以上甜品。
年輕的女侍者很快端上一份紅絲絨和一份歌劇蛋糕,後者上面插了一支細的螺旋蠟燭,盤上用巧克力醬寫著「❤生日快樂~LOVE FOREVER❤」,四角畫了新古典風格的裝飾圖案。
她將這份放在了亮的面前。
「不好意思,今天並不是我過生日。」
亮抱歉地笑了笑。
「而且⋯⋯從剛才開始,就覺得有什麼事誤會了⋯⋯」
「啊啊。」光也看向她,「確實⋯⋯」
侍者的手停頓了一下,「失禮了,這就為二位重新做一份。」
「不用了,就這樣吧,沒關係。」
「啊,那麼請問關於『誤會』⋯⋯可否說得詳細一點?您對食物有什麼意見嗎?」
「不是的,菜品都很喜歡。不過,我們其實⋯⋯」亮望向燭火,又抬起頭看向女侍者。
「只是朋友。」
光的臉在明亮的火光後顯得模糊。
「朋友」。在遇到進藤之前,符合這個概念的人對於亮來說似乎只有蘆原先生。
他是父親門下最年輕的學生,他們之間沒有過多的禮節上的顧慮,也沒有對於對手的鬥爭心。長久以來,他便覺得「朋友」指的就是這種溫和、輕鬆的關係,於是有很長時間並沒有將進藤算在這個範圍內。
進藤光,到底算是他的什麼人?大概是從四年前的那時起,萌生了這個得不到答案的問題。
那是十七歲的十二月十四日,記得他們正好也約在棋會所下棋。
「喂——!進藤!你別太過分了!給我嘴皮子緊著點,今天可是我們小老師的生日!」
復盤時,北島從他們的爭執中站起來,自相鄰的棋桌指著進藤訓斥道。
被點名的少年一下轉過頭來,指向棋盤的手慢慢放下。
「欸?!真的嗎!我不知道欸。」他眨了眨眼,收起幾秒前氣勢洶洶的視線,疑惑地望向盤面另一側的對手。
「你怎麼從來沒和我說過?」
還沒從爭論中回過神,進藤責問的語氣讓他很不適應。
剛才向著黑子的進攻提出那種不紮實的「立二拆三」,也是一副理所應當的態度,好像錯的是沒有這麼想的自己一樣。
生日又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每年都能過,沒有義務說與他聽。況且難道會因為是生日就改變對他人、對圍棋的態度?無法理解。
「哼,一定要把所有的事都和你說嗎?」亮抱著雙臂向後靠上椅背,笑了出來,「感興趣的話,棋院公式站上都有寫,每位現役棋手的履歷和通訊方式。」
「哈?每天見面欸我們,為什麼還要特意上網檢索你,又不會找你談工作——你當我是跟蹤狂啊?」
進藤突然撐著桌子湊得很近,盯著他的眼睛。
「還是說你其實一直把我當成毫無關係的他人?我對你來說還不如會上網查你資料的粉絲?是嗎,眾星捧月的塔矢少爺?」
亮保持著相同的姿勢,只是直直地看著他。
凝固的沈默向四周蔓延。
光坐回椅子上。「吶,你說,我們是朋友吧?」
「朋友」——驀地意識到,自己的頭腦裡對這個詞的概念近乎空白。
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出現在他的生命裡,曾讓他感到極端的震撼、失望,又使他重新認可。而目前看似平靜的相處下,藏著至今未解的疑團。如此擅自擾亂自己生活的人⋯⋯
他嘆了口氣,皺起眉,「進藤,你自然不是與我毫無關係。但,希望你搞清楚,我們從來都是對手。不是『朋友』,也不可能是。」
「好,這可是你說的。」
光面無表情地起身,披上外套,走到前台拿了包離開。
在四周低微的議論聲裡,亮抬手,憑著肌肉記憶收拾起棋子。
——四年前,他曾否認「朋友」的關係。那天進藤走後,他一直獨自打譜,直到晚飯時間。
而如今誰也沒有過多苛責餐廳的這次「失誤」,也默契地沒有再提這段插曲。
「抱歉,客人,好像支付沒有成功呢。」女侍者從前台折回來,將卡恭敬地還給進藤。
對面的人小聲嘀咕,「糟了,一定是訂圍棋月刊的時候——」
「你有給卡設限額喔?」
新晉的本因坊,獎金自然不可能這麼快就用完。亮拿出自己的信用卡,自然地遞過去。
「嗯,因為一換季就會忍不住想買東西。」進藤低頭把卡收回,眼神飄向桌上的花,「雖然現在能自力更生,但一直花那麼多錢肯定不太好嘛,就去申請了每個月五十萬的支付限額⋯⋯」
「五十萬?這個月已經花完了?」
「嗯⋯⋯對。」
「又買了不必要的很貴的東西?」
亮挑著眉調侃,看著進藤一副被說中的樣子垂頭喪氣地靠回椅子裡。
有些可愛。
反正也不是第一天見識到這個人的消費習慣了。
「——我回來了。」
那次由「朋友」引發的矛盾之後,十七歲生日的晚上,亮推開家門,回應他的只有房子裡空蕩蕩的迴音。
他花了點時間整理這天從市河小姐、蘆原先生和其他長輩那裡收到的禮物。母親在這時打來了長途電話。
「小亮,今天怎麼樣?還是在棋會所和進藤君下棋了嗎?」
母親對於生日當天將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好像過意不去,在講了和父親在中國的近況之後,還噓寒問暖地說了很多。
而關於那個人,他想和平時一樣回答,話到嘴邊卻又停住。
「——啊啦,又吵架了?」
「沒有。」太幼稚了,怎麼可能浪費時間和這種人吵架。
母親也沒有追問,聊了亮近期的比賽和一些棋會所的新聞,再次祝他生日快樂之後,就互道晚安。
除了母親和長輩們的問候之外,亮對生日沒有多少實感,只覺得和一年裡其餘的日子沒什麼兩樣。進藤這麼在意生日,只是二人觀念上的不同。
他將禮物全部收好,關了客廳的燈,準備去洗澡。衣物從皮膚上剝離,微涼的空氣使他的思路變得清晰。
——等等,難道這種觀念上的衝突,算是「吵架」嗎?
沖完涼泡澡時,亮靠在檜木浴缸裡想著,手指下意識地捲著留長的鬢髮。
不就是「朋友」嗎,也不是很大不了的事情,他如果覺得是,那就是好了。甚至說了「今後也不可能是」,把話說這麼絕,進藤看起來是真的生氣了。
可心裡明白那種親密的定義終究不適合他們。
到底如何才能和他回到單純的「對手」的關係呢?
「——哐、哐!」
⋯⋯什麼時候睡著的?水已經溫涼。亮揉了揉眼睛,逐漸聽清了浴室外的敲擊聲。有人在很用力地拍門。
已經八點半了;匆忙地擦了一把頭髮、套上睡衣,跑過廚房的時候看了一眼時鐘。
硬挑這種時間來拜訪,多少能想到是誰。
「你來幹什麼?」
光立在門外,運動過後氣還沒喘勻,一動不動地望向他,院子裡石燈籠柔和的光線灑在他臉上——好像有些红。
亮上下打量了一眼,進藤斜挎著書包,背上一個近似棋盤大小的蛇皮袋,裡面裝了什麼四方的東西,旁邊單車的車把上還掛著三個滿滿的網兜。簡直像逃難來的⋯⋯地震了嗎?
十二月的風從門口吹進來,濕的頭髮貼在脖子上,水滴像蛇一樣爬到衣領裡。
「趕緊把門關上。」亮轉身向屋內,「什麼時間了,拍門拍得這麼大聲,知不知道會吵到別人?你是第一次來嗎,有門鈴不會按?」
「——啊,我忘了。」進藤這才把身上和車上的行李卸下來,進屋關了門。
「話說現在才八點多欸,你怎麼已經換睡衣了,這麼早準備睡覺㖃?」
又和他有關係了?
沒有完全從下午的爭吵消氣,亮抱起雙臂,視線指向地上的一堆袋子。
「這是什麼?」
「嗯⋯⋯是火鍋。」
「火鍋?」用質詢的眼神盯著他。平時每天中午強迫自己跟他吃飯還不夠,現在怎麼連晚飯都要管。
「火鍋的『鍋』啦。」進藤蹲下來把箱子打開,掏出一個巨大的⋯⋯容器。
「就是這個。跑了半個池袋才買到,也不是每個中華超市都有。」
亮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反應。這個銅製的東西兩側有馬鐙一樣的把手,下面是很高的底座,中間還有一根煙囪,整個看著像一頂帽子。
「唉,還不是夏休的時候去北京找和谷和伊角學長玩,啊,我和你說過吧,他們今年在中國棋院進修。結果那兩個不講義氣的,不盡地主之誼好好招待我,我去的時候他們居然還在⋯⋯吵架!」
進藤端著那口鍋穿過走廊,用腳推開客廳的木質障子,「後來我跟楊海先生聊了,他那天晚上就帶我們去吃中國的火鍋欸!
「是很像壽喜鍋的,一種在特定的湯裡煮食材的鍋料理,於是他們就和好了。
「嘿咻——伊角學長還喝了很多,從沒見過他這麼高興的樣子,太神奇了。楊海先生說了喔,這是『中華的熱度』,消弭一切隔閡與紛爭。」
即使聽上去疑點重重⋯⋯
「總之!」他興奮地轉頭朝立在門口的亮笑道,「想你也沒好好吃晚飯吧。來吃!」
他們就這樣莫名地在星期天的晚上,塔矢家的和風老宅裡,就著榻榻米和暖桌打邊爐。湯裡逐漸鑽出氣泡,進藤從帶來的東西裡取出各種醬料和調味品,在矮桌上擺了一排。
會留很大的味道嗎⋯⋯雖然有這樣的顧慮,但骨湯的香氣慢慢擴散在空氣裡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確實是餓了。
「這是什麼?」
他看著進藤從廚房端出來的盤子裡一團毛絨絨的像布料的東西。
「是牛的胃。」
呃⋯⋯還是不要問了。
「怎麼,不敢吃?」
「當然沒有。你知道餐具都放在哪裡吧;記得拿我的筷子。」
其實放進鍋裡煮了之後,也沒有想像中的奇怪味道。
不知是由於食物的熱氣還是吃飯這件事情本身,他心裡似乎變得輕鬆起來。
「你家晚上好安靜啊。」身側傳來自言自語的聲音。
鍋在咕嘟咕嘟,火在噼哩噼哩,還有個人一直不停在耳邊說話,到底哪裡安靜了。
「我們來看看電視!」
「吃飯,看什麼電視。」
「就是吃飯的時候才應該看電視吧,常識來說。」
只是你的常識吧;算了。
「那我要看圍棋節目。」
「啊哈哈哈哈,還圍棋節目咧?現在都幾點了,最好是有圍棋節目啦!喔喔喔,這是那個很火的漢字王綜藝嘛。看娛樂節目也能學到不少東西的——你看,這個词你就不會念吧?」
「不是『亜爾然丁』[4]嗎。」
「⋯⋯哇,還真是。『阿根廷』的漢字居然是這麼寫的!
「——你又怎麼會知道啊?」光一臉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伸向火鍋的筷子頓在半空。
哼,贏了。
亮得意地瞥了他一眼,從沸騰的湯裡夾起光放的魚板放進嘴裡。
映像管組成的繽紛的畫面在進藤臉上閃爍,他的笑聲和節目裡人們歡快的語調相互唱和。
或許是靠著暖桌,又吃了很多熱的東西,身體也暖和起來,視野裡籠罩著一片蒸騰的白霧。感覺意識也跟著變得輕飄飄的。
「哇啊啊啊啊——!」
白霧突然被進藤的慘叫沖散;亮捂起耳朵。
這個人嗓門真的很大。
「怎麼了?」
「唔,想讓火小一點的,被鍋燙到了,沒事。」
「什麼沒事,給我看!」
拽過他的右手仔細端詳,似乎確實沒有任何發紅或者起水泡的跡象,還好。
這雙手相比自己剛認識的時候已經修長硬朗了很多,明明五年前還肉乎乎的,也沒有厚厚的棋繭。
原來每天跟自己下棋的進藤,他的手握起來是這樣的感覺。
很溫暖,很有安全感⋯⋯
「好了啦,怎麼看得這麼入迷。」光移開視線,撇了撇嘴,卻也沒有把手抽回去。「橫豎是在想我會不會被鍋燙了一下就不能和你下棋了,真是圍棋怪人⋯⋯欸唷!幹嘛打我!」
「閉嘴。」
還有時間說閒話,看來是不要緊。
「⋯⋯今天,都說了不是朋友了,幹嘛還做這種多餘的事。」他聽見自己輕聲說。
進藤愣了一下;似乎是「多餘的事」做得太多,不知他指哪一件。
「勁敵的生日,很重要啊。絕對不能放你和別人過。
「看你下午那副鐵石心腸的表情,誰知道會不會一回家就找什麼更親密的人訴苦。我可是你的對手欸,唯獨這個位置,我不會讓出去的。」
——是「對手」?沒再說是「朋友」?
聽上去更針鋒相對,可「維持現狀」的暗示,讓他感到安心。
「哼,那你就多把腦子放在圍棋上一點。」
說來,這人總是不務正業⋯⋯
愛看什麼「漢字王」,卻連「阿根廷」都不認得。日語大概也不太好。什麼叫「不能放我和別人過」,關他什麼事;況且哪裡又有「別人」。
就連行為舉止都不像同他一國的——不就是想和好嗎,居然誇張到去中國人的超市買這種東西。這個鍋,很重的吧。他一路扛著這麼一堆東西騎車?從池袋到自己家?看見的人會怎麼想啊⋯⋯以一般人的羞恥心,能有這種舉動嗎。
不是朋友的話,完全不懂為什麼會做到這種地步⋯⋯
在光深不見底的胃袋的容納下,切的一整桌菜終於吃完了。
亮看著杵在和室中心的違和的大東西。
「所以,這個鍋要怎麼辦?」
「不知道欸——還挺貴的,扔掉好可惜喔。而且那個超市的老伯好像不怎麼繳稅欸。一萬五千塊,我付的時候說是只能用現金。」進藤皺著眉抓了抓頭髮,側頭看著亮,「唔,要不我明天帶去捐給明子阿姨做義工的教會學校吧?」
零點剛過,塔矢亮,在嶄新的十七歲,再一次放棄了理解進藤光的腦迴路。
嘖,一萬五千塊。買了個,一次性的鍋。
「——所以說真的,這個定價會不會太貴了啊[5]。」進藤懊惱地小聲抱怨。
「嗯?」
亮忽然回過神。他們剛走出旋轉餐廳不久,一起在錦糸町的商店街閒逛。
九月潮濕的晚風和煙火氣撥亂他的頭髮。
「沒什麼,只是想起剛才⋯⋯明明是我過生日,剛才還讓你幫忙付賬。抱歉,都是因為這個月買了太多的⋯⋯雜誌。」
「雜誌?還是關於衣服的那種?」
記得光住的地方甚至有一整面牆的書櫃用於安置買來的時尚刊物——這個人對「潮流」的追求有時候真的很誇張。
「唔?不是啦⋯⋯」光左顧右盼,忽然朝向一處,有些生硬地轉移了話題,「話說那裡有『橡子共和國』[6]欸,去看看?」
周邊商店裡充滿一種柔軟的香氣,暖色的燈灑在光的眼睛裡。
「吶吶,你知道吉卜力的動畫電影吧?」
「聽說過。」
「但是沒看過?」
「嗯。」
那樣的世界雖然美好,但離他太遠了,像天邊金色的雲。這些公仔和印刷品上的形象,他只覺得眼熟,也叫不上名字。
「哈哈哈,我就猜到。」說著,光拿起一個戴面具的圓滾滾的玩偶舉到他面前,「你看你看,這個『無臉男』,像不像桑原老師?」
「噗——」可惡,真的有點像。「快放回去!」亮一邊憋著笑一邊說,「不許說這種話,要尊重桑原前本因坊。」
「哈哈哈哈哈,是、是。」
光回頭將玩偶放回去,再轉過身的時候,意外地,兩人的臉忽然靠得很近。
周圍有柔和的雪松的味道,散發著麝香的辛辣溫度。是香水嗎?[7]
模糊的餘光裡,看到他的喉結滾動了一下;亮抬起眼,視線滑過青年下頜明晰的線條、緊抿的嘴唇、秀氣的鼻樑,撞進他琥珀色的眼中。睫毛顫了一下,目光閃躲開,又忍不住對視。
臉上變得很熱。
這種氣氛下,難道要——
突然,光轉身跑到遠處的牆邊,那裡有個很大的長著長耳朵的玩偶。
「——吶、吶!話說這裡還有那個超有名的——龍貓!你知道吧?在哪兒呢?」自顧自作出張望的樣子。「聽說只有心靈純潔的人才能看見欸,塔矢,你看得見嗎?幫我找找?」
就是那個吧,當然看得見啊喂。
總覺得有點生氣?
「進藤!你快別搗亂了——」
⋯⋯笨蛋,有必要這麼害羞嗎。
如果那天二人之中有誰藉著機會捅破這層窗戶紙,不知道現在又會是怎樣的光景呢。
忽然覺得自己回憶中的愉悅像一座孤島。旁邊除了一下一下落子的聲音之外什麼都沒有。
亮轉頭去看廣瀨先生。他的鏡片反著白光,顯得眼睛更沒有神采,一動不動地坐著,只有一隻手機械地擺著棋子。
總覺得他狀態很不好,讓人有些擔心。
「廣瀨先生。」
沒有回應。
「那個⋯⋯廣瀨先生?」
「啊。」對方抬起頭,用帶笑的聲音答,「什麼事,小老師?」
「也沒有,只是很少見到您一個人在這裡下棋。北島先生還沒有來嗎?」
「⋯⋯啊,他之前⋯⋯不,他提前回去了。說起來,」廣瀨先生突然坐直了一些,開始收棋子,「抱歉,時間不早,我也該走了。明天再見。」
「這樣啊。那麼明天見。」
廣瀨先生⋯⋯大概是有什麼事吧?
看他走得很急,險些要撞到桌角,腳步噠噠地響。桌上還放著未喝完的半杯茶。
就在廣瀨一腳邁出棋會所時,亮聽見門外傳來進藤爽朗的聲音,「嘿,廣瀨先生——啊!」隨後像是被什麼撞到,他的腳步頓了一下。
自動門的輪子開始在軌道上滾動。
「進藤君!你來了。」
「市河小姐。」進藤聽起來仍然是騎單車來的,講話時喘氣聲有些重。
「他怎麼了嗎?」
「嗯⋯⋯沒事,是因為北島先生,好像不在呢。」
兩人又輕聲聊了幾句,話語與外衣摩擦的聲音重疊。有兩三個熟客向進藤問好。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能坐在這裡一起下棋了。從相互追逐的目標到彼此認可的對手,亮說不清如今的他和進藤該稱為朋友、勁敵還是什麼別的關係。
逐漸開始希望他們之間不僅僅有棋,甚至期待著能發生一些超出同僚與密友身分的事,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今天是自己二十一歲的生日,姑且就允許自己有這樣的心情吧?
適才充滿著他腦海的人像是透過屏風看到他一樣徑直走過來,他趕緊抿起嘴,壓了壓上揚的唇角。市河小姐端來兩人的茶,轉身收走了廣瀨先生的茶杯。
光熟練地將屏風拉開一條縫,鑽進來,又反手拉回去。今天他穿了一件沒見過的白色衛衣,胸口有一塊淡藍紫色的方形刺繡徽章,讓他想起雨後的野花叢。
進藤家的衣櫃一直是個謎,很難用常見的標籤概括他著裝的風格,而更像是他自身的氣質決定著衣服穿在他身上的效果。
「塔矢,生日快樂!」光「唰」地在他對面坐下。
「謝謝你,進藤。來下吧?」
「啊啊。」
他們如常開始對弈;這幾年裡,各自都變得沈穩和自如了許多,十七歲時因為是不是朋友的那幾句不實用的話就吵得人盡皆知的衝動已經很少以這樣直接的方式出現。
亮用自己的棋感受著進藤的變化,在進藤低頭思索應手的時候抬眼看向他。
即使過了很多年,他仍偶爾記起他們時隔兩年零四個月的,職業生涯內的第一次交鋒——平成十三年[8]十月的名人戰一次預選一回賽。
那時的進藤,和他留下的那句,「是你的話,或許總有一天能告訴你吧。」
棋會所裡看不到天光,三五杯茶下去,總覺得時間還是靜止的。亮抬頭,時鐘的指針指向了四點,遠處有幾個人陸續起身離開。
「呼,」進藤深吸一口氣,低下頭說,「我認輸了。」
「多謝指教。」
亮抬手將白子攏過來,棋子相碰的聲音在四面圍起的狹小空間裡輕輕迴響。
指節不小心碰到進藤的手。對方將自己那側的白子推給他;微涼的蛤棋石的溫潤觸感融化在手心裡。
於是亮看向他,「要復盤嗎?」
光沈默了一秒。
「不了。」
「怎麼了?」
「那個,其實今天有很想給你看的東西。」
「是什麼?」
「我想帶你去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進藤不是第一次說類似的話,帶他去自己常去的喫茶店、喜歡的店鋪、某條有趣的街道。
只是這次的語氣聽起來並不一樣。
他回望那雙熟悉的琥珀色的眼睛,像深秋等待著第一片落葉的湖。
光似乎是準備了很久,將許多的思緒都寄託在了短短的一句話裡。
走出棋會所時,過冷的風吹得皮膚緊繃,使得胸口也莫名的難受,亮皺起眉。在人來人往的人群裡,進藤一下子拉住他的手腕。
今天到底是怎麼了?剛才在市河小姐那裡取衣帽和包時也是突然伸手幫他整理了圍巾,還主動接過包遞給他。
不是說感到冒犯或者覺得不妥,但兩個以同事、朋友相稱的成年男子在街上拉著手走在一起,多少會有些⋯⋯而且是錯覺嗎?他用餘光瞥了眼身邊人的側臉。甫一出門進藤似乎就一直有什麼顧慮,像用一層厚厚的硬殼把自己層層裹住⋯⋯
這樣的他,有些陌生。
「——請等一等,名人!」
突然,一個聲音從身側步道的一端傳來。有一個穿著淺灰色西裝的年輕男人擠過人群,鮮紅的領帶被扯鬆了一些。
「請問是、是塔矢名人嗎!」
進藤抓著他手腕的力氣突然大了一些,用半個身子擋在他前面。
「啊⋯⋯進藤本因坊也在!」
他們也都算是半個公眾人物,因此這樣的場景並不鮮見,大概率只是溫和的棋迷吧。
「您好。」亮禮貌地笑道,「請問有什麼事嗎?」
「那個,路上忽然遇到本人真的太興奮了,就出聲叫住了您。實在很抱歉,希望沒有耽誤⋯⋯」
青年還沒平復呼吸,說得很快,手指揪自己的衣襬和袖口。
「啊,那個,簽名板,簽名板⋯⋯」他一邊嘀咕著,從擦得鋥亮的公文包裡抽出一張空白的色紙和一支黑色水性筆,「可以請二位為我簽個名嗎?」
「當然。」亮流利地接過筆,簽好後又將紙筆遞給進藤。
「⋯⋯我、我是中學時第一次在新聞上看到您和一柳棋聖的對局的,是第57期本因坊循環賽的第四戰,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當時就對圍棋產生了很大的興趣,高中還加入了學校的圍棋社,參加了一些業餘的學生比賽⋯⋯」
棋迷自顧自地說著。
「後來上了大學,空閒的時間越來越少,就逐漸荒廢了,工作後才重新開始下棋,差不多是一天裡最快樂的事⋯⋯總之,您是我的偶像,是我最敬佩的人!所以!」
他越說越激動,終於喘了口氣。
「本來年前天元戰的最後一場期待您能挑戰成功,沒想到會在最後關頭突然告假。
「第二天報紙標題都寫『不戰敗』,是您職業生涯前所未有的情況。
「那時我特別擔心⋯⋯」
「欸?」
耳邊有什麼聲音突然停住了,是進藤手中的筆。
「不戰敗」是⋯⋯什麼意思?
「喂,」他聽到進藤很用力地說,字句像是從唇齒間擠出來的,「別說了——」
「啊?」
激昂的熱情突然被打斷,年輕人看了進藤光一眼,可能被他的眼神和話語間的狠意嚇到,終究是忌憚壓過了被冒犯的不快。
「總、總之⋯⋯現在看到您精神這麼好,就放心了!本年度新的賽季,我會繼續為您加油的!」
今天是⋯⋯平成十九年,二〇〇七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吧。
這個人為什麼已經提到了年後的事?
第33期天元戰的最後一場,他和緒方先生的對局,應該是下週四才對,不是嗎?
恍惚間,想給自己的視線找一個焦點,於是抬頭去看眼前的人。
「進藤⋯⋯」
亮聽見自己微弱的聲音從頭顱裡飄出來。
「今天是,哪天?」
光的視線從那人身上移開,對著亮搖搖頭,換上幾乎與平時無異的表情,笑起來:
「想什麼呢,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還要送你禮物不是嗎?」
亮看著他將紙筆丟給愣在原地的年輕人,跨了一步,扶上自己的肩膀,說話聲壓得很低。
進藤是很不擅長偽裝的人。
可他為什麼,要欺騙自己?難道⋯⋯
像是胃裡有什麼東西開始翻騰,有一個空洞在那裡越擴越大,擠壓著他的呼吸。
不。不對。一定是,有哪裡,搞錯了⋯⋯
亮看進光的眼底,他知道他們在對視,頭腦卻一片空白,他讀不出進藤眼中的任何情緒,哪怕那是最明顯的笑意。
手腳發涼,視覺脫離了感官,聽覺逐漸被一種尖銳的轟鳴取代;四周的一切忽然被推得很遠,又在下一刻海嘯般吞沒了他,可他觸碰不到,像被關入搖晃的沙漏——
要出去。
後退著,他用力掙開了進藤的手。
他要出去!
他一定是忘了什麼很重要的事,卻無法為這種無端的失去感找到任何現實的依據。
沒有出口。巨大的恐懼壓迫著他,他想逃,衝過了鬧市區沸騰的馬路,信號燈的紅在餘光中融化。奔跑間,似乎看見了某種可以抓住的影子,可那段距離又永遠無法跨過。尖銳的、憤怒的嘶鳴,擦過身後的機動車手煞的聲音,輪胎與柏油路劇烈地摩擦。
進藤在身後追趕,呼喊著他的名字,頭腦接收到了熟悉的信號,卻無法做出任何回應。
等亮的意識回到身體裡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正站在新宿站的東南口,盯著滾動屏幕上刺眼的時間。
今天,是二〇〇八年的一月二十九日 。
tbc.
[1] 原作中沒有給出廣瀨先生的名字,此處為二創。
[2] 過幾年要建天空樹的地方。寫大綱的時候是想寫他們在天空樹的法國餐廳用燭光晚餐來著,但寫到正文慢慢考據才發現2007年的時候天空樹都還沒建,但原址似乎也是個mall,就這麼改動了一下。
[3] 日語為「エロス」,以Cosmopolitan的配方為基底。
[4] 音「アルゼンチン」。
[5] 二〇〇七年《圍棋世界》的零售價为860円每本。
[6] 吉卜力的官周商店,主打ip是《龍貓》。
[7] 藉機推薦棋魂的官周香水。光的後調是雪松、琥珀和麝香。
[8] 西曆二〇〇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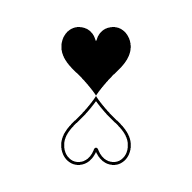
买了很多不必要的很贵的东西……比如围棋月刊什么的^ – ^这么拐弯抹角地制造和暗恋对象出去吃饭的机会,真的很可爱啊光~
而且“火锅”居然是铜锅涮肉的那种锅吗,光准备得也太本格太周到了,这都能让你买到,很神奇吧,池袋……
这一章真很像是为亮制造的一个Fake World Wonderland,被美丽的、没有尽头的世界所欺骗着活下去……但是果然亮是不会接受的啊——这点也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