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給即將到來的夏天摸了個短篇小故事,本來應該跟在「ぼやけた色に真夏の湿った夜」(蒙矓的顏色裡仲夏的喧濕之夜)目錄的最後,但,由於夏季的正篇還沒搞好,就先吐這個給大家吃吃!(正文未到番外先行渠講)(反正番外基本是可以獨立成章跟正文沒有劇情上的直接聯繫的,就像「睦月」跟「春」的關係一樣(。
*本文寫的是2009年二十二歲的光亮(及其親友)。
无奖竞猜:您猜这次有没有肉!
列車開出去四分鐘,慢條斯理的廣播終於結束,對於車裏酸澀的消毒水味習慣得差不多,身上的汗也快要被冷氣吹乾了——和谷義高叉著腿坐在第一排座椅靠過道的位置。早上八點半的太陽很快被灰色的隔音板擋住,不到半分鐘又重新從灰色的樓房窗戶上反射過來。他聽見塔矢亮沈默著「嘩」一下將遮光板拽下一半;身後也發出了相似的聲音,奈瀨輕輕說了句:「這樣就好啦。」然後繼續和藤崎明有一搭沒一搭地小聲聊天,聽不清在說什麼,偶爾會突然笑起來,又像燒開的水壺一樣憋回去。社和越智在過道另一側的雙排座位上——社今年四月剛剛正式轉入東京本院,好說歹說,飯友又多了一個——他們看起來聊得很開心,是說社支著腦袋望著窗外面無表情地講個不停,越智則半瞇著眼睛,一副完全不想聽的樣子。
週六早上的新幹線沒有很多人,他們後面的一兩排甚至有空位。細碎的談話聲混入電車行駛的噪音之後,耳邊就顯得格外安靜。和谷一手捏著手機和後排的伊角聯機下黑白棋,另一隻手搓著背包裡瓶裝綠茶的蓋子。伊角在準備竜星戰,賽程和他只相差幾天,倉田先生也有參加。而他自己一週多前剛以不大的優勢從阿含·桐山盃二回戰勝出,連假之後不到三週又是準決勝,森下老師的期望也随之高涨,雖然是件好事,但他果然還是需要偶爾從圍棋裡出來一下。
進藤光坐在他旁邊;他感覺到進藤在瞥他的手機屏幕。這個邀請他們去他鄉下外婆家合宿三天的傢伙從坐下來到現在基本上一句話都沒說。和谷抓了抓頭髮使它們立起來一點,好讓冷風從中間吹過去,用餘光觀察著左側這兩個不省油的燈。塔矢正看著窗外,從窗戶上的倒影看得見他的眼睛,那眼神,簡直能把玻璃瞪出洞來;而進藤的視線在塔矢、他的手機屏幕和腳下的地毯之間來回移動。搞什麼,放假第一天早上就愁眉苦臉的——他忽然開始羨慕因為有別的約而不能來的福井;早知道要連續三天對著這兩個又不知鬧了什麼彆扭的人,他还不如滾回去打三天遊戲。
雖然近年也見他們鬧過不少次矛盾了。有時会吵得很兇;外化為塔矢下棋的時候一身肅殺之氣,進藤走路的姿勢像是要去打人,早到一小時就為了不用和對方在棋院門口遇見,多爬一層樓都不願在同一個自動販賣機前排隊——彷彿回到了互相賭氣的中學時代。而即使沒有在吵架,塔矢對進藤發火也是經常的事;在旁人看來確實是維持著純粹的「勁敵」的關係,也只有從院生時代就認識進藤、聽過他倆風言風語的同輩好友會明晰棋院雙子星的私交——記得有次手合前在對局室外與同事聊起近期的棋賽,村上信一七段順著塔矢的話說了進藤幾句不好,卻被反唇相譏狠狠地嘲了一頓。望著塔矢亮遠去的背影,有熱心的同事拍了拍村上這個倒霉蛋的肩膀:「哎,看你不了解塔矢,進藤可是他的地雷,他們倆的關係那叫一個水深火熱。」和谷聽著,在心裡翻了個白眼——什麼「水深火熱」,說個小孩都懂的道理,這叫做「疏不間親」。
其實原本他和塔矢也沒有多深的交情,對他的印象僅止於「目中無人」、「有點不近人情」。他不知道進藤光這兩年為什麼總是帶著塔矢參加他們親友之間的聚會,更不曉得看起來也沒那麼情願的塔矢怎麼就同意了。不過這樣一來二去,他倒是逐漸覺得塔矢也沒有表面上那麼難以相處,甚至大多時候還挺好說話,待人接物也有夠周到,說到底還是家世背景的緣故?參加他家的研討會之類與圍棋相關的場面倒沒什麼,只是偶爾一起玩的時候會真切地體察到這種違和⋯⋯比如上次在進藤家轟趴時一起喊了披薩的外送,吃著吃著卻見進藤突然起身:「我去拿雙筷子。」塔矢則說:「啊,我想要叉子。」——姑且忽略這居家氛圍的對話為何進行得如此自然而流暢;那什麼,普通來說達美樂的瑪格麗特披薩會需要用叉子吃嗎?它值得讓洗碗機多洗一個叉?認真的?這就是當今日本腐朽的上流社會嗎?
說起來,塔矢亮這個人,棋下得好也就算了,偏偏還長了這麼張臉——只可惜如今這張臉映在窗戶上的表情還真不怎么好看⋯⋯
他忽然覺得座椅靠背被誰推了一下。
「⋯⋯怎麼了,和谷?」伊角說著,從椅子後面探出頭來,「你都pass三手了。」
「欸?啊,抱歉。」和谷趕緊低頭把快要休眠了的屏幕點開,落下一子。
——殴,該死,下錯位置了。
「⋯⋯還以為你有什麼戰術,」伊角在背後幽幽地說,「原來沒有啊。吶,能在黑白棋上贏你可真少見。」說著,不客氣地占了角落的一格。
——天殺的!進藤光,都怪你。
而一旁的始作俑者們仍是那副各懷心事的彆扭樣。
不過看伊角的樣子彷彿完全沒留意到這點,奈瀨和藤崎自上車起就聊得沒停過,更不用說過道另一側的越智和社了——秉承著一柳門下的內卷作風,二位正全神貫注地對棋聖戰的A組循環賽進行復盤。
——所以只有他一個人在風暴中心承受這莫名其妙的可怕低壓嗎?
和谷看著屏幕中間重新出現的兩黑兩白四個棋子,無聲地嘆氣,拎出包裏的綠茶使勁悶了幾大口,心下為這三日充滿了未知的田舍之旅感到無盡的擔憂。
進藤光將視線從眼前灰色的車箱擋板上移開,上面印的那些白色小字的注意事項隨著車廂晃來晃去,讓他覺得心煩。他嘆了口氣,左右瞟了瞟,索性閉上眼睛。
這種狀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果然還是一週前的那個晚上吧。
上週六做晚餐時聽著電視裡岐阜下吕溫泉的旅遊宣傳,他突然有了在三日連休時組織合宿的主意,正好也有一段時間沒去看外婆了。外婆一個人住在愛知縣靠海不遠的鄉下,接到光的電話時聽他想要帶朋友來玩,只說:「那可得把院子好好佈置才行。」——他記得外婆屋前的那片小院,小時候放暑假回去玩,總愛在那裡待上一整天,躲在已經採收過的草莓地裡只露出腦袋,就像全身都泡在了清涼的香氣中;七月花期的番茄隨手摘了用涼水沖一下就可以吃,酸甜的汁在口腔裡「呲」一下炸開;晚上在露台鋪上一張竹席一條毛巾被,聞著鹹鹹的海風和微苦的薰香入眠,翌日四點多爬起來去看野海灘上的日出,商陸的枝頭墜下一串串黑珍珠一樣的漿果,回來時還會看到架子上沾著露珠的牽牛花。
剛給朋友們打完一圈電話,隨即聽到亮的聲音從門口傳來:「我回來了」。
「辛苦啦。」光把食物從廚房端出來,順勢撐著桌子說:「下週末準備跟大家一起合宿喔,去我蒲郡的外婆家。」
亮洗過手,正準備上樓淋浴。「⋯⋯嗯。」
「喔對了,」光突然跟著跑上兩截樓梯,扒著扶手說,「那幾天鄉下還會有花火大會,這兩天你什麼時候有空?一起去買浴衣吧。」
亮已經走到樓梯口,有些疑惑地回頭看著他,樓上還沒開燈,窗外的夕陽灑在他半側身子上,「浴衣我有很多件,而且最近日程排得有點緊,要不你自己去?」停了一下,又補充道:「還有什麼想買的都隨你,要去表參道Hills的話刷我的卡就好。」
——等等,才不是這個意思!就是因為你有太多絹質的「上等」浴衣才要去買一件棉的吧——想起五月神田祭那天,傍晚一起逛到了明神前鳥居,剛好夜間廟會開場的煙花正在預熱。當時,他站在亮身後,那層高級的、柔軟的布料攜雨季潮濕的微風交纏著包裹在亮身上,從他的視角,飄動的長髮下的後頸、脊柱淺淺的凹陷、甚至連角帶圈住的後腰和臀部的曲線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偏偏本人還毫無自覺,自顧自地抬頭觀賞煙火,又轉過頭對他微笑,手裡的團扇有意無意地遮住半邊領口,輕聲問:「怎麼了?」
——但要怎麼講自己是不想再讓別人看見他穿那種衣服的樣子啊?難以啟齒的細微處的綺思,說出來的下場只能是被罵:「別開玩笑了」、「進藤光!」、「你腦子裡成天都在想什麼」。
亮看著他像是還要說什麼,卻又只是緊閉著嘴神色複雜地盯著自己,等了一會兒便要轉身去浴室。
「那個,還是稍微騰出一點時間,只是去買衣服啦!」
「為什麼?不可以自己去嗎?」
「我——不是、總之你一定要去!」
「明知道這週工作很多,為什麼非要去逛街?理由呢?」
「因為——就是、因為⋯⋯」因為你太色太容易引狼了!這樣說會不會被打一頓?
「⋯⋯幼稚。」亮扔下一句,轉身走去浴室。
「喂喂,說誰幼稚,是你太天然了吧?連這種事都——」
而在他回過神來的時候,唇槍舌劍的戰況已經超出了可控的範圍。當晚,亮便一氣之下收拾了最基本的用品住回了自己家。塔矢夫婦沒在日本,卻是緒方先生不知從哪知道了這件事,沒過兩天在棋院四樓的休息室撞上,見他端著茶老神在在地對自己笑:「進藤,『純情房東俏房客』的劇本不好演吧,啊哈哈哈⋯⋯」——什麼鬼。不過是他的錯覺嗎,這人講話是不是越來越像桑原老師了?
直到昨晚為止,一方面由於棋院節假前的例行用工強度,另一方面也因為兩個人還在冷戰,彼此竟是一封郵件也沒有發過,更不要說通電話和見面了。週五回到家吃晚飯的時候,還沒有收到亮的任何消息。光打了半個鐘頭的腹稿,一邊洗著盤子一邊又排練了幾遍,終於鼓起全身的勇氣撥通了塔矢邸的座機——並沒有人接。不在家嗎?可他今天的日程應該是下午就結束了才對。雖然不是沒料到這種結果,但是想著亮一週之後還是不願意和自己講話,光只覺得很後悔。他是真的生氣了啊⋯⋯
「嘀——」
聽到語音信箱開啟的提示,光才反應過來,趕忙說:「喂,是塔矢家嗎——我是說,那個⋯⋯亮,明天去我外婆家的事還記得吧?跟他們說好了早上八點集合,品川站發車,記得定個鬧鐘,別起不來了——啊我在說什麼呢,你要來的話肯定不會忘也不會遲到的,畢竟是你嘛⋯⋯我是說,如果你還想來的話⋯⋯就這樣,那晚安,明、明天見——」
他幾乎是把聽筒拍回座機上——剛才從自己嘴裡蹦出來的都啥,連日語都不是吧啊!而且完全沒有表明任何要和好的意思,只會讓亮更加生氣不是嗎,如果他直接不來了可怎麼辦⋯⋯
於是今天早上,進藤光七點就到了車站。早早地站在檢票口,才覺得即使自己像個傻子一樣提早到了一個小時,可亮如果真的不願來還是不會出現,而他就算出現了,也不會因為自己而提早到——所以這到底是在幹嘛?
「嗯,失禮了,請問——」
光意識到有人在對他講話。
「我們想要去熱海,」回過神來,發現眼前搭話的是個金髮的白人女孩,卻意外地說著一口流利的日語,她戴著棒球帽,背了一個大包,穿著很簡單的背心和短褲,手裡拿著一張地圖;身邊站著另一個同樣是金髮的姑娘,「請問是在這個站坐車嗎?」
「啊,熱海的話,應該也是坐東海道新幹線。」
「OK,謝謝——您也是坐這輛車?那要不要一起去買票?」
他剛想回應,另一個女孩又突然接話說:「您是一個人來旅行的嗎?好酷喔!」
「唔,沒有啦,」進藤無奈地扯出笑容,「我和朋友約好了,只是在這裏等他。」——即使不知道他會不會來。
於是女孩們沒有多說,再次道了謝,祝他旅途愉快之後就離開了。
他本想去離檢票口遠一點的地方等,卻在將要轉身的一瞬被重重地撞了下肩膀——雖然算是早高峰時段,但畢竟是週六,這裡的空間遠不至於擁擠到走路會相互碰到的程度;進藤剛想責問這傢伙怎麼回事,就正對上了他一週沒有見到的人的眼睛。亮留在他肩上的觸感還沒有消退,在他一步遠的位置停下,神情冷峻地望著他。他沒說話,只是把手裡一個顏色明豔的東西推到光懷裡,隨即一言不發地刷了乘車券進站,整齊的髮尾幾乎要把空氣切成兩半。光愣了愣,驚訝地低頭看向手中多出來的東西——是套了層紺色和紙的包裹,上印著鎏金的起伏的青海波。
塔矢亮週五晚回到家時,就發現光兩個小時前給自己打過電話。那條語音留言他重放了幾次,聽著聽著便笑了出來,腦海裡甚至還原出光垂頭喪氣得額髮都耷拉下來的樣子,想撥回去又怕時間太晚會打擾到他休息——其實早在幾天前就消氣了;只是心裡還有點不舒服,不過就是想逛街而已,都說了可以刷自己的卡,為什麼還非要讓他陪著去;也太愛玩了吧,幾歲的人了還這麼不分輕重。可自己這不還是下班之後繞道去他愛逛的商場給他買了他想要的浴衣嗎⋯⋯其實當時如果說「盡量騰出時間」的話,也就不會變成現在這樣⋯⋯這麼想著,這天早上,亮卡著七點三刻來到車站,準備等光到了之後把認真當作禮品包裝好的浴衣給他,不失體面地道歉,和好,然後開心地去鄉下玩三天。只是沒想到一向習慣踩著點出現的光已經在檢票口,而且在和兩個陌生女孩聊天。亮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他看到他在笑,是闊別七日的、此時的他所想念的笑容——昨天晚上打電話的時候還是那種很委屈的語調,今天心情就可以這麼好嗎⋯⋯亮莫名地煩躁起來,又意識到自己一定是想太多,婆婆媽媽的杵在這裡很難看,於是更加煩躁。他遂低頭看了眼抱在手裡的東西,在兩個女生走遠後,像完成任務一樣丟到光的手裡,決心不去看他的表情。
希望號在豐橋站停下,他們換了車,到達蒲郡的時候還不到十點半。從舒適的冷氣裡出來,彷彿掉進一個蒸鍋。
一群同齡人聚在一起,確實有緩和氣氛的效果。伊角跑去服務台撈了份旅遊指南,上面是彩印的蒲郡地圖和景點,「哇,好小的城市,不過居然連水族館都有?——我們今天要不要上去竹島的神社參拜一下?」
「對欸,」奈瀨說,「愛知縣的國家天然紀念物!剛才在車上聽明明講了,連結陸地與孤島的石橋和海上的鳥居,好浪漫喔。」
「啊,肯定是要去的,」光抓了抓頭髮,完全沒有看路就開始往前走,「不過外婆有說今天到了之後要招待我們吃流水素麵來著——雖說是『招待』,但竹子還是要我們自己去砍啦,估計也得費上幾個小時。」
「喔?竟然有這種好事,」和谷衝到光面前一把拍在他肩上,「馬上就能吃到真正的流水素麵欸,用竹子流的!進藤你怎麼不早說!」又抓住依然在看旅遊指南的青年,「真是太感動了,你說是不是啊伊角!」
伊角拿著地圖的手一抖,刚想说什么,越智就在他背後開始嘟囔:「上山砍竹子?這種事進藤你可沒講過,難得的休日誰想做苦力啊,你們誰愛幹誰幹,反正我不幹。」
「越智啊越智,」和谷轉過來叉著手,「真是一點品味都沒有。海之日、流水素麵、東海岸的田舎,多麼完美的夏季風物詩啊!這可是我們大和男儿的大和魂——」伊角和奈瀨對視了一眼。和谷繼續道:「不過像你這種夏天都不出門只躲在屋裡吹空調的少爺大概是不會懂的吧,太可惜了!」
「嘁。」越智白了他一眼,剛準備還嘴,社突然擠到他跟前攔住,轉而看向光,用嚴肅的語氣問:「所以進藤,咱們該往哪走?」
光指著前面,「順著這條大路,到那邊的山腳就是了。」
藤崎看起來也是認識路的樣子,對於光的回答似乎想說什麼,但看社點了點頭並移動到了和谷和越智中間,她也就沒有插話。
離開車站四周縱橫的馬路之後,便只有一條雙車道的柏油路,沒有多少車,路面的盡頭被太陽烤得泛起飄動的波紋,管風琴樂一樣悠長的蟬鳴與之相和。人行道有零零碎碎的樹蔭遮蓋,大部分時間卻還是要指望旁邊的樓房。漸漸地,樓房也少了,只剩下斜頂上鋪著瓦片、牆上裝著木窗框和木欄杆的獨戶人家,和米店、車行之類的低矮商鋪;道旁樹也不再有,路邊停了幾輛汽車和自行車,金屬在烈日下閃閃發光。遠處的藍天沒有一點雜色,天幕下是一座青綠的山;他們像是已經走了好久,但那座山看起來完全沒有變得更近。
亮走在一隊人的最後面,藤崎和奈瀨將地圖從伊角手裡拿過來看,和谷似乎和社達成了某種共識,聊得很認真。
一直默默跟在旁邊的越智推了推眼鏡,問:「進藤,還有多遠?」
「嘛,前面有條鐵道,到那裡就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了。」
朝他手指的方向望過去,一側生了紅鏽的鐵板牆和另一側的灌木叢之間狹窄的空隙裡,似乎的確有鐵道黃黑相間的閘口和綠色的崗亭,被蒸騰的熱氣扭曲。
「哈?既然這麼遠,剛才在車站打個車不好嗎。」越智有些不耐地說。
「欸,會覺得遠嗎?」進藤疑惑地回頭,「小時候來這裏玩,都是一路從車站跑到外婆家的,大概四公里的樣子。」
越智把肩上的背包帶子挪了一點位置,「四公里,真敢說啊⋯⋯也不考慮一下還有女孩子。」
「我是不用擔心啦,」奈瀨擺了擺手,「明明還好?」
「啊,其實以前也跟著阿光來玩過幾次,路都認識了,不要緊的。」
和谷嗤笑了一聲,「我看只是你自己走不動了吧,越智?」
「——」
社抬起胳膊正好擋住越智的視線,向前指著說:「你說那個鐵路嗎?」
前方的馬路變寬了一些,一輛藍白塗裝的細長列車從中間呼嘯而過。
「嗯,對。」
「這是⋯⋯東海道新幹線的車吧?和我們坐的那趟一個色。」
「是啊,東海道新幹線有穿過蒲郡的山區,只是沒有設站,所以才要換乘。」
「⋯⋯喂喂,你們關東的鐵路規劃是不是有點毛病?」社依然保持著均勻的步速,音量卻變大了,「真是敗了,剛才我們就該一直坐到這塊兒,然後撬窗戶跳車。」
在棋盤前面完全不會認為一個小時很長,走路的時候卻像是過了一整個上午。道路時寬時窄,有高有低,那座山常常被建築和樹林遮擋,再次見到的時候,還是那樣遠。塔矢一路上沒有抱怨什麼,只是逐漸感到腿已經完全是在機械地移動,腳跟由痠痛變得麻木,背包也壓得半邊肩膀發燙,像卡住的軸承。
身邊慢慢變成小湖和梯田,道路順著山體盤旋而上,太陽毫無遮攔地照射下來;不知不覺地,再往兩旁看的時候,已經一面是高牆一樣的林木,一面是綠油油的深淵。光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忽然加快了腳步。藤崎笑著對奈瀨說了什麼,後者望著前面點了點頭。
轉過又一個彎,光跑向一座用金黃的矮籬笆圍起來的院子。
「哎,阿光⋯⋯」藤崎試圖叫住他,可他已經一手搭在了院門上。
「喲,我來啦!」他向裡面喊,熟練地伸手從裡面打開了那道只及腰高的小門,轉身站在門邊回頭示意大家跟上。
正在他們猶豫是否該效仿光私闖民宅一般的行為時,裏屋灰褐色的木門拉開,一位繫著靛藍印染圍裙的老婦人走下兩級台階,用圍裙一角擦了擦手。
「小光?」
光聞聲跑過去,一下子抱住老人,將腦袋埋在她肩上,「幸子——!」
⋯⋯竟然會!直接稱外婆的名字嗎——眼看著名叫「幸子」的老人家笑著將一隻手搭在光的後背上輕輕地拍——棋院一直有「進藤光其實不是日本人」的傳聞,某些臆測又分別派生為「奶奶是外國人」、「琉球人」、「阿伊努人」;亮對此也有所耳聞,而其中邏輯大抵是,由於一直染髮、瞳色比較淺,濃眉大眼、輪廓分明的長相也很與眾不同,穿衣風格又非常前衛,再加上有些叛逆、甚至偶爾狀似「不良」的行事作風,攪和在一起就變成「進藤光其實是混血」這種說法。可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人,非要隨身帶著一把墜有紫色流蘇的夏扇;亮又想起他在兩年前成人日那天晚上要求自己幫他打耳洞的情形,想到他後來對自己講他和佐為的過往⋯⋯
「⋯⋯真是,又長大了,外婆都不敢認了。」
老人抬起手摸了摸光的髮頂,光便乖順地把頭低下來,「欸嘿嘿⋯⋯」
「三年不見了吶,過節也只得打個電話——」又看到門外的一群人,忙說:「呀,快去讓朋友們都進來,怎麼能叫客人在外面等。」
既然都這樣說了,他們也就照做,亮回身將院門重新閂上。屋子前面是一小片用一排排短木樁劃分成小塊的花圃,陽光下金黃的、嫩粉的月季和陰影裡三色的繡球開得正好,菖蒲還餘下幾株花頭,波斯菊五彩的蓓蕾已經從一片濃郁的綠色中抽出;花圃中間一條乾乾淨淨的石磚路,角落擺著一個工具箱、一隻鐵皮噴壺和一圈水管。
「——吶,這是我外婆幸子!」光摟著老人的肩膀笑道,又拉著每個人依次介紹一遍。院門口沒有門牌,他們聽藤崎明叫「幸子さん」,便也跟著稱「幸子さん」。
在玄關處脫下鞋子之後,一行人跟著光穿過門廳,去分好的房間放下行李,回到起居室的餐桌圍坐下。室內開著空調,樸素的薰香、曬得發熱的木頭和舊傢俱的氣息掩蓋了製冷劑的味道。那一份已經皺了角的地圖被當成紙扇相互傳著。
「這房子蠻大喔。」社四下看了看說。
「家裡的老宅嘛,以前是我媽和兄弟姐妹一起住的。」
不多時,幸子從廚房端出準備好的蟹腳天婦羅蓋飯,又拿了一盤甜瓜。「是後院裡摘的喔,只有這個季節才有。」她笑著說,「不夠吃的話,廚房還有。吃好了才有力氣上山。」
午飯之後,已經是下午一點多了。藤崎和奈瀨主動提出幫忙洗碗,並留下來準備晚餐的東西,男孩子們開始分配砍竹子的任務。
「啊,要不要去超市買點喝的?」社問道。
光打開冰箱看了一眼,「嗯,家裡只有茶,可以帶幾瓶汽水回來放在後院的冰桶裡——」
「那就⋯⋯」越智推了推眼鏡,「我跟社去超市好了。」
「欸,話說上次在和谷家的時候就是社和越智一起去買的吧?」
「——嚄,那可千萬別再讓他倆去!你們都不記得上次了?」
聞言,藤崎轉向奈瀨:「上次?」
「上次」是指,四月的某天在和谷家的研究會下棋到很晚,於是決定讓快棋輸了的越智和社去便利商超買宵夜的那天。本來十五分鐘能往返的路,兩個人費了近三刻鐘才回來。而購物袋打開的那一刻,凌晨一點上目黑寂靜的街區中某間狹小的公寓裡發出了一陣哀號。
「我有說了三遍『零度』欸!」進藤抱著大瓶的還掛著冷凝水的原味可樂皺著眉大喊,「為什麼還是買了有糖的?夏天快到了我在減肥啊非要我說出來嗎!」
越智拎出葡萄味的波子汽水,看都不看地撕掉封紙、把蓋子按下去,只聽見彈珠敲在瓶頸上發出清脆的「叮」一聲,「⋯⋯這還有區別了。」
「⋯⋯等等,我要的是『蘑菇山』,這怎麼只有『竹筍鄉』啊!」原本在翻袋子的和谷從地上跳起來,「是誰!是誰點的『竹筍鄉』!」
「反正都是巧克力餅乾——」
「你懂什麼啊!」
「誰叫你就知道坐在沙發上要這要那的,根本記不住好嗎。」
「記不住?!你從小到大沒去過超市喔?那麼常見的東西都能拿錯。」
「⋯⋯好歹波子汽水是沒錯的啊。」
「那是因為你自己要喝才會記得吧。」
伊角在他們的爭執中冷靜地插話:「⋯⋯話說,怎麼去那麼久?便利店就在旁邊的啊,發生什麼事了嗎。」
「啊、那個,說起來——」社抬起左手尷尬地摸了摸後頸,「哎⋯⋯都是因為你們東京話裡食物的名字太難講了啦。」
回憶起適才在便利店,差不多把能記得的都買了,越智和社站在收銀台前,他眼看著社抬手跟店員問了晚上好,把購物籃放在台上,然後指著一旁的點心櫃說:「再麻煩來一個『太鼓饅』,謝謝。」
店員愣了一下,嘀咕著:「『太鼓饅』⋯⋯是什麼⋯⋯」他用求助的眼神看向一旁的越智,越智流下一滴冷汗,默默搖了搖頭。
社似乎意識到了什麼,比劃著解釋道:「⋯⋯那個,就是一種紅豆餡的點心。」
「豆沙包嗎?」
「呃,不是。」
「銅鑼燒嗎?」
「也不是⋯⋯」
「那、鯛魚燒?」
「不⋯⋯但是很接近了!」
店員撓了撓額頭,繞著櫃檯看了一圈,對他們鞠了一躬,「請您稍等一下。」說完轉身進了儲藏室。
最終,在店員根據進貨單取出來的堆滿整個檯面的所有紅豆餡點心製品中,社眼睛一亮,撿出一個手掌大小的塑封包裝,「喔,原來在這裡叫『今川燒』!真厲害,好罕見啊⋯⋯」
「吶,就是這樣。」越智向伊角解釋完,喝了一口波子汽水。
「吶,總之就是這樣啦~」回到當下,奈瀨對藤崎說道,而後者正捂著嘴努力不笑出聲音。
「好了好了,」伊角說,「不介意的話,還是我和越智去超市吧。」
「我寫個購物單?」光從茶几下面抽出便利貼和圓珠筆,又指了指和谷和社,「——那一會兒我們三個上山咯。」
這時,一直不發一語的亮忽然站了起來,「我也去。」
亮有着这样的印象,從和光確定關係開始——不,其實是從更早的時候開始,光似乎就一直對他採取物理意義上「過度保護」的態度:逛街時會理所當然地幫他提東西,在家也從不讓他搬重物;印象深刻的是神田祭那天看山車的時候,背後和兩旁全都是歡呼、鼓掌、唱歌的人群,身前用來分隔觀眾的注連繩跟著搖晃,不斷被周圍的人碰到,但在這樣的氣氛中也逐漸習慣起來。直到忽然覺得擁擠的感受消失,才發現是光的手臂攔在了自己身側,原本下意識地想讓他在公共場合收斂一些,別做這麼親密的舉動,又見其實并沒有人在看他們,便用團扇掩住唇角,也默默地向後靠了靠——同樣是男性,總是受到這樣的關照,偶爾會有被低估的感受,不過自己原本就不爱做體力上的事情,於是大多時候也就樂得清閒。
但現在畢竟和光是「吵了架」的狀態。儘管知道光在旅程中有很多人要招呼,亮還是對於他從今早開始就好像不敢對自己說話、不敢讓自己做事的樣子感到很不自在。
光有些驚訝地轉頭看過來,短暫地打量了他一下,略帶遲疑地說:「塔矢⋯⋯還是留在家裡幫忙吧?」
「為什麼?」亮向前邁了一步。瞧不起人嗎?以現在的情形,這種特殊對待完全沒有必要吧。
沈默地對視了一會,是光先移開了視線,「呼⋯⋯不是我說,你先看看自己穿的是不是能上山的鞋啦——」
「——?」
亮這才意識到,早晨出門的時候只隨手從鞋櫃拿了一雙低幫的軟皮鞋,這已經算是他相對休閒的裝束,因為當時也完全不知道會需要去山上。
「——濺到泥了或者弄濕了的話,難道要重新買一雙嗎?」光歪了歪頭,挑起眉毛,「我可不想因為你,一個月踏進愛馬仕兩次。而且這種鞋底走石子路會很傷腳欸。」
亮剛想要嗆回去,藤崎小跑過來說:「好啦,塔矢君跟我們一起過來吧。」
奈瀨也從開放式廚房的島檯後探出半個身子,「快點,準備在院子裡吃麵的話,還有好多東西要洗喔。」
進藤和塔矢之間果然發生了什麼事情吧⋯⋯社就算早些時候沒有注意到,在上山之前他們兩人的對話中也發覺了。
實際上也不需要真的進山,只是路過一條水渠、一道小溪,再順著碎石路往竹林裡走,靴子踏下去像踏在厚厚的雪地上,竹葉之間「沙沙」的聲響如同海螺深處的濤聲一樣逐漸將他們包圍。
剛認識進藤光的時候,社覺得他們或許是非常相似的人——與同齡的普通中學生不同,幾乎過分地執著於圍棋、不太循規蹈矩、有心事、看起來不像好孩子。於是剛認識沒多久,他就跟進藤講起自己的經歷,一半算是需要給這些每天堆積在腦子裡的瑣事找個出口,一半是認為能夠獲得共鳴。然而在之後的幾年間他逐漸發現,進藤雖然看起來不服管教,伴隨有諸多出格的發言和行徑,卻意外地是一個自然而然就能夠處理好人際關係、照顧到他人情緒的、並沒有什麼攻擊性的人;而反觀自己,大部分時間還是獨來獨往,和家裡的矛盾也沒有絲毫改善,即使他已經參加了數屆北斗盃乃至各路知名國際賽事、入駐成為見報《圍棋週刊》的常客。
「就這兒了。」進藤停下腳步,抬頭看了看。他們身處高及一半小腿的野草地裡,四周全是望不到頂的竹子,來時的小路早就見不到了,連陽光都被層層的竹葉過濾得只剩下斑駁的影子,空氣中飄散著濃郁潮濕的清香,攪動著巨大風鈴一樣的竹枝。
進藤找了一塊野草少一些的地方,將工具箱放下,拿出手套、柴刀和口罩分給他們。「——還準備了帽子嗎,幸子她。」
用柴刀砍竹子不算容易,由於是要做食器的東西,只得慢慢鋸開;於是大約切進去不到一公分就要換人,並且為了保險起見,還要砍兩根。
「話說,進藤?」輪到社的時候,和谷問旁邊正在活動手臂的人,「記得塔矢是在準備棋聖戰的B組循環第三場?」
「⋯⋯唔,是。」進藤看起來在想事情,甚至一時沒有意識到在問他話。
「他狀態怎麼樣?」
「啊,還不錯。」他點頭,「畢竟是他嘛。」
和谷肉眼可見地眼皮跳了下,又問:「那你呢?今年三星火災杯的國內預選?」
「嗯,沒問題的。」
「⋯⋯」
這段實際上沒什麼營養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
所以說,像進藤這樣的人,竟然會和塔矢亮有如此頻繁的矛盾⋯⋯看來問題只能是在塔矢了?但塔矢雖不是熱情主動、情感外露的人,卻向來處事周到而禮數周全,和其他人的關係並不差,從未聽說過他和別人有嚴重的爭吵,而唯獨跟進藤⋯⋯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說到底,憑以往的經驗,看他們分分合合到現在也沒有一拍兩散,多年的朋友之間最終總是會重歸於好的吧,與其在這裡操心進藤和塔矢的矛盾,不如多想想自己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
「換你了,和谷——」他正了正帽簷站起來,走到旁邊。進藤還在揉自己的右臂,但似乎心不在焉。「說起來,進藤,真羨慕你有這樣的家人啊。」
聞言,進藤猛地轉過頭,不知是不是他的錯覺,一瞬間他仿佛看到進藤眼中流露出驚懼的神色,又像反應過來什麼了一樣迅速恢復了普通的神態。
「為人很熱情、一直支持著你⋯⋯呵,其實我之前也以為只要證明自己,就能讓我的家人轉變態度;現在看來,是我的願望太不切實際。」社脫掉右手的手套,摘下帽子拿在左手,抓了抓漂成全白的乾硬頭髮。「上次回去看他們的時候,本來想著會因為我離開一段時間就對我態度變好。結果到的頭一天還相安無事,自打第二天開始,就又回到每天從早到晚聽著我爹為了各種大小破事對媽又喊又叫,順帶著讓我找個正經工作的狀態——我買的那一堆《圍棋週刊》他們倒是還沒扔。」他把帽子重新扣回頭上,看向竹林深處,「總之,現在終於跑出來了,離開了『家人』⋯⋯」
進藤默默聽著,低下頭沉吟了片刻,「『家人』嗎⋯⋯」他的視線一直看著手裡的柴刀。「其實我家也不是像你見到的,一直都這麼和睦。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外公外婆是住在東京的,離我父母家很近,是會經常串門的關係。直到有一次,幸子她⋯⋯和外公吵了一架,很兇,到了幸子直接住回老家、完全斷開聯繫的程度——當時我還不記事,是我媽後來跟我講的——這樣大概持續了一個月左右,結果外公就在那時候走了⋯⋯」進藤抬起頭,社沒有去看他的表情;他像平時緊緊握著扇子那樣握著那把刀,「她後來好像消沈了很長時間。媽試著聯繫過,但是打不通電話。直到又去登門拜訪,才知道她已經把豐島區的房產賣掉,搬到蒲郡的山裏來了;之後就一直自己住在這邊。這也是為什麼她沒有掛門口的名牌,會讓別人,即使是晚輩,直接稱呼她的名字⋯⋯」
他說完,走過去接下和谷手裡的活。「所以說⋯⋯沒有什麼東西會一直持續的吧,」他在刀刃刻進竹莖裂口的粗礪、單調的聲音中繼續道,「爭吵、不和也好,親人之間的紐帶也好,人和人之間縱使曾有過再緊密的聯繫,說不定哪一天就會突然消失了。」
那把刀終於穿透了整個主幹;耳邊忽然安靜下來。依然青翠的竹樹緩緩傾斜,午後熾烈的陽光從它背後洩下,墜落的枝葉濺起金色的塵土。伴隨葉片彼此傾軋的聲音,似乎再次響起了風。
亮將棉布搭在剛擦乾淨的椅子靠背上曬乾,提起空的水桶去菜畦的另一側打水。說是菜畦,每塊也不過種上十幾、二十株作物;他不常見到長在地裡的蔬菜,沒有開花掛果的話,就基本上都不認識。幸子夫人中午時給他們嚐的甜瓜看來是從牆邊的藤上採的,捲曲的蔓、褶皺的花中間還躺著幾顆淡青色的果實;一些矮小的、長得像微縮盆景一樣的小樹上結了一串串紅色和綠色的番茄,點綴著星星一樣的黃花;除此之外,都是大片的綠油油的葉子,或是已經只剩下枝幹的。他把手裡的塑料桶放在地上,擰開了龍頭等著水接滿。一天最熱的時候剛剛過去,天光不再是一片晃眼的白,而染上了一點柔和的金色;他終於能夠不費勁地睜開眼睛望著頭頂和遠處的晴空,如同藍染用的顏料直接潑灑在高遠的白雲上,於是雲層就這樣化開,流過陽光做成的天幕,在視野的邊緣沉澱得發紫。這樣濃烈的藍紫色倒映在腳下那一桶圓形的水裡,像一面鏡子,他在近乎純色的背景前面看到自己的臉,沒有什麼表情,眼角緊繃,嘴唇抿成一條線。原來自己之前看起來一直是這樣的嗎⋯⋯他對著倒影,緩慢地做出微笑。
還有一條長椅、三座木支架要沖洗乾淨,完成之後,在竹子抬回來前,後院的工作就暫且告一段落。幸子夫人在講如何調製蘸冷麵用的各種醬料,又問起想要吃什麼小菜。亮把用過的水澆到菜地裡,把空桶放回牆根,轉頭看了一眼上山的方向——他們還沒有回來。於是他走上台階,脫掉鞋子,準備去廚房看看。
露台連著後院,地上擺了一隻矮桌,雨棚頂上掛了風鈴,風鈴裡裝著一圈薄鐵片,一起隨著微風輕輕晃動。欄杆上爬了纖細的藤蔓,掛著星星點點的紫色;塔矢猶豫了一下,湊近去看。是未開的牽牛花,花蕾柔軟的尖端像海螺一樣右旋成一簇,靜靜地藏在陰影裡。
「塔矢君?怎麼了嗎。」幸子夫人的聲音從身前傳來。
「啊,沒事。」亮回過神來,直起身微笑著說:「這邊剛好整理完。還有什麼我能做的?」
她已經摘下了圍裙,靠在通向露台的門旁邊。「和我去準備加工竹子用的工具吧?」她走進耀眼的陽光裡,身後留下溫暖的、微苦的香氣,「阿光他們該要回來了。」
亮跟在她身後。
還沒走兩步,便聽她說:「番茄又可以摘了。」於是轉身走到土埂上,彎腰托起一串果枝,拈了幾顆下來,放到水龍頭下面沖洗之後遞過來,「吶,嚐嚐?」
儘管相比起和同齡人打交道,他更熟悉也更擅長與長輩相處;可他對於自己家裡祖父輩的人卻沒有多少印象,父母晚婚,他並沒有見過爺爺奶奶,而母親與娘家又不太來往。於是在光說帶他去外婆家合宿的時候,他就不禁在心裡猜測起「外婆」會是什麼樣的形象。
他小心地接過掛著水滴的鮮紅果實,「謝謝。」
酸甜的、微涼的汁液在口腔中噴濺。海鷗從竹林上空飛越,影子追著潔白的羽翼在他們腳下劃出它的航線。他抬眼,發現幸子夫人正望著它消失的方向。
「可能這麼說會很怪,」老人回頭道,「不過我總覺得,塔矢君和阿光好像是很相似的人。」
「欸?」有點驚訝。
「嗯,都是會用笑容掩飾心事的人呢。」
一直以來,都是被認為和光性格相反,連他自己都想不出他們除了圍棋能有什麼共通之處,但突然聽旁人這麼一說——
「⋯⋯確實,也許是這樣沒錯。」
進藤總是很開朗的樣子,即使有困難和憂慮也都會直接說出來,和朋友們一起放鬆,調整心情。但就是這樣的他,卻有不會對任何人道出、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曾對自己講的過往。
「說起來,阿光小時候經常去這旁邊的棧橋上釣魚。」幸子忽然笑了,「本來是他爸爸要去,他非要跟著,據說還像模像樣地端著釣竿坐了半天。結果魚沒有釣到,卻釣上來一只高腳蟹,他以為是大蜘蛛,嚇得動都不敢動。回來之後還很是得意,大家也都說阿光有釣魚的天賦,一晚上就開開心心地過去了。」她朝自己嘴裡丟了一顆番茄,「誰知道第二天孩子就開始發高燒,仔細一看才發現,是腿上被蟹鉗夾破了。問他疼不疼,他說疼。又問那為什麼昨天沒有講,他邊哭邊說:『因為一點都不帥啊,被螃蟹夾了什麼的。』」
「這⋯⋯還真像是他說出來的話。」亮擋著嘴輕笑。
「是啊。」老人也是滿臉笑意,眼角暈開溫柔的細紋,「所以,阿光其實是個心思很細的、凡事都會有自己的考量的孩子。」熱風吹動她耳邊的白髮,「不管是出於對自己形象的期待也好,不想讓人覺得麻煩也罷,他很會看人眼色的,一般都不會讓人誤會自己。知道你們關係很好,所以今天看到你們的相處,會有點意外呢。」話題突然轉移到自己身上,亮見幸子對他眨了眨眼,「是吵架了?」
「——啊,」有這麼顯眼嗎⋯⋯他移開視線,「沒有,是我自己的問題。」現在想來,與其說是吵架,不如說是自己單方面抓著他說錯的話追責、賭氣,非要他講出他不想講的心事,把工作帶來的壓力順勢一起發洩到他身上,而等到頭腦冷靜下來,已經不知道怎麼和好了。
說著光太幼稚,其實自己才一直是他們關係裡不成熟的那一方。
沈浸在自省的情緒裡,卻聽幸子突然停下腳步大笑起來。「哎呀,真是可愛的孩子。居然會用『問題』這樣嚴肅的詞!」拍著自己的胸口順了順氣,才說:「——你們年輕人之間,哪會有什麼『問題』;時間還長著,吵吵停停,總能重新黏回到一起,我是很有信心的喔,都是青春的經歷嘛。」老人說罷,整了整衣服,又朝他微微附身,歛起神色道:「⋯⋯我家阿光,之後也請多關照了。」
塔矢愣了一下,趕忙跟著鞠躬說:「哪裡。這邊才是。」
他看著幸子順著土埂往前走去,在一座白色矮房前面站住,隨後從口袋裡拿出鑰匙打開門。
和光真的有些像——即使萍水相逢,也能夠讓人覺得溫暖和輕鬆,感到被關心著,卻不會因此而產生負擔,他遂樂意接受,也願意敞開心扉,甚至有一瞬忘記了自己在面對相差兩輩的人。
只是,不知是不是他的錯覺⋯⋯可能這樣想對光的外婆會很失禮⋯⋯但剛才好像、有被八卦到一些很重要的事?
越智和伊角把飲料在冰桶裡擺好的時候,進山的一行人也回來了。男生們將竹子劈開、去掉竹節、打磨、沖洗、消毒,做成流麵用的水槽之後,已經是下午四點。餐具放在露台的小桌上,麥茶和瓶裝飲料在旁邊的冰桶裡,後院架起的水槽的下游擺了一排椅子和長凳。每個人拿著各自的杯子坐好;光站在水槽頂端,右手邊放著一大盤掛麵,左手端著自己的茶碗。「嘛,好啦!」光把嘴裡的麵嚥下,「準備!五、四、三——」
社一捶大腿,「喂進藤你不要自己先吃起來啊!」
「哎呀,」水管的龍頭被旋開,光夾起盤裡的麵懸在水槽上方,「總之要開始流啦——」
「喔喔喔喔喔,」和谷舉起筷子喊,「來了來了——」
其實椅子根本是沒有用的,因為完全沒有人會乖乖坐著吃。亮本以為在很靠近終點的地方就可以安心坐下,但最終還是被迫跟著大家站了起來。麵是提前煮熟、瀝過冷水的素麵,蘸醬是鰹魚醬油裡加了芥末和圓蔥,又根據自己的口味放了些味素、芝麻和天婦羅花。流水讓麵變得又冷又滑,入口的涼意之後,白麵的麥香、昆布的鮮味和簡單配料的點綴在口腔中慢慢散開,像有風從身體裡吹過。
「這什麼沒效率的吃法。」越智在第五次看著麵條從筷子中間滑走之後嘀咕道。
「嚄!」和谷見縫插針地衝過去接住放到自己碗裡,「看我的這招『斷』!」
社瞥了他們一眼,默默地咬開一莢毛豆,就著喝了口冰茶,又回到前面等著搶下一團麵。
「⋯⋯搶了半天不還是沒夾到嘛。」奈瀨看著經過一群筷子的圍攻之後流過來的麵,在下一個竹節的地方攔住。
藤崎笑道:「但這樣真的好涼快喔。」
「誰想來放麵嗎?」光大聲問,「還有一半。」
「已經只剩一半了?吃得好快啊。」
「準備兩小時,吃起來五分鐘。」
「——喂,提著筷子提前在這裡攔是作弊的吧!」
「這不是也沒有放到水裡嗎!自己吃不到不要怪我。」
「我說你們,讓開一點啦,完全擋住了欸!」
「哎哎別推我要掉了要掉了——」
亮無聲地歎了口氣,從他們背後繞過去,「進藤,換我來吧。」
「欸?啊,那就辛苦你了,塔矢。」光朝他笑了笑,眼神卻在他身邊打轉,隨後放下盤子端起茶碗擠進專心盯著麵條的人群。
「進藤,你剛才吃掉了不少吧!我可看見了。」
「很餓欸,又不能跑過來和你們搶,講講道理——幸子,也過來吧!」光說著抬起胳膊朝外婆揮手。
他一面將短袖T恤的兩邊袖子捲到肩上,胸前的衣料因此垂下兩道弧型的褶,高舉著的手臂上流暢的肌肉繃緊,露出光滑的腋下,內側不常曬到的偏白的皮膚暴露在陽光裡;從寬鬆的袖口看得見一點點身側的線條,胸肌投下的陰影悄悄地伸進輕薄的棉布下面。向前探身的時候,衣服便貼在汗濕的後腰和背上,隨著肌肉的起伏而波動著,像雲的影子撫過綿延的山脈。
亮差一點忘了放新的麵。
他瞥見在光身邊擠來擠去的男孩子們,毫不在意地碰到彼此的手臂、肩膀和腿,奈瀨和藤崎滿臉司空見慣的表情,一邊和幸子有說有笑一邊像看學生運動會一樣看他們爭搶;光低頭瞥了一眼濺到身上的水,汗珠順著臉頰流下來,拖著一條閃爍的痕跡,墜在眼角,再不以為意地抬起手背抹掉——亮知道自己在盯著他,但他移不開眼睛。他沒來由地想起了光打球的樣子。在他們十八歲的那個夏天,也是因為什麼雞毛蒜皮的小事而陷入冷戰的狀態,於是他出門之前站在玄關的鞋櫃前面,把鞋子拿出來又放回去,猶豫了好一會兒是否仍該履行這個已經過了太久的約定。終於踏進球場時剛好看到光搶下一個籃板,少年一躍而起的身影刺破盛夏午後悶濕的空氣,投進他毫無防備的眼底,在他的記憶裡種下新生的、青澀的綺念。他沒有發覺自己出了神,直到光在隊友的簇擁間回頭看到了他,驚喜地咧開嘴笑著向他揮手——他站在樹蔭下,卻感到臉上發燙;像是石子落進一片平靜的潭水,泛起停不下也抓不住的漣漪。那一刻才意識到,原來他已經⋯⋯喜歡上這個人了啊。後來,知道光的戀心也屬於他,有幸讓這份感情得到回應。从他們成为戀人開始到現在,早就不止一次地見過彼此的身體,也有過數不清的不足為外人道的親密接觸,可再次見到的時候,還是會像最開始那樣⋯⋯
從耳根到雙頰、甚至脖子都熱起來。頭頂的太陽很毒,但他知道不是因為這個。他將頭髮往前撥了一點以遮住臉的側面,覺得有些不自在,像是情緒被挑釁或者刻意地忽視了一樣。不到半分鐘前放下去的麵被不知道誰的筷子夾走,於是他又向流水裡丟了一團——說來,這個人真的一點都沒有意識到這種著裝有多不得體嗎?就這麼讓自己的身體被隨便看到⋯⋯雖然腋下和胸口不至於被稱為「隱私部位」,但一直以來是只有面對自己才會露出的樣子,更何況現在還有女孩子在場。
等等,他在胡思亂想些什麼啊⋯⋯
「塔矢,已經沒有了嗎?」光的聲音響起——該說「不合時宜」還是「恰好」?
「嗯?」他趕緊轉頭去看手邊的盤子,「還有最後一點。」
剛放下去不過幾秒,他便聽見伊角在一片哄鬧中說:「看來上半場的封手是我呢。」
吃過一輪麵條之後,又架起了燒烤。開始第二輪之前,藤崎提出要拍合照,於是女生們提議帶了浴衣的幾個人回房間去換上。
光和越智在庭院裡等著,順便換上新的茶葉,一邊盯著燒烤用的炭火。他看見亮從露台走進室內之前回頭瞟了他一眼,眼神很快又被整齊的黑髮遮住。繞在欄杆上的牽牛花隨著他身後的風顫了顫——從竹林回來的時候,他見亮和幸子正聊得開心,望向自己的眼神也回到了以往的柔和,本以為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重歸於好,亮卻在方才吃麵的時候不知為什麼又重新板起臉來。難道是因為一群人搶東西吃的氛圍讓他不舒服?還是飲料和食物都太冷了?或者還在生自己的氣嗎⋯⋯想起最終還是沒有帶他去買硬質棉料的浴衣;光忽然覺得有些緊張。
「說起來,越智?」他撥拉著冒出紅光的木炭,「聽社講他最近都住在你家?」
「⋯⋯嗯。原本定好要接納他的親戚忽然把房子租給別人了。大阪人嘛⋯⋯」越智放下茶杯,厚厚的圓形鏡片反射著白色的日照,「所以在他找到新的住處之前,暫且收留他一下。」
「真好啊,」進藤歎了口氣,「可以天天一起下棋。」自己和亮分居的這一週讓他意識到七天竟可以如此漫長,在棋院的時候期待著偶遇又擔心真的碰上了會不會尷尬,回到家面對空蕩蕩的公寓,便想念起他的棋、還不可避免地想念著他的⋯⋯人。
越智挑了挑眉,「你和塔矢不是也經常下棋嗎?就算他不住你家。」
光愣了一下,一邊從炭火前撐著膝蓋起身,一邊想如何回答才能顯得自然些,而下一秒的景象打斷了他的思路——露台的門再次拉開,木屐的聲音落在傾斜的陽光裡,微風將柔軟的藤色平織紬輕輕吹起,溫潤的光澤與淺色市松紋樣交錯,像晴空在紫藤架下斑駁的影子,寬大的衣袖拂過同色的橫紋角帶,袖口下露出精緻的小臂和雙手。亮的眼睛半藏在黑髮的陰影裡,但進藤感覺到他的目光也停在自己身上。
無論看過多少次,仍會猝不及防地為眼前的人所俘獲;想要向所有人炫耀他的好,又自私地希望能獨佔他這副模樣——其實普通來說也不會有別人因為看到亮穿著絹制浴衣的樣子就起虎狼之心吧,只是自己「喜歡」的心情太強烈,被蒙蔽了一些理智罷了⋯⋯
突然聽到身後有人咳了一聲。
越智叼著不知從哪裡來的冰棍,又給自己倒了一杯茶。
亮轉頭從光面前走過去,身後留下一直伴隨著他的薰香的氣息。
合照過後,他們並沒有立刻開始吃東西,而是在院子裡四處走了走,拿著手機拍了不少照片。光看見亮走向倉庫的方向。從那條路也可以回到屋內,只是遠一些;除此之外便只是堆著剩餘的竹子和沒有收拾的工具。
「⋯⋯浴衣真是麻煩。」他聽到越智的聲音從菜畦那邊傳來。
「所以說越智,」和谷拖長了語調說,「你是真的欠缺一些品味。」
「這句話你今天說了多少次了。」
「還不是因為你總在抱怨!」
光在一旁無奈地笑出聲。這麼想來,幾年前他總和亮鬥嘴的時候,在外人聽起來可能也是這種樣子吧。伊角還在試圖勸架,社不知去向,奈瀨和藤崎沿著土埂邊逛邊聊。他看了看通向倉庫的路,繞過菜地往那邊走去。
亮提著柴刀一下一下地朝眼前手臂粗的竹子上砍著。進藤光⋯⋯這個人從上山回來開始一直沒怎麼搭理過自己也就罷了,甚至不穿自己專門為他買的浴衣——可能是連包裝都沒打開過,就那麼放在了背包裡。心事都寫在臉上了,也沒點主動的表示,只會在那巴望,看有什麼用,把自己盯出洞來就能和好了嗎?是不是傻的⋯⋯竹子從兩節中間斷開。塔矢瞥了一眼工具箱邊上搭著的手套,還是沒有戴上。他小心地將砍下的竹筒擺在圓銼下面,讓那些密密麻麻的尖硬的凸起把粗糙的切口磨平。自己到這邊一隻竹碗都要做完了,他恐怕都沒有意識到吧。還穿成那種樣子在女生面前晃,衣衫不整、寡廉鮮恥、不守男德⋯⋯亮換了一把更細的銼刀繼續磨;淺金色的空心莖內部圓滑得幾乎映出他的倒影,他把竹碗捧在手裡,旋轉著觀察是否有殘餘的纖維——
「塔矢?」
亮的手抖了一下,猛地回頭。身後的牆擋住了一半的歡聲笑語,光站在房屋的拐角處,離他十幾步遠。感到左手食指一陣刺痛,於是他背過身去,放下竹碗低頭去看,發現指腹中間被劃開一道指甲蓋寬的口子,割痕斜著切破半透明的表皮,鮮紅的血從那道縫隙裡慢慢地滲出來,像雨水漫過青磚一樣填滿皮膚上細小的紋路。
他還沒有完全反應過來為何會有這樣的傷,便聽見身後的腳步焦急地靠近,他被推著肩膀轉身,眼看著光抓著自己的手將割破的食指含進嘴裡。口腔的濕熱像有形一般從傷處流過全身的血液。光沒有看他,銀粉一樣的細汗從眉梢散落到頸側。
亮驚訝地抽氣,「進藤——」他聽見自己用有些顫抖的聲音說,感到從耳根到脖子的肌膚都在發燙,「⋯⋯沒事的。」
光停下嘬吸的動作,放開他的手指,上面裹了一層晶亮的水漬。「可能有竹刺扎進去,這麼熱的天,很容易發炎。」他左右看著已經不再滲血的切口,眼神裡充滿擔憂,卻還是沒有迎上亮的視線。
「已經不疼了,真的。」亮微微使上一點勁,想要抽回被握住的手,未果。他四下看了看,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放回光身上「⋯⋯我們還在外面。」
光這時才抬眼,盯著他,又輕輕在傷口上舔了兩下。他跨過橫在地上的竹竿,影子覆蓋在亮身上。亮向後退了一步,小心地低頭繞過地上的雜物,腳卻先碰到牆根;面前的人牽起自己沒有受傷的手放到他頸後,吐息攪著若有若無的灼熱的風灑在臉上。
一層層海浪般的蟬鳴沖刷著彼此呼吸的聲音。
「喂,越智!」社一邊喊一邊從屋裡跑出來,看來是剛換好衣服,手裡抱著折疊棋盤,「我突然想到了!」
越智終於放棄了跟和谷爭論「品味」的問題,推了推眼鏡,回頭問:「你想到了⋯⋯?」
「今早在車上擺的,第143手的變化。」他說著把帶來的折疊棋盤打開擺在廊下,「就在剛才換浴衣的時候。」
「哪一盤?」伊角問,跟著越智往回走。
「棋聖戰A組循環賽第四場,芹澤老師對緒方老師那局。」
「喔,要下棋嗎?」幸子笑道,「要不要我去把那種有腳的棋盤拿過來?」
「啊,請讓我來吧。」
「居然還有這種東西嗎!」
「是阿光幾年前回來的時候自己搬來的,」幸子一邊帶著伊角和社來到放棋盤的茶室,一邊慢悠悠地講,「看到是這麼大一個東西的時候還真是嚇了一跳呢。」
社抬著棋盤出來,擺在廊下。大家已經聚在這邊,越智剛剛復述完前後手大致的戰況。社坐下打開棋笥,準備開始落子。
「欸,進藤和塔矢去哪了?」伊角環顧四周,問道。換浴衣的時候,他有聽見塔矢先拉開房間的門出去了;而他自己回到後院的時候,進藤就站在燒烤架旁邊。剛才他們在菜畦裡聊天的時候,他還看見進藤仍然站在那兒。
「對喔,沒看見他們。」
「進藤我不知道,」越智回答,「不過塔矢好像有往那邊去。」說著指了指倉庫的方向。
「倉庫嗎⋯⋯」藤崎小聲道,「阿光會不會也過去了?而且從那邊也可以回裏屋。」
「我倆剛才進去的時候他們不在。」社說。
「等他們一下嗎?」
伊角從露台上繞下來,「我還是去看看吧。」
做流水用的竹樋的時候就是在倉庫前面的空地,碎屑、餘下的邊角料、多出的大半根竹子和用過的工具都沒有收拾。那邊現在沒什麼特別的動靜,倒是背後討論的一群人聲音更大一些,蟬鳴配合著從遠處響起。他從轉角走過去——白色的倉庫出現在視野裡——看了看周圍,然後停住腳步。
「——原來都在這裡啊。」
進藤挨著房子的牆壁站著;塔矢在他身後,背對著他們。地上的柴刀和圓銼動過,還多了一個小竹筒。
伊角將目光從那個竹筒移回進藤的臉上,「你們,要來復盤嗎?棋聖戰A組循環的第四場。」
「伊角學長,」進藤抓了抓頭髮,「那個,能不能問幸子把醫療箱拿來?」
「欸?好的——不要緊吧?」
「沒什麼。只是這個竹子的切口還是太毛糙,要用砂紙打磨一下。復盤不用等我們了,一會兒會過去的。」
兩輪冷麵、一場研討和斷斷續續的燒烤過後,暮色終於在不知不覺間降臨。仲夏的白晝拖得很長,卻走得也快;將用過的餐具摞起來搬到廚房、殘渣收到廚餘垃圾一起丟掉之後,蒼穹已經變成濃郁的紺色,半沉的淺金的斜陽在地平線上慢慢融化。
藤崎回房間拿出手提攝錄機,繞著後院轉了一圈,又去每個人面前打招呼。
光闖進畫面裡,拉著老人家,舉起一個空飲料瓶充當麥克風,問:「那麼有請幸子小姐,請問這一天過得怎麼樣呢?」
幸子抬頭看著光,又對著鏡頭招了招手,笑道:「很開心喔,是去冥土之前最好的禮物呢。」
「哇啊啊,不要說這種話啦——」光連忙擋住鏡頭,「這段剪掉!」
「欸,明明在錄像嗎?」奈瀨望著鏡頭問道。
「是喔。奈瀨今天很漂亮。」
奈瀨笑著左右轉了兩圈,她穿了一件芥子色的浴衣,抬起袖子展示竹葉的紋樣。
「——嘿,塔矢君!」
「是?」亮本來坐在廊下,兩手捧著光用砂紙打磨好的竹碗,眼睛盯著碗底反射的微弱的夕陽。忽然聽到藤崎喊他,匆忙抬起頭。
「塔矢君也穿了非常好看的浴衣。」鏡頭靠近了一點,「材質看上去好特別,是什麼?」
「謝謝。」塔矢微笑道,「是平織的結城紬。」
「是『那個』結城紬?」
「上過NHK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結城紬嗎?!」
「嗯⋯⋯電視節目的話,我不是很清楚。」
「好厲害喔⋯⋯」鏡頭在他身上多停留了一會兒,忽然抖動了幾下,角落裡傳來「呲啦呲啦」的聲音。
「——呀,越智君在做什麼?」
視野中,越智背對菜畦站著,手裡拿著一支剛點燃的煙花棒,一動不動地看著四散的火光慢慢燒到底。
「居然買了煙花棒欸。」奈瀨小聲感歎。
「哎,越智!」和谷的大嗓門比他本人先進入畫面,「這你買的?」
「是啊。」越智點了一支新的,繼續看著它燒,「鄉下的超市真是什麼都有。」
「啊哈哈哈,我說大少爺,你到底會不會玩啊?這又不是火柴。」和谷說著把煙花從越智手裡搶過來,「好好看著——」然後在空中寫了個大大的「笨蛋」。
鏡頭在努力地克制著抖動。
最後一抹金色的落日消失在竹碗的底部。亮抬起頭,夜空中已經浮出了幾點銀白的星,地平線上卻還留著火焰一般的餘暉。他腦子裡還在不斷地回放在倉庫旁邊的場景。聽到有腳步聲靠近的時候,真的很緊張;光卻像只是普通地看到他劃破手一樣,立刻恢復到冷靜的神態,分明剛才還是那種蓄勢待發的樣子。而自己甚至在伊角さん離開之後,仍覺得心跳在腦子裡轟鳴。
煙花棒在空中揮舞的迷亂的金色線條中,光的身影鑽過菜畦,悄悄在亮身邊坐下。亮沒有看他,也沒有放下手裡的竹碗;閃爍的焰火忽明忽暗地照亮他的餘光。他忽然隱約看到欄杆上的牽牛花開了,紫色的,薄而柔韌的邊緣迎著即將消逝的晚霞。
過了大約四支煙花的時間,亮終於還是慢慢地握住身邊人的手。他明顯地感受到光輕顫了一下,隨後回握住自己的手指。光的視線落在他臉頰上,像一束有形的燈火;他偏過頭,讓黑髮多垂下來一點。
「⋯⋯牽牛花會在晚上開嗎?」他聽到自己輕輕問。
「都叫做『朝顏』了,怎麼會在晚上——」光看向亮注視的方向,忽然沈默下來。
在他們身邊不遠處,紫色牽牛花在花瓣中央托起瑩白的五角星形狀的花芯。
許久,光抬起頭輕聲說:「也許是受到了天上的彥星和織姫的心願的感召吧。你看,」他靠近了一些,側過臉,指著夜空一側道:「那顆靠下一些的很亮的星就是織姬星,」手指劃到另一邊,「銀河的對面是她的戀人。一個月後,舊曆的七月七是他們相會的日子,但也是銀河漲水的日子,」光繼續說,「所以到時會飛來一群喜鵲,架起橋,讓他們得以約會。」
他從眼角看到光眸中的夜色。順著他的指尖望過去,他從未親眼見過的、傾倒的色粉一樣的星夜中,淺淺的銀河從夏季大三角中間穿過,將光指出的兩顆星遠遠地分隔在兩側。少了城市的燈火,目之所及都是閃爍的天穹,像是面朝星海墜落,視野邊緣沈澱了一層舊相片一樣的暈影。
亮笑道,「⋯⋯這也是佐為さん和你說的?」
光轉過來看向他,「才不是什麼事情都是他告訴我的,我也有自己看書的嘛。」
終於躺在枕頭上的時候,天空已繁星遍佈。和室正對院子的門大開著,薰香的白煙堪堪觸到搖晃的風鈴,初昇的殘月照亮景物的表面,其下仍然留給黑夜。亮在他身邊,呼吸平穩,雙眼靜靜地闔著。已經一週沒有像這樣和他一起入睡了。脑海中又涌现出下午的事——現在想想,反而很慶幸伊角有來找他們;如果當時真就那樣擦槍走火,合宿的時候、白天、在外婆家的倉庫旁邊什麼的⋯⋯想想都覺得太超過。
說起來,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亮都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七天沒有見到他、很想念他的樣子;難道只有自己這麼躁動不安嗎⋯⋯像是頭腦失控了一樣,不是確切地想著具體的事情,只是想和亮做些什麼。但這時候把他吵醒的話——
「進藤?」亮忽然低聲喚道,「睡著了嗎?」
光繃直了身體,有些汗濕的手心貼在腿上,「⋯⋯沒有。」而甫一講完他就後悔了,心虛地不敢轉頭去看,就索性繼續盯著天花板。
亮沈默了一下,又說:「那,稍微抱我一會?」一邊轉過身來側躺著,抬起眼睛看他。
他猝不及防地對上那雙清澈的黑眼睛,喉結來回滾動了一下,聲音順著顱骨傳到他自己耳朵裡,和腦海中擠成一團的各種小場景混在一起——是他想的那個「抱」嗎?雖然非常確定亮要表達的不是這個意思,但這樣的話在這個時候說出來是要做什麼?更何況今日的情況實在不允許——他脫口而出:「不,那個⋯⋯」
隨後就感覺一隻手蓋在他臉上將他推到一邊,再睜開眼的時候,亮已經翻過身背對著他了——居然生氣了嗎!「不、我不是那個意思啊!」其實哪種「抱」都無所謂,他當然想要,想撫摸他、親他,想做更多的事,只是出於非常現實的顧慮——意識到自己的音量,他重新壓低了嗓音對亮的背影解釋:「不是那個意思,是因為怕你會累啦,今天走了很多路,明天還要早起。」見亮沒有任何反應,接著道:「而且這裡的房間完全不隔音的——你聽嘛,是社。」
從相鄰的和室傳來貓科動物一樣的打鼾的聲音。
亮的肩膀似乎放鬆了一些,卻還是沒有轉過來。過了一會兒,只聽他問:「你又怎麼知道一定是社?」
?在意的點好怪。「⋯⋯還不是第一屆北斗盃的特訓住你家,那時候被迫聽了一晚上,就刻進我DNA裡了。」
不知過了多久,睏意逐漸爬上了眼皮。光將手臂輕輕放在亮的腰上,後者轉過來面對著他,額頭抵著他的肩膀,往他胸口縮了縮。光不自覺地微笑,靜靜舒了一口氣,閉上眼。彼此的呼吸消散在若有若無的夜風中。四肢的知覺逐漸變淡,像是漂浮了起來。
迷矇中,忽然聽見亮說:「明天⋯⋯一起去竹島上的神社吧。」
「⋯⋯嗯。」
「想看你穿我買的浴衣。」
「嗯。」原來那一包東西是浴衣啊。
「⋯⋯要一起釣魚。」
「嗯。」小時候確實經常在附近的海邊釣魚。不過亮怎麼會突然想起來⋯⋯釣具都不記得放在哪兒;明早去倉庫找找看好了。
「想看你釣蜘蛛蟹。」
「嗯——欸?」光一下醒了,身體的知覺重新掉回床墊上。幸子難道把這種事情都說出去了嗎?!小時候黑成炭的黑歷史,居然被亮知道了——
「那,就這樣說定了⋯⋯」亮的語調裡明顯帶著笑意,聲音因為睏倦而變得含糊。
須臾,光也安心地放任自己的意識沈入漆黑的睡意。海風的鹹味擾動了溫熱而微苦的盤香,隨風滲進來的月色籠罩在他們身上。
明天醒來的時候,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終わり。
End Notes
這篇的標題「光そへたる朝顔の花」(直譯是「染上光暈的牽牛花」)neta自源氏物語裡的和歌,就是描寫光源氏長得俊美,側顏在黃昏的落日下讓人聯想到染上白露反射的餘暉的月光花←把原句的「夕顔」(月光花)改成「朝顏」(牽牛花)後音節聲調還是很對,就這麼拿過來用了。紫色牽牛花也是本文線索嘛(應該還挺明顯的),花語還有「虛幻的愛」、「愛情關係裡的安全感」的意思。所以中途亮看見的牽牛花都沒有開(因為光亮在鬧彆扭),而最後居然在晚上開了(是不常出現的情況),也是這一天裡角色心情轉變的象征。
↑之前跟讀者交流,發現會有人不明白標題的意思,所以想著要不以後還是都解釋一下?(但這樣會不會顯得很煩/很多餘sos,請告訴我)
打了一整篇的擦邊球最後他倆還是什麼都沒幹,這種感覺太棒了! (?)本意是想寫個吵架→和好的有夏天氛圍的故事。但果然他們要在蒲郡住兩晚,憋了八天,再怎麼能忍,到明晚肯定就滅茶苦茶do了吧!旁邊的和室睡著四個兄déi,亮老師要忍住不能叫出聲音什麼的,想想就刺雞! (停)←總之大家腦補一下第二晚的花火大會和之後doi的過程吧我就不寫了(x)
中文沒有這個稱呼細節上的區別所以提一下:奈瀨全程稱呼藤崎為「明明」,是說的「あかりちゃん」(akari醬)喔!
以及雖然寫了他們是「同齡人」,但伊角比光和亮整整大了四歲欸(不要說出來。
鞏固了光嫌棄愛馬仕等品牌的人設(x
「蘑菇山」與「竹筍鄉」的問題可以百度一下,類似於豆腐腦的甜黨鹹黨之爭。
所以越智是真的很鐘情葡萄味的波子汽水啊(。)
故意植入了下呂和熱海的旅遊廣告(?)致敬一下《時光》裡類似的「大家放假去合宿」和「光帶亮回鄉下老家」的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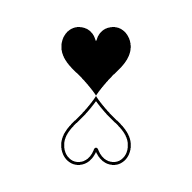
喜欢夏天的故事!!浴衣 花火 牵牛花 流水素面这些夏天的意象都特别有气氛!吵架中还会为对方的魅力动摇的两个人好可爱🥺因为吵架稍稍拉开了距离,更让人觉得dokidoki了…让我很在意的是成人日当天亮为他打耳洞的事……嘶……太色了🙏我很喜欢为对方留下永久的痕迹…脑子里已经在幻想第二天晚上滅茶苦茶do了,既然是夏天 就可以欣赏到亮的黑发贴在脖颈上、汗水顺着光的前胸滑落的景色了吧🙏明明很舒服还要忍着不出声,还会听到隔壁同伴的声音如此之近,亮老师辛苦了😇
是脐橙,明晚他们的姿势一定是脐橙(发出lsp的声音
啊啊感觉标题有解释会比较好!因为老师好像本来就有写长notes的习惯捏,而且看老师的解释会比自己理解诗意很多!
好叻那以後就都解釋一下!謝謝反饋<3(其實標題一直是白白在想,我自己也不會日語qwq 她能找到很多厲害的典故!)
長notes確實⋯⋯是我自己長年以來的毛病x 因為很多腦子裡想的東西不能放到文裡(也沒什麼放進去的必要都是亂七八糟的hhh)所以就只能寫notes,一度會寫千字notes⋯⋯希望沒有煩到hhh
没有烦到!里面有些梗看到会顺手查一下,不过吸收的信息也会有偏,看到notes才有原来是这样的感觉!比如蘑菇山那部分我查到是两个食品牌子就接着往下读了,看注释才明白有这层缘故,如果知道这一层就更有趣啦。
好耶!那以後會稍微提一下這些小心思(順便更新了一下end notes的內容加入了更多解釋(x
可爱!有种小彩蛋的感觉 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