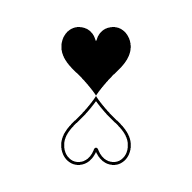一百個夜晚過去。塔矢亮是經常看日曆的人,卻很少把特別的數字圈出來,或者在旁邊的空白裡寫東西,更不會提早一百天開始數日子;於是寫字台上的日曆一直乾乾淨淨,看著像擺設一樣。
冬假的第一天早上,他把日曆挪到了床頭,放在恆溫箱旁邊。那天無風無雪,最後一片深金色的銀杏葉在短暫的陽光下無聲地從黝黑枯瘦的枝頭離開,邊緣僅剩的一道綠色消失在行人的腳下。假期的前一天起,那個衝入他生活裡的魅魔變成琵琶琴身大小的黑色的一團,縮進恆溫箱裏闔上了金綠色的眼睛;待他反應過來自己在算著他睡著的天數的時候,已經過去將近一週。
進藤光是在他坐在地上從衣箱裡找出加絨的長大衣的時候告訴他魅魔需要冬眠的,那時剛剛立冬。
「這已經是我最厚的衣服了,」他對站在一邊饒有興致地研究他的毛衣的魅魔說,「天氣還會變冷,你要不要去買點更暖和的外衣?」
「嘛⋯⋯其實過不了多久我就再不需要出門啦。」進藤聽起來很開心。
亮停頓了一下,放下手裡的大衣,回頭抬起眼睛看他,「為什麼?」
「十二月左右的時候,就要開始冬眠,」進藤抓了抓頭髮,尾巴在小腿上慢慢地捲起又鬆開,「和睡覺差不多吧,只是睡著的時候沒有意識,中間也不會醒過來而已。因為沒法像人類一樣保持穩定的體溫,所以不睡這一覺的話——」
「那,會要多長時間?」
「應該是三四個月,但還是要看明年的氣候⋯⋯總之大概春分時會醒過來的。雖然屋子裡一直很暖和,但可能還是需要一個恆溫箱⋯⋯」他伸直手臂上下左右畫了一圈,「大的、那種。」
亮一直忽略了魅魔是變溫動物的事情;他知道,但是很少去考慮這個特性所導致的進藤和他之間的差異。進藤也必然過慣了每年實際上只有八九個月的生活,他的同類都有同樣的習性,於是把「三四個月」說得輕描淡寫——就像人類覺得晚上就是應該睡覺,但人類養的貓可能不這麼想。
「啊,另外,」進藤忽然在他旁邊坐下來,「醒來之後可能會失憶⋯⋯一段時間,這樣。」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劃了一個大約十釐米寬的間隙,彷彿這能用來表達時間的長短,「不過無論如何魅魔都不可能做出傷害契約者的事。就,麻煩你到時候不管發生什麼都立刻餵我。」
立刻餵他?
第二天放學之後,亮去寵物店訂購了家裡能放下的最大的恆溫箱——展示樣品裡蹲著一隻科莫多巨蜥——這麼想了一下,又去順路的超市買了一盒相模幸福001。
這之後的幾週一直在做期末考試項目,天還暗著的時候出門又在天黑之後才回來,有時直接在鋼琴凳上打盹,黑咖啡當水一樣喝,琴鍵、腸弦、鋼弦、弓和鼓槌的觸感像是黏在了手指上,夢裏都是琴房和學校的場景;他時常覺得忘記了什麼重要的事情,「冬眠」這個詞卻總是被腦海裡的曲譜淹沒。進藤的作息逐漸和他重合,室內的溫暖和長明的燈讓他開始習慣熬夜。他們會在週五晚上或者週六做愛,這之外的時間,進藤就還是那個因為和他「住得很近」所以比較熟絡的、美術學部日本畫專業的學生。
小雪過後一週,第一個不需要忙碌的夜晚,他們在床上做了三次,在浴室又來了一次,終於清洗乾淨身體之後相擁著躺進被窩裏,進藤將臉貼著他肩窩,忽然說:「我會從明天開始睡覺。」亮不記得自己說了什麼,大概是「我知道了」之類的;墜入無意識的黑暗之前,聽到的最後一句話是,「春天見」。
兩個月來第一次被朝陽喚醒,即使閉著眼,腦海裡也是一片濃郁的深金色。他習慣了比進藤早起,習慣了睜眼的時候一片漆黑、身旁有一團模糊的鼓鼓的東西;陽光徑直落在另外半邊幾乎平整的空床上的時候,他以為自己做夢回到了一個人住在這裡的日子。
進藤已經鑽進了恆溫箱裡,半個身子縮在翅膀底下,前爪墊著腦袋,尾巴盤在身前,眼睛闔上,整齊細密的鱗片隨著越來越慢的呼吸像清晨無風的水面一樣微微波動。
亮記得他第一次從人形化為爬行動物的時候。那是他們認識的第三天;接近黃昏,他照例準備去義大利餐廳做兼職琴師,在校門口被進藤攔下來,非要和他一起去,並且不等他說出拒絕的話,便「嘭」地一下變成一隻小蜥蜴趴在他手心眨了眨眼。原本是藏在外衣口袋裡,結果在前台被眼尖的伊藤看見,只得說「新養的守宮,不放心讓他自己在家」,還要做出一副非常保護他的樣子。
「這樣倒是比一個成年人要節省空間。」回家之後,亮環顧房間四周,托著下巴說,「以後你在家就變成守宮好了。」
實際上,更多的時候還是變成家貓大小的龍的型態——「是龍,不是守宮啦!」進藤大聲強調——因為更接近原形,會比較節省魔力。這時候的進藤依然是擁有珈琲色的小小的尖角、黑色覆鱗的帶鉤爪的翅膀、細長的尾和倒心形的尾尖,以及夕陽下的貓眼變石一般的、大而圓的眼睛。變成爬行動物之後,他會尤其喜歡溫暖的地方,即使是夏天。亮需要工作的話,他便坐在人類的肩膀上,試圖用柔軟的髮梢把自己蓋起來;休息時則蜷在臂彎裡,或者臥在胸口,小尾巴晃來晃去,直到亮被撓得太癢,不得不叫停為止。
「所以為什麼冬眠的時候就要這麼大的地方?」亮望著剛剛送貨到家的、半人高的恆溫箱,思考著應該放在哪裏。
「因為我本來就這麼大啊。」進藤看了看箱,像抬空箱子一樣把它抬到了床旁邊,「維持變小的狀態也是要消耗魔力的。」
於是就理所應當地佔用著家裡僅存的一點空地,像一塊石頭一樣一動不動地睡一百天?甚至只是提前了一個多月才告訴他,還要專門為此買一個沒用的大箱子。以及什麼叫「醒來之後可能失憶請立刻餵我」,難道還要從早到晚盯著一個根本不會動的東西等他醒?而且失憶又是怎麼回事?
可他自己的確已經坐在恆溫箱前面望著這個不知死活的生物很久了。音響裡的唱片不知什麼時候停了下來,待機狀態的電子屏幕上,四個藍色的平行四邊形的數字一閃一閃,一點點幽冷的光隱匿在房間的溫暖裏,又在眼前魅魔的翅膀尖端出現。零點差五分。
「大概是死了吧。」亮小聲道。
他站起來,膝蓋發出輕微的響聲,腳和小腿有些麻。走進浴室,對著鏡子看了看自己的頭髮,從旁邊的掛鉤上摘了一根橡皮筋,將一天沒有洗的髮絲高高地束起來——只是一天沒洗,算上今天也只有兩天而已——打開了淋浴噴頭,一邊慢慢脫掉衣服一邊等著水變熱。
管他呢,隨那個傢伙去吧。亮站在有些燙的水流下面,水從狹窄的孔裡出得很急很硬,像老師用來打初學者的手的小木棍——「手腕立起來!」「注意指法!」之類的——他終於對著一睡不起的進藤說出了「死」這個字,莫名地有一種解脫的感覺,比期末演出結束時還要鮮明。本來也不是計畫內會出現在自己生活裡的⋯⋯剛剛適應了他在耳邊從早到晚地聒噪,現在又突然說安靜就安靜下來,捉弄人一樣,不如直接消失算了,自己也可以回到原來一個人住的清淨日子。
只是少了如此頻繁的性生活、沒有人三天兩頭給他做飯、工作的時候沒有一隻小爬行動物趴在身上、在學校不再被突然拍肩膀、不再會聽到「歡迎回家」和「辛苦了」而已,根本沒有什麼可想念的。
關了燈,斜著躺在不大的床中央,閉上眼睛,把自己裹在被子裡。周圍分明什麼都沒有,卻還是覺得吵。腦子裡像關不掉的循環磁帶一樣播放著進藤縮成一團睡在恆溫箱裏的畫面,配上滾動的類似於「他如果真的死了怎麼辦」之類的字樣;暗處一個他不想聽見的聲音認為他只是在說氣話,直到枕頭壓得一邊耳朵疼,不得不翻個身。他不斷告誡自己不要睜眼,否則就會失眠一晚上,後來甚至開始背音階和琶音,從大調到和聲小調到旋律小調又倒著回來;可這些微弱的努力總是被沒完沒了的響亮的循環畫面打斷。如果是他一個人住,這種時候他應該爬起來創作,而不是給自己洗腦「閉著眼總會睡著」;可他現在想的卻是如果進藤光醒了並且失憶了,一定要藉機讓他戴套。
說起來真是氣人,每次作出一副委屈的表情說什麼「我忘記了」、「實在忍不住」之類的,然後保證下次一定戴,卻在清洗的時候還試圖再做一回——可惡,也不知道要弄出來有多麻煩。雖然一直以來也不是由自己來洗就是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睡著的。第二天早上——或者是中午?下午?放假的第一天就關掉了鬧鐘——意識醒來之後,身體還賴在床上,直到實在太餓了,肚子不停地叫,於是只得起來找東西吃。
很好,手邊的空床還是冷的,恆溫箱裏的傢伙還是死氣沈沈的一團黑色。這一天和昨天沒什麼兩樣,天色開始變暗了才發覺好像什麼也沒有做。
他早早地放棄了想要提高創作效率的打算,合上電腦、關掉音響、把沒有翻頁的書摞回原來的樣子,鑽進浴室裡洗頭。水流的聲音下,隱約聽到外面有什麼沈悶的響動。沒有鎖門嗎?不至於吧,上一次出去還是兩天前上班的時候。可能是風太大了,或者書摞得太高掉到地上了,或者誰家又在搬東西也說不定——不會是別的事情。他用力閉著眼,讓小木棍一樣的熱水捋掉頭髮上的泡沫。
分明堅信著外面什麼要緊事都沒有,還是覺得心跳在加快,身體裡有一種想要馬上出去看看的衝動。見鬼。如果不是擔心再這樣下去會由於心慌而暈倒在淋浴房裡成為又一個遺相悲慘的孤獨死案例,他才不會著急擦乾頭髮、隨意裹了一件浴袍就推開門。
恆溫箱裡出現了一點金綠色。那些鱗片開始微弱地、非常緩慢地起伏。亮站在幾步遠的地方,眨了眨眼,甚至忘記關掉浴室的燈。蓋住身體的翅膀顫了顫,鉤爪輕輕伸縮,尾巴向外挪了一點。他覺得胸口被自己的呼吸堵住了,肋骨和裡面的肺葉發痛,眼睛周圍也開始變得酸澀。
浴室的黃色光線太暗了;應該去打開房間的燈,開關就在恆溫箱旁邊。然後打開恆溫箱的燈,看看剛才到底是不是幻覺。可他動不了,像被什麼附身一樣。
「大概春分時會醒過來的。」——是這麼說的吧。亮隱約記得自己所想像的場景是三月中下旬的晴朗的下午,被陽光曬著慢慢地醒來,看到那雙許久未見的眼睛回望著自己。然後他們會像進藤希望的那樣再一次做愛,找回那些久違的感覺,直到忘了時間。
髮梢的水順著脖子爬到浴袍裏,將他拽回昏暗的現實。
「嘭」一聲。翅膀撞到恆溫箱的側壁,似乎想要伸展開。
突然清醒過來,反手拍掉浴室照明的開關,藉著腿腳的記憶大步走到床邊打開屋頂的燈,眼睛被刺得緊緊閉上。亮想起那盒嶄新的相模幸福001在枕頭下面,和改錐放在一起;這麼說一點也不浪漫,但他哪個都不想立刻用到。頭髮裏殘餘的水打濕了小塊的床單。
再次看向恆溫箱的時候,那雙熾烈的眸子已經完全張開。黑色的爬行類半個身子立起來探出箱子外面,角的顏色由陰鬱的灰逐漸變得溫暖,耳後的棘與雙翼一起緩緩張開。振顫的鱗片反射節能燈的白光,如同河冰開化露出的波瀾。
在亮能夠看清之前,它從過於狹小的箱子裡躍出來,翅膀一闔一展,一陣風掠過去,那雙熟悉的眼瞳便已經佔據了他全部的視野,豎瞳在強光下收縮,似乎在辨識眼前的生物。虹膜的紋理像粼粼的銀杏葉海。有東西扣住他的手腕,是乾燥圓滑的龍鱗的觸感。潮濕的黑髮涼涼地墊在腦後,他聽見日曆被掃落到地上的聲音。
尾尖挑開了浴袍的帶子。
「⋯⋯進藤!等、一下⋯⋯」有冇搞錯,難道要這樣做嗎⋯⋯雖說答應了醒來後會立刻喂他,可是,以龍的型態?
即使相隔數月,他還是記得生出鱗片的粗大的性器在體內衝撞的感覺⋯⋯畢竟有好幾次,進藤的身體都在做愛時無法控制地異化——那還僅僅是魅魔的能力失控而魔化的類人形,而面前是一條剛甦醒的龍——不行的!腦中的畫面讓他臉上燙得發麻——應該說能夠想像出這種場景本身就已經足夠有問題了——他不停地搖頭,抬起膝蓋,掙扎著試圖擺脫哪怕任何一點束縛,髮絲橫落在臉上,他在模糊的黑色之間再次與那雙眼睛對視。層疊的鱗片逐次隆起,龍的頭緩慢地旋轉了一些,目光的焦點外,從模糊的咽喉深處傳來低沈而厚重的振顫。眼週的細鱗驀地躍動,半透明的瞬膜漲潮似地滑過眼球,又很快退回來。
話說,進藤他現在⋯⋯是失憶了?
亮定了定神,雖然魅魔的原型有些獵奇、怪誕甚至可怖,但眼前的龐大生物猶豫的神態仍能讓他聯想到進藤一開始出入人類世界時的樣子,比如⋯⋯第一次來歌舞伎町接自己下班,見到街口放滿杜蕾斯的自動販賣機時那雙琥珀色的眼睛裡那困惑和天真的神情,站在人類的視角,這甚至有些⋯⋯可愛。他忽然覺得無需害怕了。
⋯⋯不,一定是直視了這雙眼睛的緣故!就算是龍的型態,這依然是蠱惑人心的魅魔的眼睛。
亮側過頭去,緊閉上眼。
加之進藤現在還未記起他們的關係⋯⋯不就回到了類似於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嗎?僅僅將自己作為食物的狩獵——
纏捲的思緒被嘴唇上乾燥而溫暖的觸感蓋住,柔軟的、熟悉的、令他安心的。亮悄悄睜開眼,看到的是屬於人類的形狀好看的唇瓣。金黃的髮梢撓著他的眼角,剛才的一切像是一場半真半假的夢,只有手腕上的紅痕提醒著他這三個多月的等待。他試探著抬起手,指尖繞著珈琲色的小小尖角,穿過眼前人淺色與深色的髮絲,沿著耳後停留在後頸微微凸起的骨節上。那裡覆蓋了很細的鱗,隨他的呼吸而伸縮。親吻越來越焦急地落在下頜、喉結、頸窩,又回到唇間,繞上他的舌頭。他感到雙腿被慢而重地壓到大開,骨麟的觸感一排排印在大腿內側。
「別、稍微⋯⋯」
——太快了。剛從一百天的獨處裡走出來,他還沒有原諒進藤過分的來去自如,卻要立刻任這個六親不認的魅魔擺佈,這甚至不足以被稱為合姦。
可他清楚地感到身體在做出回應,被觸碰的地方有些癢、輕輕地變熱,又匯聚到下面讓他腹部發緊——見鬼的契約,那根本就是個賣身契。
「哈、嗯⋯⋯」
涎液在耳邊「噠」一聲落到床單上的時候,亮才記得呼吸,又被口中藤蔓似的舌堵回去;他無法忽視地感到下體漲得發熱,分不清魅魔的尾巴和指爪哪個在擺弄他的性器、哪個在玩他的穴口。他在進藤短暫地允許他換氣的間隙裡嘗試推開撫摸他下半身的東西,卻隱約看到倒心形的尾尖從那裡牽出黏膩的絲來。
既想要讓自己的理智反駁自己的身體,又要用身體對抗魅魔的掌控;可他哪個都做不到。他忽然想起自己確實地想念過對方的陪伴,平日的生活也好,床上也好;他會想起進藤說話的語氣、身上好聞的氣味,他用嘴、手或尾巴撫慰自己的感覺,而那雙手現在正隔著浴袍抓住他一邊的薄薄的乳肉,另一邊暴露在空氣裡,粉紅的乳頭被壓在靈巧的舌下面揉搓。
「啊⋯⋯嗯、好癢⋯⋯」他試圖向後躲,本能卻又讓他靠得更近,「呃啊⋯⋯」肉粒被不輕不重地咬住,每動一下都隱隱地酥麻。
「喂,你⋯⋯」久違的略微沙啞的人聲從胸口傳來,「竟然已經準備好了啊。」
準備好⋯⋯什麼?「唔、等一下!還沒有——呃、呃嗯——」
他的手落在枕邊攢緊那處的被單,分不清是害怕或是興奮,又或是單純想叫他戴上新買的套。後穴被侵入帶來的酸脹感讓他下意識地動了動腰,又很快被鉗住,生硬地按下去。腔道緊緊纏上進入身體的異物,穴口包裹著抽插的柱身,將它吸吮得水光一片。看似無意的頂弄下,體內那一點重新被喚起,他無法抑制口中的哭叫。眼底發酸,餘光的視線泛起霧汽,他抬起手臂擋住了自己的視線。
不完全的、搖晃的黑暗中,身體內外受到的刺激變得格外鮮明。亮發覺自己心裡藏了一種昏沈的慶幸;進藤看不到他的臉,看不到他的眼神,他只需躲閃他自己無法承認的屈辱的愉悅。
沒事的⋯⋯沒事,只要這樣餵他就好,很快,馬上就會結束⋯⋯
「⋯⋯喜歡我。」
恍然間,手腕被握住,用不容置疑的力度壓在耳側,迷濛的視線猝然對上那個人橄欖色的眼睛,灑在臉上的是急喘的氣音。
「你明明,喜歡我這樣做。為什麼,在哭?」
光覺得困惑,心裡像是有一團線酸澀地纏在一起,分不清是自己的情緒還是純粹和宿主共了情。眼前的人是他的契約者,年輕青澀的肉體、清秀美麗的面龐、哭泣時潮紅的臉頰和濕潤的淚眼,被慾望折磨的樣子完美符合魅魔世界對「墮落之物」的刻板審美,漂亮得要人命。
性器上因為休眠而收攏的鱗片被許久沒有這樣使用過的腸道緊緊壓在一起,刺激之下本能地又有了張開的跡象。手掌下的腰身顫抖著、徒勞地扭動,光潔的皮膚上印下杏花般的痕跡,像是要逃脫,卻只讓他陷得更深。光感受到身下的人類每一根神經都興奮起來,目光渙散,雙唇像索吻似地張開著;他在享受後穴裏飽脹的感覺和胸口刺撓的撫弄,甚至自己對他身體的禁錮。可他心裏的情緒卻像滿是泡沫的海水灌進來,那些眼淚盡是委屈。
是自己做得不夠好嗎?才剛睡醒,所以有些生疏⋯⋯?
身後的雙翼展開,翅膀寬大的陰影裏,細密的汗珠和未乾的淚痕隱約閃爍。光俯下身去吻他的眼淚,含住殷紅的雙唇,舌尖在口腔中輕輕攪動,陰莖因而在濕熱的身體裏埋得更深。光察覺到他的躲閃,他的手腕無力地試圖抽離,雙腿在空中緊綳著,腰扭動著想要退開,每次的掙扎只讓柔軟的内壁更加敏感地收縮,漲紅的前端已經滲出液體,隨著頂弄在小腹上一晃一晃。
「嗯、嗯啊!進藤,別⋯⋯」
光不明白面前的人爲什麽這樣抗拒他身體的感受。由契約而傳遞到他心裏的苦澀的感覺堵在胸口,他想將這個美好的人罩在身下,給他最溫柔的撫摸和親吻,可這樣受到虐待似的表情讓他移不開目光,帶著哭腔的呻吟、含糊的拒絕的話與顫抖著灼燒的呼吸一起摩挲著他的耳廓,從額頭到尖角的根部都熱起來,尾尖像蛇一樣纏住他張開的大腿壓在身側,將他的身體拉近,細嫩的皮肉被勒得鼓脹,鱗片在白净的皮膚上磨出紅痕。
想并攏雙腿的被用力拽開,性器重重地釘進去,平坦的小腹被頂得鼓起。
「嗯哈——!呃、啊⋯⋯不,唔唔⋯⋯」
上面和下面的水聲蓋過被深吻堵住的呻吟,光憑藉本能衝撞對方體内的那一點,微微痙攣的腸壁推擠、挽留他,綫條流暢的長腿不自覺地分得更開,纖瘦的腰腹從床單上弓起,他的宿主在許久的等待後的第一次高潮裏緊緊將他箍在體内,擡起頭張著嘴迎合他的吻,粉色的陰莖將白濁濺在自己身上。
亮覺得整個身體像一灘被一層層打開表面的奶油、露出了戚風胚的蛋糕。嘴裏被濕黏的親吻填滿,下頜有些酸痛,津液從淚痕上流過,破碎的聲音從唇間擠出來,剩餘的盡數灌回喉嚨裏;手臂被壓高了太久,骨頭和肌肉發涼,幾乎失去知覺,仍然腫脹著的乳頭偶爾碰到進藤的胸口,激起一陣刺痛。
初嘗到一點飽足,光覺得每塊鱗片的根部都燥熱起來。身下的人擡起渙散的目光,黑髮盤捲在白皙的臉龐兩側,散開在淺色的床單上。
「名字⋯⋯」光在他耳邊呢喃。
這樣煽情的景象似乎和腦海裏某些已知的東西重合,引誘著光更多地取悅他。
「⋯⋯告訴我、名字⋯⋯」
在高潮的餘韻裏像失血似地暈眩了一瞬,聽見低啞的嗓音擊在鼓膜上,亮隨即清醒過來。
在床上說自己的名字,誰會做這種事⋯⋯而且面前的魅魔已經不認識自己,難道說出名字就能讓他醒過來嗎?他等了這麼久,在夜裡小心地想像著久別重逢的第一次,卻是這樣粗暴的對待⋯⋯
光的性器仍然埋在他裏面,他有些難耐地想要夾緊雙腿,乳尖卻被一片濕熱裹住,那裏已經變得酥麻,被輕扯的疼痛變得針一樣鮮明。魅魔的手從小腹爬上來,伸進腰下,順著脊柱來回撫摸,尖銳的指爪隱約碰到皮膚。
「不、唔⋯⋯」
雙唇被輕輕含著,舌頭舔舐紅腫的唇瓣,在齒列間打轉,一點點撬開他的嘴。
「告訴我?」他聽見進藤在親吻間沙啞地說,「只是想讓你、舒服⋯⋯」
溫柔的語氣使亮的身體過電般地顫。第一次的時候就是這樣,嘴上想徵得他的同意,卻已經自説自話地做了所有的事⋯⋯比起這個,他感覺到魅魔的體液隨著下身的頂撞一點點灌入,肉體不得不爲他打開,從每個接觸的地方傳來的快感堆叠在一起,那一點理智像風浪間的一座孤島,身體深處的記憶被喚起,像是出於本能一樣貪婪地享受著。
不行,一定有什麽辦法能讓這一切停下——
「至少也⋯⋯啊、給我戴個套啊⋯⋯!」
聽見他的話,光擡起頭來,盯著他的嘴唇。
原來是在意這種事嗎?自己的契約者竟然是這麼傳統嚴肅的個性?從他身體上直白的反應還真看不出來⋯⋯
小學時就瞭解到人類進行性行為時會使用「安全套」來防止產生後代,直到現在仍然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失敗的發明——不能控制是否生育,就要爲了不必負擔照顧幼崽的壓力而犧牲做愛的快感,真是有夠弱的物種欸。而且不管怎樣,魅魔以進食爲目的和人類性交,自己面前的還是男性,是無論如何不會產生後代的。與其在乎這種莫須有的顧慮,更重要的果然還是——
「可這樣你會不舒服。」他看向亮的眼睛。
意思是自己會吃不到那麽多飯。
「嘖⋯⋯每次都有藉口。」身下的人皺起眉頭,「給我戴上,要麽就下去。」
光看他瞪著自己,眼角還紅著,完全沒什麽威懾力,但語氣好像真的很不滿。既然會這麽堅持……大概是他真的更喜歡那樣?或許人類確實發明出了體驗好一點的避孕套也説不定。
從枕頭下面拿出來的一片硅膠緊巴巴地裹在性器上。鱗片的粗糲感被緩和了許多,鮮明的、濕黏的撞擊聲裹挾著滑膩的快感,這樣的交合尚且説不上溫柔,卻更像普通戀人之間的溫存。聽著自己發出的不輕不重的呻吟,亮想,這樣他至少能夠保持相對的清醒。
「呃⋯⋯!」
他沉溺在熱浪似的歡愉裏,光低沉的喘息在他身前起伏。下一秒,便覺得腿被抬高,魅魔的上臂正壓著他,雙腿被彎折到胸前。
「做什麼——呀啊!」
那條尾巴纏緊了大腿内側的皮膚,酥麻的感覺匯聚到下身。亮將眼睛睜開一條縫,看見琥珀色的雙眸化成一團熾烈的火焰,瞳孔縮得細長;而他自己股縫間的穴口被各種液體裹著,露骨的景致就這樣暴露在眼前,陰莖直直地貼在被頂出性器形狀的小腹上,已經釋放過的痕跡順著皮膚流下,前面未曾受到過任何撫慰,又再次有了擡頭的跡象。
驀地,像從高處墜落一般,感官重新被拉扯著無限地放大,腸壁似乎再次碰到那些春藥一樣的液體,努力維持了不久的理智又變得搖搖欲墜。
「嗯呀、唔。不,這樣不行⋯⋯嗯、嗯啊⋯⋯」
體內深埋著的那根東西抽出來一半,看見張開的鱗片已經把薄薄的套劃破,精液從無數條裂口裏漏出來。
「就知道這個不行嘛。」光索性將那片乳膠剝下來扔到一邊。「質量也太差了……」
亮在心裏翻了個白眼,又羞又憤地斜睨那非人的物什。
可他很快就沒有心思胡思亂想了。沒了那層阻隔,看見眼前的陰莖仍然猙獰地挺立著,沾滿精液的肉棒重新進入他,他的手臂被光扯著,背不禁向後弓起,整個人像個懸空的鞦韆。光的下腹壓著他的臀肉,身下滿是攪奶油似的水聲。
「笨蛋⋯⋯啊、哈、哈啊,那裡,嗯!別——」
「嘖。」
亮搖著頭,剛想要說什麼,又被一根又硬又涼的東西插了滿嘴。
「唔——」
進藤用尾尖撥弄著他的舌頭,任何聲音從喉嚨裏出來,都變成顫抖的喘息和嬌吟。
「不要⋯⋯拒絕我。」
光微皺著眉,濕潤的眼睛盯著他一眨一眨,陌生又近乎飢餓地觀察他的表情,從眼角到嘴唇、胸口,順著腰腹向下,視綫像羽毛的尖端掠過他裸露的肌膚。在這樣的注視下,身體不受控地顫。
抬起模糊的視綫,將注意力放到口中的異物上,小心地吮吸。眼看著那根覆滿鱗片的不屬於人類的器官一點點向他的口中擠壓、抽插,頭腦中好像有什麼在融化,他不禁聯想到一些更情色的場面。越來越頻繁而劇烈的刺激搖晃得他無法再分心去剋制自己,僅存的一點羞恥心在身下的撞擊和胸前的逗弄之下,彷彿一團雲霧一樣被衝散了。
用浸滿情慾的熱烈的目光望著他,注視著他含吸著自己尾巴失神的表情,光在能夠思考之前,雙臂已經將掌心下的身體翻了個面,染上哭腔的驚叫傳進耳朵裏,翅膀不自覺地抖了抖。一截溫軟的腰塌下去,他身下的人類無法用手臂支撐住上半身的重量,臉頰側著壓在揉皺的床單上,黑髮向四面流淌。他撛著他的手腕反拽向自己,讓宿主抬起他的頭顱,抻直那段好看的脖頸,長尾順著舌根探進深處。
「啊、嗯、唔呃⋯⋯」
身下人雙腿蹭著床單,為了保持平衡而把腰彎得更深。「呃唔!」他適時地向前一頂,便聽見人類悶哼地叫了一聲,同時感到深處被他淫褻著肏開的小嘴神經質地抽搐起來,已經高潮過一次的媚肉含著陰莖上立起的鱗片顫抖。
亮迷蒙地睜著眼,感到下腹被那根東西插得一鼓一鼓,在體內緊窄的小口上來回磨蹭,嘴裏全是鱗片的玩意挑逗似地戳著他的咽喉部,一下一下讓他吞得更深。
「嗯⋯⋯」
雙重刺激下,感官的體驗太過淫靡,被非人的生物像飛機杯一樣使用著,卻貪戀每一下頂撞開那一點的快感,甚至還想要更多⋯⋯
光尖長的指爪嵌進細嫩的腰肉,穴口緊跟著絞緊,柱身上凸起的青筋和密集的鱗片一同碾磨著腸壁,汎起熒光的橙紅色淫紋從下腹順著堅硬的性器一圈一圈地生長,蔓延進那個被迫接納著它的地方。
「呃!」等等⋯⋯!
身後的撞擊忽然頓住,感到肉棒卡在那個緊窄的地方抽動了一下。
「唔、不、唔嗯——」察覺到光快要到達,他用力搖著頭,試圖掙脫前後的雙重制錮,可是尾巴已經壓著舌面頂過了喉嚨,頭部無法再自如地動,發現自己無論上下都被完全地姦淫著侵犯,溢出的驚叫變成無助的呻吟。
光握著他的腰向後按,有炙熱的液體一股股灌進肚子,情色的飽脹感使他不自覺地扭動著身體。
「哈,別動。」
龜頭捅過結腸口姦弄著那處小嘴的感覺讓亮感到不安,哭叫卻被魅魔的尾巴堵在喉嚨裏,自己的性器在腿間搖晃,稀薄的精液甩得到處都是。
那根魔化的陰莖前端腫脹,像生了倒刺一般牢牢地嵌著,每動一下就帶來甜蜜的刺痛。光死死地掐著他的腰,讓他沒有一點拒絕的餘地。
「唔呃、嗯嗯⋯⋯嗚,不、行⋯⋯」
喉嚨裡的異物終於退出,魅魔的長尾轉而卷上他的腿讓它們保持分開,彎折成適合授精的姿勢。
光貼上來,從後面擁著他,壓著在他身體裡繼續頂弄著射精,一邊雙手伸進他的胸口和床單的間隙去揉弄他的乳尖,將角貼在他肩胛骨上蹭,伏在他身上啃吻他的耳垂。
被注入精液的腹部壓迫在床面上,他不自覺地臀部擡高來讓自己舒服一些,也讓肆虐的性器插入得更深;乳尖被揉得酥麻,乳孔都被玩弄到張開,緊貼在柔軟的床單上磨蹭,同時感到貫穿他的堅硬肉柱堵著那些粘膩的液體又開始動作。
「嗯、嗯啊,不要⋯⋯太、滿了⋯⋯哈⋯⋯」
光注視著身下人殷紅的眼角,只見那雙濕潤的眼眸正失神地上翻,一截舌頭淫亂地探出來,已經是全然爲他打開的樣子。射精的時候感到裹著他下面的那圈嫩肉正一縮一縮地親吻著龜頭。不禁又壞心眼地在那來回頂弄了幾下,結局是讓宿主身前的性器也緊跟著高潮,體液順著白皙的大腿滴墜在床單上。
維持了一會這樣的姿勢,等到第一波精液盡數注入,他便將宿主翻過來,托起他的後腦親吻,讓性器在柔軟的甬道裏轉了半圈,使他們的身體隨著深吻一起嵌得更緊。
「唔、唔嗯⋯⋯哈⋯⋯呃哈!」
兩股急促的心跳清晰地在腹腔内的血管裏振動,亮全部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身體深處的的小口,陰莖在這裡的每一次姦弄都讓他觸電一般顫抖,不自覺地勾起脚趾,大腿内側摩挲著進藤的腰。他已經無暇回應魅魔靈活的唇舌,只是張著嘴任他舔食,感受著體內不停湧出的飽脹感,無意識地發出煽情的鼻音。
許久,光感到身體裏的燥熱開始消退,鱗片有了收縮的跡象。長達三個月的飢餓之後初次感到飽足,這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自己將宿主折騰成什麽樣子——人類仰面躺在一片狼藉之間,雙腿勉强勾著他的手臂,釋放過多次的花莖透出可憐的紅色,挺立著貼在灌滿精液的突起的小腹上,水色的眼眸失神地上翻,雙唇鬆軟地張開,涎液在露出的小舌上閃爍,口中含糊地吐出凑不成詞句的音節。望著眼前這幅景象,他握著宿主的腰進入到最深,龜頭重新肏開內裏被灌滿的口,在那裡抽动几下,完成又一次射精,頂部膨脹著,淫邪的突起把那圈嫩肉撐開,只見身下人的眼睛蒙上更多的霧,本能地哼叫著發出不知意味的呻吟,掌中的腰徒勞地掙動了下,緊貼著腹部的肉棒吐出近乎透明的清液,感到包裹他的甬道和小嘴顫抖著收縮,可憐地含下了最後一波濃精。
一陣久違的香氣讓亮從漆黑的睡眠裏浮上來。緊接著,爬滿全身的酸痛像鬧鐘一樣充斥了他的知覺。他揉了揉眼睛,試圖坐起來,又很快放棄了。床邊的保溫箱空著,厨房裏有個許久不見的人影,朝他轉過頭來。
亮覺得這副場面有强烈的既視感。
「喂,你是只會做這一種東西嗎?」
光本想溫柔貼心地問早安,然後好好為昨晚道歉,卻被這個摸不着頭腦的問題搶了話。身爲魅魔怎麽可能只會做煎蛋餅!平時給塔矢做的早飯也會盡量換各種花樣,煎蛋餅這麽普通的東西,出現的次數屈指可數。
不過,好像確實每次出現,都是在自覺做得很過分之後。 前兩次只是冰箱裏碰巧只有那一點食材,不過這份料理確實總能讓他開心一點?
「對不起。」他關了火,斟酌著說,「多虧你,這次冬眠也順利度過了。昨晚真是辛苦了,今天正好也是休息日⋯⋯」
亮記得那條「醒來之後請立刻餵我」的要求。他還沒有完全醒過來,沒什麽心思聽這個魅魔講話。溫熱的煎蛋與火腿的味道飄蕩在四周,他想起每次伴著這樣的香味悠悠轉醒,進藤低沉輕緩的聲音落在耳邊,如果忽略自己連床都起不來這件事,完全就是模板一樣的甜蜜早晨。
「很懷念⋯⋯」團成一個包的被窩裡傳來亮悶悶的聲音,「⋯⋯小時候,每次從診所回來,媽媽也會買個風車給我。」
「是怎樣的風車呢。」
亮的腦海中順時浮現出四片鮮亮的色彩,伴隨自行車的鈴聲隨風搖晃,隨後在一片灰色裡戛然而止。
現在早就不知道放到哪去了,那種東西,已經扔掉了也説不定⋯⋯
「咦,你都把這裡的東西放哪去了?趁我睡覺的時候⋯⋯」
在上下左右翻找調味品的間隙,光回過頭,看見春日近午的陽光流進房間,床上的人正若有所思地望著高處一片虛無的暖色,細小的灰塵飄蕩著,墨色的眼睛像清晨的雨水般閃爍。光忽然意識到自己對他的過往的瞭解仍然僅限於最初爲了考試取得的資料上的那一部分,現在的相處讓他相當滿足,以至於從未想過黑道少爺會有什麽樣的過往。
「⋯⋯你剛才說,每次從診所回來?」難道是自小多病,或是經常受傷⋯⋯?
昨晚帶著抽泣的呻吟在腦海裏仍然清晰,現在看來,自己確實對他太粗暴了,才會讓他記起這麽痛苦的事,人類是多麼弱小的生物⋯⋯想到資料裏寫他爲了追求音樂獨自離家,又看看這間狹小的公寓,忽然覺得心疼起來——
「因爲父親經常需要看醫生,槍傷之類的,有熟識的診所。」
「⋯⋯這樣。」關掉燃氣灶,光將蛋餅盛進盤子,若有所思,「那來吃早飯吧?」
À suiv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