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奏:2003年的夏天
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的時候,客艙內的空氣似乎一下變得悶濕。光坐直起來,揉了揉眼睛。恍惚間看見遠處的航站樓像一塊巨大的鰻魚——剛用過飛機餐,怎地好像又餓了?
從小窗望出去。明明還不到七點,天色卻灰暗得能擰出渾水來。霧濛濛的空氣中,跑道的燈從視線裡滑過,視線所及,飛機上和地勤的制服上都寫著漢字,乍看之下和羽田機場也沒什麼不同。
他進藤光,在十六歲的夏天,第一次離開日本的國土,並且是一個人在旅行。
今年五月的北斗盃,舉辦地就在北京。由於要備戰本因坊戰循環圈的對局,他和亮都沒有參加這次予選,只是在棋院看了轉播。
多虧了秀英,如果去年的誤會沒有解開,他這次肯定會放棄五月在日本的賽程,去和高永夏一決勝負。當然,以他和亮這樣的年紀打入三大頭銜的循環圈,比起青少年限定的國際賽事,和日本最頂尖的高段棋手對弈的機會才是更讓人趨之若鶩的。
可不知為何,在他心裡,「北斗盃」這三個字還是揮之不去,像個無法抹掉的記號。
「早上好。」
「喔,進藤君來了。」
推開轉播室的門,看見天野先生從亮對面的座位上站起身,同他打了招呼。在場的還有一些編輯部的人和幾個院生。屏幕上是空的棋盤。
「塔矢君,你們今年都打入了本因坊循環圈,下週編輯部可能會對你們其中一人做個專題采訪。到時候越智君他們也回來了。」
「好的,到時麻煩您安排。」
第一局是中國對韓國,鏡頭停在主將的棋盤上。電視的音量被調高了一些,亮從棋盤上取走那罐黑子。光也在對面落座,打開自己面前白子的棋笥。
其實不用怎麼糾結,就在「北斗盃」和「本因坊」之間做出了選擇。可循環賽的結果並不理想。本因坊的頭銜對他來說自然舉足輕重,但即使認真備戰、全力以赴,對上高段棋手時仍屢吃敗仗。在對手豐富的經驗面前,他的那點棋感幾乎毫無用武之地。光不會自大到認為他能立刻獲得本因坊的挑戰權,可一直輸棋的感覺太不好受,他的心情也逐漸與一年前的不甘心重疊。
對局開始,亮擺上了第一枚黑子。
去年北斗盃的主將戰,光坐在高永夏對面,以敵對的心態去拆解他的每一手棋。而現在跟著螢幕上他的手落下一枚枚白子,置身事外地觀察他的思路,發現他們其實沒有那麽多不同。
「『拆』嗎?那可以在這裡『斷』,」亮抓取下一枚黑子,懸在所指的位置上,「下方打吃,互換兩個角的先手。」
光緊跟著擺上他所說的那幾步,又說,「可如果先不理這一手,而是在這裡『長』出去?」
「太不謹慎了吧。我順著『貼』,三手之內就能和前面布好的這一子接應上。」
「那我點在這裡好了,你還能是三手之內?」
聞言,亮皺起眉,幾個院生聽著他們的談話,面露懼色。
「說什麼呢?拆東牆補西牆的,也太勉強了。」
然而幾手之後,高永夏的白子確確實實落在了光所提到的位置。
「你看,我説什麽來著?」
亮低頭思索了一下。「可他先在角上補過一手來牽制黑棋的優勢,還是比你剛才那樣穩妥許多。」
光這一年裡和高永夏在「幽玄之間」下了不少棋,也研究過他的棋譜。同為秀策的學生與模仿者,他們之間的輸贏大抵是四六開。他知道自己還有不足,卻也找不出應對的方法。
對局結束,黑輸三目半。那傢伙還是贏了,並且贏得和去年一樣漂亮。
熒幕暗下去的時候,當時偶然聽到的一句話忽然在腦海裡響起——
「『秀策』,是誰啊?以前的棋士嗎?」
高永夏那時是故意出言不遜來挑釁,等這層坎邁過去,才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彼時在場的除了那一小部分棋手之外,其餘的人表現出的不是對他的話贊成或否定,而是疑惑,繼而漠不關心。
每天以棋手的身份所面對的人,媒體、贊助商、觀眾,即使是同樣與圍棋有切身的利益關係的人,也只能窺見這個職業的冰山一角。
已經兩年了,逐漸發覺好像也做不了什麼。
對無法向任何人證明佐為存在的自己,對無法達到那個高度的自己,感到了極度的懊惱。
到底,該怎麼辦呢⋯⋯
「——可惡啊!今年夏天必須再去好好和趙石下幾局。」
今年日本隊的大將、副將、三將依次是社、越智和和谷,結果敗于中韓。和谷這傢伙從北京回來之後好像很不甘心,沒頭沒尾地發簡訊過來說要吃飯,結果敲了自己一頓回轉壽司。
「夏天?你夏休的時候要去中國棋院踢館啊?」
「嗝〜沒那麼嚴重啦。」和谷放下筷子,擺了擺手,「只是去切磋一下,切、磋~
「伊角學長已經和楊海先生說好,今年七月會再去進修,我正好跟著去嘛。在北京住個幾週,可以常去棋院裡跟中國人對弈,順便也能觀光一下咯。」
要去中國啊⋯⋯自從前年伊角學長從北京回來,時而聽他提起在那邊的見聞。這下又聽和谷說起,總有些好奇中國棋院是怎樣的地方,就提出也要一起去。
「好啊!你看下機票吧,七月十一日,航班號是CA1252。沒問題的話我讓伊角學長通知旅店那邊加個床位。」
於是撥打了全日空的訂票熱線,卻被告知與他們同一趟的航班已經客滿,只好訂了晚一週的班次過去。
「——什麼?阿光要去北京?!」
週末回家拿行李箱的時候,聽美津子大呼道。
「嗯,昨天剛買好機票。」
「怎麼會,阿光可還沒有出過國啊,怎麼突然要到這麼遠的地方,會不會⋯⋯」
「哎呀不會的,我跟朋友一起去啦,而且中國不就在旁邊嗎?媽你總是瞎操心欸。」
「那麼旅行證件、旅行證件⋯⋯阿光還沒有成年,護照是要怎麼申請啊⋯⋯」
「欸。」光握起拳頭在手掌心敲了一下,「對喔,還要用到護照。」
「啊⋯⋯這可真讓人擔心。」美津子捧著臉,憂心忡忡地看著他,「媽媽也只是和爸爸去夏威夷的時候辦過一次旅行證件而已。那次是為了度蜜月,所以申請的理由是觀光,但阿光這個,算什麼好呢⋯⋯」
「要不就寫去中國棋院觀光吧。」
塔矢這傢伙似乎也挺常去海外旅行的。
年初在棋會所見面時,他有提起去了深圳和父母一起過年,返程時由於要轉機,還在上海逗留了幾天。
「這個,是給你的。」
「啊?」
「度假的伴手禮。」
這傢伙真是夠客氣的欸。
左右瞧瞧,似乎市河、蘆原和一些常客都多少有收到些小禮物。好像就是一種禮節性的問候,不是什麽特殊對待。
接過亮遞來的盒子,正面畫著荷花的圖案。翻到反面,在密密麻麻的小字中認出了營養值表。
「這是⋯⋯吃的嗎?」
「是『冰糕』,上海的特產點心。」
聽著亮把這兩個漢字念出來,還是沒明白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白色的、看起來像冰淇淋,名字也聽起來像冰淇淋。
「所以,這是⋯⋯天熱的時候吃的?要放冰箱嗎?」
「應該⋯⋯不用吧?」亮愣了一下,「就是這麼常溫擺在店裡的。上海好像也沒有很熱,和東京差不多。」似乎想起了什麼,又補充道,「不過深圳確實是很熱呢,這個新年假期簡直過得像夏天一樣。」
「哈?但這倆是在同一個國家吧。」
「是啊,有南北的溫差而已。鹿兒島和北海道不也是一個國家嗎?」
「唔⋯⋯可是一月的鹿兒島還沒有熱到會像夏天的程度。」
「⋯⋯因為深圳在,比鹿兒島緯度更低的地方。」
「緯度更低?就是更南部的意思?難道,在夏威夷附近?」
「不是。」
「那是在關島?」
「怎麼可能⋯⋯」亮的語氣有些不耐,「唉,你趕緊抓子吧。」
所以中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啊⋯⋯?對這個國家的瞭解,也大都是和圍棋有關,或許還有中華料理?熊貓?長城?剛才在飛機上有看一點旅行指南的介紹,三十倍於日本的領土、十倍的人口⋯⋯對這樣的數字根本沒有概念,從小在東京生活,就已經覺得日本的人有夠多。
「東京」、「北京」,「京」的漢字也是同一個喔。明明讀音不同,卻都是國都的意思。
那麼從東京到北京,算不算是一種「上京」⋯⋯?
從海關出來,順利地取到了行李,光找一個角落站住。
將扇子放在一邊,從箱子裡取出隨身的香體噴霧來用。聞到熟悉的水果氣味,飛機上積攢的睏倦也一掃而空。[1]
説好一落地就與和谷聯係,於是掏出手機,打開了國際漫游。
沒有在海外旅行的經驗,可是聽和谷說通話的資費會很貴。現在可是自力更生了,每個月還有那麼多房租要交,果然還是得節省一點。
「已經落地取到行李了。要怎麽去住的地方?或者你現在有空嗎?直接叫上伊角學長一起去吃飯也行。」光撰寫了郵件按下發送。
捏著手機等了幾分鐘,行李轉臺週圍的人數已經少了一半,不見有回復。
大概還沒看見吧,大週五晚上的,他們說不定去哪玩了?
跟著顯眼的「Taxi」字樣和圖標,走出機場的時候,天空已經下起雨,沈重的熱氣隨著雨水像一條巨大的棉被撲面而來。
濕熱的季節,灰色的天際線——呼,這不還是和東京差不多嘛。
在雨裡東奔西跑地找了一圈,才看見等候計程車的隊尾。順著工作人員的指示走到一輛深紅色小汽車前面。剛要拉開車門,卻對上一個男人震驚的表情。
嗯?等等,為什麼副駕駛已經有人了,這不是顯示的「空車」?
「那個,啊,泥、泥蠔。」臨時有和塔矢學一點中文,現下好像只有這一句能用上。
「您好,您好。」
這是位很俐落的中年人,嘴角還掛著一抹僵硬的微笑,警惕地盯了他兩秒,視線掃過他挑染的金髮。隨後謹慎地從他身後繞過去,打開後備箱。
坐到副駕駛深灰色的皮椅上的時候,隔著一層灰色的柵欄,依然感受到駕駛座傳來的打量的目光。
喔~原來中國的計程車,座位和日本是反的呀。仔細一看,道路的行駛方向也是——昨晚還發郵件問過和谷到中國需要注意什麼,那傢伙怎么都没说。
尷尬地理了理濕漉漉的劉海。提前帶了寫有目的地的紙條,記得就放在褲子左邊的口袋裡⋯⋯
「唔哇——」可是剛才在雨裡全身都淋濕了,水性筆的字跡變成了當代藝術一樣的鬼畫符。文具都在箱子裡,也不知道要怎麼向司機借筆。
司機還在用疑問的眼神看著。深知自己的中文遠沒有好到能夠和當地人順暢溝通,但也只能硬著頭皮,回想著記憶裡亮向他示範的發音,猶豫地開口。
「中⋯⋯中國⋯⋯棋院。」好像是這樣的?
看到男人眨了眨眼睛。
「棋院。」比劃了下棋的姿勢,又在空中畫了個方盒子。「棋,院。」
對方盯著前方的高速路想了幾秒,忽然反應過來,點了點頭。
緊了緊白手套,握住方向盤,司機發動了汽車。緊跟著放起聽不懂的廣播,似乎沒什麼可和他聊的。
雨點擦著車窗向後飛去,灰蒙蒙的雲蓋在濃綠的樹上,天邊漏出一道淺色的斜陽,看見有人頂著公文包在路上狂奔。
光想起他這次離家時並沒有帶傘。
東京的街道似乎更冷硬一些,陰雨天氣就愈發晦暗,黃昏時的光源幾乎只來自那些霓虹燈管和明晃晃的燈牌。
「人類都可以到月亮上去了,雨傘卻還是雨傘的樣子⋯⋯」
那個人和他并肩走在大雨裡時,曾這樣說道。
「不過,平安時代京都流行的是紙做的傘,和小光的這把很不一樣呢。」
「紙?做的傘?」
「是啊。是竹子做的傘骨,唐紙製的傘面,上面塗滿胡麻油。
「雨天的時候,朱雀大街上就像開滿了彩色的牽牛花。」
「㖃⋯⋯」
「但現在,好像是黑與白這樣樸素的顔色更受歡迎了。」
「因為時尚是會變的嘛。你喜歡的圍棋,以後會變成大熱門也説不定。」
——耳邊響起澀谷交叉點熟悉的音樂,不知不覺綠燈已經亮了。
「嗯?進藤?」
「啊、抱歉,剛才走神了。」
六月的雨季,和亮從棋會所出來。再次撐著傘路過這個地方,猝不及防被回憶侵襲。
急忙跟上亮的腳步。雨傘的邊緣將他們隔開,四面的雨聲和人聲夾雜在一起。
「⋯⋯說起來,下個月二十號緒方先生會辦研討會,在我家,也是塔矢門下的例行聚會,要來嗎?」
努力分辨著亮的話音,視線不知不覺落在他的嘴唇上。
「現在已經是本戰的第三場了,一勝兩負。」
那對薄唇染上水霧,像雨中櫻花的顏色。
「緒方先生⋯⋯應該會帶很多桑原老師的棋譜來討論。[2]」
什麼東西在蠢蠢欲動。有那麼一瞬間,很想就這樣把佐爲的事告訴他。
「無論今年結果如何,下届的挑戰權都可能在我們之中——喂⋯⋯你幹什麽?」
亮看著身邊多出來的熱源,一時不知道該不該退開。
原來是光收了自己的傘,像塊磁石一樣鑽到他的傘下。
「雨聲太大了,聽不見你説話。」
「可你⋯⋯不是有傘?」
「都說了是距離太遠沒法和你好好說話嘛!」光瞥了眼自己的肩膀,又抬頭看了看透明的傘頂。「欸嘿,這個大小正好欸。」居然不會淋濕,只是有水氣淅淅瀝瀝地飄到布料上。
亮僵硬地握著傘柄往前走,光感到他的脚步不知不覺變慢了一些。
「剛才的⋯⋯也不是特意說給你聽的,自言自語而已。」
「嗯?什麼自言自語?不是在邀請我去你家的研討會?」
「⋯⋯你不是說沒聽見嗎!」一記眼刀剜過來,「那就當我沒說。」
「喂喂,說了就是說了!什麼叫『當你沒說』。聽過的內容,我的腦子又忘不掉。」光停頓了一下,「只是已經定了要去中國棋院參觀的行程,好像就在那幾天。」
「這樣⋯⋯」亮思索了一下,「那也好。」
考慮到自己現在是三連敗的狀態,從亮的話裡竟然聽出一絲欣慰之意。
是啊,也許換個環境就能找到出路也說不定——在和高段棋手的對弈中,逐漸察覺到無法贏棋的原因並不只是棋力或棋感的差距,而是一些長年沉澱下來的東西,譬如心態、決斷或是某種信念。
欸,這麼說來⋯⋯這傢伙剛才是在關心我?
忍不住又瞟了亮一眼。
真的假的?
計程車在路邊停下。
「先生,咱到了啊。」
光回過神來,窗外並不見棋院的大樓。
剛想問什麼,轉頭一看,司機已經下車去開後備箱了。
拖著箱子站在人行道上,一陣風過去,空氣裡滿是夏天雨後鹹濕的氣息。
聽和谷提過棋院門口是很寬的大街,旁邊有條河,對面有各式各樣的餐廳。可這附近全是色彩柔和的居民區,立在油綠的小公園和彩色地磚鋪出的道路之間。
「嘖。」
掏出手機看了一眼,仍舊沒有新郵件或未接來電。
要不還是給伊角打個電話吧,他來過北京,可能會知道這是哪。
按下通話鍵,光沿著步道一點點向前走著,直到接通的「嘟——嘟——」聲轉變為忙音。
伊角沒有接電話,可耳邊還是響起了日語。
「喔?這不是進藤君嗎?」
「是。」欸,等等,「楊海先生?!」
「真巧。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我是來找和谷和伊角的,約了在棋院見。」
「棋院?」楊海露出困惑的表情。「所以爲什麽在這兒?」
「是司機把我放在這裡的。」
「可是這兒是『西苑』啊。」
「對啊,我在機場就是這麽和他説的。」
「哎唷⋯⋯我是說這兒是『西苑』,不是『棋院』!」
「嗯?」他剛剛重複的那兩個詞有什麽區別嗎?
「唉,你跟我來吧。我正好也要回宿舍。」
光隨著楊海的脚步往前走,步道很寬,道旁立著一排松柏和不知名的巨大樹木,背後傳來嬉鬧聲,有孩子蹬著滑板車從身邊過去,幾位老人慢悠悠地搖著大蒲扇散步。
「那個,這裡離棋院很近嗎?可以走過去?」
「不近,我們要去巴士站搭車。」
整了整被登山包帶壓住的衣服,光忍不住東張西望。
在和圍棋沒有任何關係的場合偶遇了世界頂尖的棋手,也沒有在做跟下棋相關的事,總覺得很違和。
而且這位棋手還有五個世界冠軍在身,並兼任這兩屆北斗盃中國隊的團長——
「楊海這傢伙,勾結安太善耍詐,簡直是、嗦、人面獸心!」
上個月在中華拉麵撞見倉田厚時,曾聽他痛斥道。
「欸,發生什麽了嗎?」
這屆北斗盃若有這麼勁爆的新聞,和谷回來時怎麼沒提起?
「韓國隊臨場交換大將和副將,沒想到中國隊也跟著換!就我們什麼都不知道!事前給社和越智做的針對性特訓都打水漂了!嗦。」倉田大口吸著拉麵,「真是的,平時說什麽追求神之一手的高度、日中韓地道的才能之戰、架起三國友誼的橋樑⋯⋯真上場了卻都在使這種伎倆!」倉田一拍筷子,「進藤,你聽了也很憤慨吧!」
「嗯?嗯⋯⋯」
可這不是我們去年就幹過的事嗎。倉田先生,怎麼罵自己罵得這麽來勁。
更多的關於楊海的信息還是從伊角那裡聽説的,從中國回來之後他們二人似乎一直保持著聯絡。上次在伊角家,還見他泡了對方寄來的中國茶。
「這是楊海先生老家特產的茶葉,叫『普洱』,我在之前打工的吃茶店裡見過,是一種很高級的茶。」
「啊,我在常去的棋會所的飲品單上也有看見。」好像還聽市河小姐抱怨過這種茶葉空運到日本後總是會碎。「聽説很難完好地運輸?」
「嗯,確實是這樣,但是楊海先生在外面包了很多層氣泡紙,盒子裡也用泡沫墊著,所以寄到時還是完好的圓形茶餅的樣子。
「楊海先生,真是很可靠的人啊。」
「是很難得⋯⋯話説伊角學長,最近在追星?」
從剛才就看到伊角原本空蕩的出租屋裡忽然增添了許多女優的海報和性感寫真集,以及一地的空紙箱,總讓人有些在意。
「啊,這、這些都是楊海先生讓我幫忙代購的!因爲受了他很多照顧,就答應了下來⋯⋯」
「呃⋯⋯」
所以「很可靠」的楊海先生大概也不會忘記簽收這些謝禮吧。
「——嘿,到了。車站就在這兒。」
在候車的塑料椅上坐下,楊海把手裡的紅藍條紋編織袋撂在地上。
「來坐,還有位置。」
「啊,沒事,我⋯⋯」光邊説邊擡脚。
箱子的滾輪朝後「哧溜」滑了一下,光差點一屁股坐地上。
「⋯⋯我坐箱子上就好。」
楊海對光去年北斗盃的表現有很深的印象,也一直聼伊角說這孩子棋下得非常厲害,只是現在看著,還是很難把眼前這個少年和下棋這樣的職業相聯繫。而且剛下飛機就迷路了什麽的⋯⋯
「楊海先生在這裡做什麼?」光盯著他的編織袋問。
「啊啊,剛回家一趟,我父母家在這附近。這些是從家裡帶的特產。我爹媽前陣子回老家省親,順帶捎了些糕點、零食、辣椒醬,什麽的。」
「ㄟ,聽說楊海先生的老家還產茶葉?」
「嗯,是在西南邊叫『雲南省』的地方。」
「經常回去嗎?」
「哈,不能吧。要坐六個小時的飛機,之後還要轉巴士進山,實在太遠了。」
「六個小時?!」光露出非常震驚的表情,週圍的幾個人聽見響亮的外語,又是變聲期特有的破鑼嗓子,不禁回頭望向他們。「啊,抱歉。」光趕緊捂住嘴。
「哈哈哈,塔矢老師現在住在深圳,每次來北京也要四五小時呢。話説這次北斗盃沒看見你?塔矢二世[3]也沒有來的樣子。」
「呃,我和他都有國内頭銜的循環賽,正好也在五月。」
「欸,進藤君和塔矢君已經打入頭銜的循環圈了?十六歲的年紀,可真是了不起呀。有希望取得挑戰權?」
「如果能扭轉三連敗的話⋯⋯」光撓著頭髮尷尬地笑了笑。
「嘛,我十六歲的時候才剛定上段,那時候勝率也是一塌糊塗呢。」
循環圈嗎⋯⋯就算現在成績不佳,也不容小覷。
去年的北斗盃之後,《圍棋世界》六月刊的封面上,日本棋院以雖敗猶榮的態度提出了「新浪潮」這個概念,大致是說新晉的棋手都很有潛力,遲早會在國際賽上嶄露頭角。
「出版社倒真會寫。什麽『新浪潮』,這不還是墊底了,在給失敗找藉口。」
「而且是國際賽啊,日本近年是越來越不敵中韓了ˊ_>ˋ」
「是啊,真懷念塔矢行洋大師還代表日本出戰的年代。」
「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塔矢亮還是值得期待的。」
「可是青少年裡就他一個人能從中韓手裡贏棋,有什麽用呢。」
「而且還臨時被換成副將,日本隊明顯是想田忌賽馬但失敗了吧(^^;;」
「今年日本的主場都一塌糊塗,也不知道明年得是什麽樣。」
楊海看過雅虎論壇上的一些説法,圍棋愛好者之間還是質疑的聲音居多。其實身爲被評價對象的職業棋手,對於這些宣傳目的的措辭和呼籲反而沒什麽感覺。在他看來,即使日本圍棋現下青黃不接,就環境來說,聲援造勢和聯絡商業合作的能力還是很強的。
這麼想著,楊海看了光一眼。
兩年前的新初段,卻有著對高永夏下戰帖的氣魄。十六歲的年紀,至今也沒有太多釋出的棋譜⋯⋯媒體話術之下的實力,能是多少呢?
還是這幾天找個時間,和他下一局看看吧。
「那個,進藤君,你那把扇子,不用的話能不能借我扇扇?」
「呃?嗯。」
說著,楊海朝光伸出手,光卻明顯地頓了一下,把扇子打開看了一眼,直接開始替他扇風。
「啊⋯⋯謝了。」
話說進藤不覺得熱嗎?三十度的天氣,還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有路過的人盯著他看,他好像完全沒在意。
直到在車上靠窗的位置坐下,才看見光的額頭上果然也全是細密的汗。可他只是拿著扇子發呆,打開又合上,如此反反覆覆。
唉,孩子別是給熱傻了吧。
巴士不緊不慢的顛簸讓光有些犯睏。
已經沒有再主動去回想那段經歷了。偶然拾起時,甚至發覺記憶都變得模糊,逐漸抓不住和那個人相處時的細節。
這把扇子,對他來說不只是扇子,所以也就從沒想過它實用的那一面。
總覺得不能就這麼輕易地睡著。光抬起手臂拉開窗戶,讓傍晚的風迎面灌進來。
自行車的鈴鐺聲此起彼伏。雨後的天空裡,太陽已經西斜,磚石色調的房屋和灰色的瓦頂都被染成古樸的金色,公園、商鋪和餐廳門口挂著風格古怪的手寫漢字招牌,有人推著車沿街賣瓷器,人行道旁鋪開一排亂糟糟的小攤。
「欸?」
驀地瞥見路邊聚了一小撮人,人群中間擺著一張折疊桌,有兩位老人正面對面坐在凳子上⋯⋯下棋?!
揉了揉眼睛確認沒有看錯,光忍不住扒著窗框直起身來仔細觀察——圍觀的人全都眉頭緊鎖,連中心的二人也是一副苦苦思考的樣子,手裡的菸頭兀自燒著——看這架勢,確實是在下棋沒錯。
不是任何在日本見過的棋種。木製的棋子上面寫著一些漢字,列在棋盤兩側,會讓人聯想到將棋。
只是這些棋子黃澄澄的顔色、圓圓的形狀配上深色的刻字,越看越覺得更像家附近的神社新推出的除厄饅頭⋯⋯
「喏,給你。」
光從楊海先生手裡接過一個鼓鼓的塑料包裝的東西。
「餓了吧。剛才聽你肚子都在叫。」
「啊!謝謝。」撕開包裝袋,裡面是看起來很酥脆的、吃起來絕對會掉渣的糕點。讓人想起一些公德與禮儀問題。「那個,這也能在車上吃嗎?」
楊海擺了擺手,「別讓售票員看見就行。」
「啊,好。」
一口咬下去,有很芳香的鮮花的味道。[4]
車廂前邊,售票員正和司機聊得熱火朝天,整個空間充滿了他們的高談闊論,好像也沒心思看他。
⋯⋯似乎很多東西都出現在乍看不合時宜的地方,又覺得非常自然。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好像太近了;可人就是群居動物,是否本就渴望這樣的關係呢?
時間沖淡了很多東西,又無法完全抹去。每當翻開秀策的棋譜,他望著的是那個人的背影。他好像繼承了佐為的一部分,並迫切地想要證明這份遺產的價值。
這不是他面對任何一個其他棋手時的心態。
「和你對弈,讓我想起了網上的sai。」
「我不是sai喔,很可惜就是了。」
「是你⋯⋯」
「塔矢?」
「是第一次遇見的那個你,在棋會所和我對弈了兩次那個人,就是sai。」
佐為⋯⋯大概從外人的視角,我和你就是這樣密不可分的關係吧。
現在塔矢也能看見你了,只不過是透過我。
「抱歉,我說了奇怪的話呢⋯⋯
「你下的棋就是你的全部,只有這不會改變,這樣就⋯⋯足夠了。」
我的棋⋯⋯是我的全部?
可我一直在下你的棋啊。在那麼多學習著你的棋的人裡,我甚至遠遠不是最強的那一個。
塔矢也好,高永夏也好,和他們下棋的時候,越來越強烈地體會到,我並沒有因為曾經被你附身而變得特別。
我看著你的背影,追隨著你的引導來到這裡,才發現面前黑壓壓的一片,全是與我無異的、向上攀爬的人。
你不在我身邊,我該用什麼超越他們?在你之後,我又該看著誰呢?
「中國棋院」四個金色書法大字在褐色的樓上很醒目。不禁掏出手機拍了一張,附文「欸嘿,到了(゚▽゚)」,順溜地發給亮。
一陣晚風吹過,一旁的樹葉發出細密的響動。
擡頭看向風來的方向,幾株瘦高的樹上飄著大片雲霞似的花,有五六個人在樹下觀賞。是合歡嗎?開得真好。
可真正吸引他視線的並不是這個,而是旁邊那棵無人在意,卻讓他覺得似曾相識的樹。
大概只有葉子的時候,很難注意到它是一株玉蘭吧。
七月的塔矢門下研討會不能去,就應下了六月末的邀請。緒方先生不在,氣氛相比研討會更像是茶會,蘆原還帶了格外精緻的便當,並堅稱是自己做的。
臨別時,發覺院門口好像多了棵沒見過的樹。種在很好的位置,卻沒有任何花。
「塔矢,這是什麽樹啊?」
「這是那棵玉蘭,你見過的吧。」
「啊,是這樣嗎?」
「不在花期而已。」亮看了看四周,又瞟他一眼,「你上次還說它好看的。」
也對,明明開花的時候會覺得它的花苞和香氣很有存在感,怎麽現在就留意不到呢。
有些東西,在默默生長的時候,很容易讓人忽略。
如果忽略貼滿一面墻的女優海報和床上鮮艷的大花被子,楊海的宿舍其實很樸素,根本看不出是世界冠軍的房間——除了一張床上放著的棋盤,可上面正堆著筆電、盆栽、手機充電器和燒水壺等雜物,看起來並不經常使用。
在棋院門口時,楊海提議請他吃晚飯,順便去他宿舍坐坐。本以爲能吃到北京烤鴨之類的當地菜,結果楊海熟練地從衣櫃裡給他拿了一盒牛肉味泡麵加三根玉米腸。滋味竟也意外地不錯。
嚼著品客薯片,喝著放涼的綠茶,光坐在空的那張床上,書桌前的楊海用另一台電腦整理郵件。
「楊海先生,也很擅長英語呢。」
看著楊海的手在鍵盤上流暢地打出一串字母,光不禁發出這樣的感歎。
「哈哈,是法語來著。在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通信。」
「奧林匹克?」
好像有聽過這樣的傳言,說圍棋即將入奧成為正式比賽項目。可光沒想到,會有楊海先生這樣的棋手在親自處理這件事。
「是啊,項目的申請已經被批准,後續本來是該通過各國的委員會向洛桑總部提交賽程計劃書的。」楊海看了他一眼,「可你也知道,翻譯容易出問題,尤其是圍棋的規則和術語。而且三國各自提交的話,流程很慢,內容又會重複。
「這半年來,我同各國的棋手聯係,收集大家的意見整合成一份提案,做一點收尾工作,今天終於可以完成。再過幾個小時,等瑞士那邊天亮了,就可以定時發送了。」
「欸?」所以意思是⋯⋯「圍棋很快就要成爲奧運會的正式項目了?」
「是啊。不止是圍棋,還有象棋、西洋棋、跳棋、麻將等等。
「除了亞洲,在美國、英國、歐陸的諸多國家和澳大利亞,世界各地智力項目的從業者都在為這件事的促成而努力。
「明年是雅典,五年後就是我們。」
敲下最後一個標點符號,楊海按下完成鍵。
「圍棋在世界舞臺上的初次亮相,就會在2008年的北京!」
看著楊海此時的神情,光也被他的熱情感染。
世界嗎?
越過塔矢亮,越過高永夏,越過更多人的背影,好像望見了一片空曠的處女地。想要變強,變得在那一天到來的時候,能够站在那個地方。
不是為了任何人,不是為了無法證明的過去,或是觸碰不到的未來,只是為了我的圍棋。
佐為,塔矢說得沒錯⋯⋯
我的圍棋是我的全部,只能由「我」來超越他們。
神之一手,我會替你完成。
我⋯⋯是有這樣的資格的吧。
「楊海先生,能不能和我下一盤?」
楊海回頭,看見的是不知為何握著扇子,緊緊盯著他的光。
「⋯⋯好啊。本來邀請你上來,就是想和你手談一局的。」說著,朝堆滿雜物的床看了一眼,「要不就在電腦上下吧,你坐這兒來,我讓你兩子。」
「不用了,請讓我和您分先。我想知道⋯⋯奧運會的實力。」
一場對局結束,天色已經暗下來。
「啊啊啊——不行,我認輸了!」光指著屏幕右上角,「果然這裡還是太勉強了吧,是我的判斷失誤,沒想到在這裡引起劫爭會成為最大的敗筆,應該更穩妥地加厚左側的形勢⋯⋯」
「嘛,我倒覺得不是劫爭的問題。」楊海看了看光。「如果先前在這裡『虎』而不是『粘』的話,是可以接應到的。你看——」
楊海點了幾下鼠標,直接退回到了那一步,下在另一個地方,又順著之前的幾手做了變化。
「真的欸,真的是這樣⋯⋯」
「不過還真是被你嚇了一跳呢,關鍵時刻的判斷很大膽。」如果是正式比賽的對局,這樣應變自如的下法確實會給對手不小的壓力。「呃,雖然我也沒有盡全力,但能感覺⋯⋯你之前的三連敗只是經驗的問題,繼續保持這樣的氣勢吧。」
「啊,是,那個,多謝您的指教!」
「不用跟我客氣。話説你們明天有安排嗎?我上午有空,可以帶你在棋院轉轉。」
「好啊,我沒有——啊,剛才忘記和和谷他們聯係了!」
這才想起掏出對局前靜音的手機,看見了——二十三條未讀消息?!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19:42:29
主旨:你在哪
剛才在河邊和老頭子們下棋
你在哪
我有空」
「送件者:伊角 慎一郎
日期:2003年7月18日 19:44:43
主旨:怎麼了?
進藤,剛看到你給我打了電話,我回撥過去沒有人接。和谷下午出去了,他有去接你嗎?」
「送件者:伊角 慎一郎
日期:2003年7月18日 19:45:38
主旨:地址
崇文區[5]天壇東路80號。
如果沒接到的話,來這裡找我。攔一輛計程車,給司機看這個地址就可以。」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19:58:12
主旨:你在哪
看到了回我
你不會還在機場吧」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0:30:03
主旨:回我啊
我在去機場路上
你這傢伙
看到了回我」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0:48:26
主旨:好慢啊
現在路上晚高峰
你在機場的話原地等我一下
看到了回我」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1:18:12
主旨:回我
你給伊角也打了電話?
他去棋院找你了沒找到
你到底在幹嘛」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1:32:25
主旨:不會被綁架了吧
再不回我要報警了」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1:35:07
主旨:ARE YOU HUMAN TRAFFICKER
是人販子嗎
YOU ARE CRIME
CALLING THE POLICE」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1:40:32
主旨:YOU ARE CRIME
HE IS JAPANESE
I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LLING THE POLICE」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2:17:08
主旨:XXXXXXXXX
XXXXXXXX,
XXXXXXX,XX,XXXX,
XXXXX!XXXX!!
XXXXX,XXX。」(看不懂的中文)
「送件者:和谷 義高
日期:2003年7月18日 22:20:47
主旨:無主題
如果不是被綁架的話
進藤我恨你」
以上,附八個未接來電。
「那就這麽説定咯。」
楊海關了電腦。
「話説今天都這麽晚了,你要不就睡這兒算了?我正好把床收拾收拾。」
「呃,不,那個,我還是回去吧⋯⋯」
和谷身心俱疲地回到旅店的時候,擡眼看見伊角也站在房門口。
「和谷?你那邊怎麼樣?」
進藤不見了。
「我在棋院裡轉了一圈,都沒找到。」
想著他可能還困在機場,一個人又不認路,叫了車趕過去,路上堵了一小時,在到達層轉了一大圈,各種廣播尋人無果,只好又叫車回來。
「聼你説進藤可能被人販子綁架了,還要我寫段中文,到底怎麽回事?」
聯想到這樣的可能性,再加上前兩天的事,他現在和這個人說一句話的心情都沒有。
「喂,你回答我啊!」
和谷抽出門卡要進門,可伊角同時伸出門卡,把他擠到旁邊。
和谷瞪了他一眼,也不甘示弱地擠回去,兩隻手撞在一起。
伊角到底是比他高半個頭的成年人,這手勁懟得他有點痛,可他毫不卸力,二人一時僵持不下。
「喔,你們都在這裡啊——」
進藤突然出現在樓梯拐角,走廊的盡頭,拖著行李箱,包挂在肩上一晃一晃地走來。
「不好意思,剛才碰到楊海先生,他請我吃飯,之後又下了一局,就沒有看郵亻——誒呦!」
「混蛋!知道有多讓人擔心嗎?!我真的差點要報警了欸!就不會先説一聲嗎!」
「啊啊,對不起啦~」光挨了一爆栗,吃痛地捂著頭,「話説都站在這兒做什麼,房卡壞了嗎?」説著刷了自己的卡推門進去。「剛剛前臺的姐姐跟我説這裡的卡都舊了,容易消磁,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去找她換。」
打開燈找到唯一的空床,白色的床單、被子和枕頭在上面堆成一座小山。光把箱子推到邊上,將背包撂在一旁,費了點勁把床鋪好。
「唔,你們要洗澡嗎?」
沒有人回答。
「那借我先用一下㖃。」
在淋浴間簡單沖涼之後,光仰面倒在枕頭上,想起那張被雨淋濕的字條還放在褲子口袋裡。
「話說,這兒哪裡能洗衣服?」
拿去洗之前要記得取出來。不過剛才也沒看見這裡有洗衣機⋯⋯
短暫的沈默之後,伊角回答了他。
「放在門口的洗衣簍裡,白天客房服務會收去洗的。」
「喔,好。」
臨睡前查看一下郵箱,沒有新的郵件——看來塔矢今晚並沒有開電腦收信的樣子。
真好啊,剛到北京就受到了楊海先生的親自指導,對方態度還很友善。
和厲害的人下了這麼漂亮的一盤棋,應該寫下來發給塔矢看看,可是好累喔,明天再說吧。
黑暗裡,迷迷糊糊聽見自己的聲音:
「塔矢,我有個問題想問。」
「怎麼了?」
「『中國棋院』在中文裡該怎麼寫啊?」
「中文也用漢字,這四個字和日語的寫法是一樣的。」
「欸,真的嗎。」
房間的燈忽然「啪」一聲被打開。本能地閉上眼,耳膜卻受到比强光更劇烈的刺激——
「——這不是廢話嗎,進藤?」
看到一張意想不到的臉。「哇——!塔矢,你怎麽在這裡啊!」
昨天不是到棋院就和他報平安了嗎,怎麼還這麽生氣。
「不認路爲什麽在機場的時候不拿地圖?我説過漢字寫法是一樣的,完全沒聼進去?會給我發郵件,不會用手機寫『中國棋院』四個字給司機看?」
對喔,還可以用手機打字。當時只顧著着急沒有筆,確實沒想到。
「發音也都白教你了?為什麽粗心成這樣,出門不看天氣預報的?不知道今天會下雨?」
這個人吼得真的很用力,還從來不知道他居然可以這麽大聲。
只是,塔矢整齊烏黑的頭髮隨著他每個用力的詞句晃動的樣子,總讓人移不開視綫。
鋒銳的眉緊蹙著,一雙上挑的鳳眼因爲怒氣而瞪大,面上微紅,眼尾似乎有些濕潤,飛快地喊出這些話語的嘴唇透出溫潤的粉色。
離得那麽近,彷彿伸手就可以碰到,那樣柔軟的觸感——
嘖,怎麽又開始想這種事,明明還在被他吼,用手堵住耳朵都覺得好吵。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甚至房間裡都是回聲,這樣下去真的會聾——
嗯?
眨了眨眼。塔矢的身影消失了,但確實有光綫。窗簾已經打開,是陽光照進房間裡。隱約聽見熟悉的話音,是在盥洗室的方向。
原來是做夢啊⋯⋯揉了揉眼睛,踩著一次性拖鞋去打招呼。
伊角見他過來,卻先轉頭對和谷說:「幹什麽呢,瞧你把進藤都吵醒了。」
有些嚴厲的聲音擊打在四周的瓷磚上產生回音。
這兩個人怎麼看起來⋯⋯心情很差?把自己吵醒又不是什麽大事,以前合宿的時候也有過,應該不至於這麽生氣?
四下瞧了瞧,見一隻繪有紅色花朵的大瓷盆倒扣在地上。和谷已經換好衣服,看了他一眼,從鼻子裡哼了一聲,摔門出去了。
喂喂。
光這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什麼,想起和谷適才陰沉的臉色,感到一陣寒意攀附在脊背。
這氣氛,該不會是⋯⋯在吵架吧?!
「抱歉。」
伊角將盆撿起來放回架子上,從墻角撛過拖把擦乾地上的水漬。
「那個,伊、伊角學長⋯⋯?」
「沒什麼,和谷他這兩天心情不好,不是針對你的。」伊角似乎已經恢復到平時溫和的狀態,笑著對他說:「這個時間,可以一起去棋院一樓的食堂吃早餐,如果你想的話。」
可是因為食物太豐盛,也因為食堂人太多,等光幹完了早飯的四個肉饅頭三根油條兩個糖火燒和一碗豆腐花,也沒找到合適的時機問清楚早上的事。
「你上午有什麽安排嗎?」嘈雜的環境裡,伊角把聲音抬高了點。「我等等會去三樓的訓練室看看,現在是暑假,留在棋院的棋手和學生都在那裡自習。」
「楊海先生昨天說上午可以帶我參觀棋院,我⋯⋯我還是先去找他好了。」
「行,他住303室,你知道的吧。」
「嗯嗯。」
見他點頭,伊角遞過來一個透明袋子,裡面裝著兩個糖油餅,「他托我買了這個,麻煩幫我帶給他吧。」
三樓的樓梯口,光看著伊角徑直走進訓練室,用中文和在場的人打招呼,好像和那些人很熟識。耳邊又重新響起他聽不懂的語言。
「唉。」不知道和谷這傢伙現在在幹嘛呢。
光無端想起了他們三個都還是院生的時候的那件事——
「你們知道真柴怎麽了嗎?」大聲嗦著可樂,「他看起來像被人打了。」
麥當勞的卡座裡一片寂靜,大家聽了光的話,齊刷刷地看向和谷。
「嘁,是那傢伙若獅子戰下不贏伊角學長,就亂說人壞話。所以我用拳頭教訓他一下罷了。」
和谷說著,用力扯開一袋番茄醬。
「——哎呀。」
醬汁濺到和谷手上,伊角連忙遞出自己的紙巾。
「可是和谷,打人總歸是不好的⋯⋯」
「喔〜原來和谷上週被篠田老師叫去訓話就是因為這個啊。」
「就你哪壺不開提哪壺!」和谷不客氣地從他餐盤上搶走一根薯條,「我那屬於是英勇就義了。」
和谷平時是個很隨和的人,不會輕易發火,很開得起玩笑。除非有什麼真正觸及到原則的事⋯⋯
觸及到原則?對伊角學長嗎?怎麼會?
再次來到楊海的房間,他似乎才剛睡醒,打著哈欠只穿背心短褲就來開門了。
許是還有點起床氣,楊海也沒怎麼招呼他,只指了指空著的凳子說「坐」。盥洗室裡傳來洗漱的水聲。三十分鐘後,楊海才穿戴整齊地出來,很自然地坐在書桌前享用起代購的早餐。
空氣中飄散著糖油餅微焦的甜味,光有些焦躁,他的目光在牆面上飄來飄去,從女優的寫真看到明信片和貼畫,又注意到楊海的茶杯。
那是一隻白色釉面的杯子,杯口染了一圈濃艷的藍,光總覺得還在什麽地方見過⋯⋯
「那個,楊海先生,中國最近很流行這樣的器具嗎?」
「你説這種搪瓷杯子?五十年前就很常見了吧。」
早上看見的盆,記得也是這樣的風格,上面還噴繪了一個像是字又像幾何圖案的符號。
「搪瓷?原來是這種材料啊,難怪會發出那麼大的聲音。話說楊海先生,」光有些猶豫地開口,「今天早上和谷和伊角⋯⋯他們好像吵架了。」
「欸,怎麼說?」
「具體的我沒問,只是感覺很嚴重,早上起來就聽見一個盆被打到地上,那聲音,我都要聾了。」
「啊?打架了?」
「應該沒有⋯⋯」光的眉毛擰了起來,「就是從來沒見過他們兩個關係不好。」
「這樣啊⋯⋯那他們現在在哪兒?」
「伊角學長應該還在訓練室吧。和谷他⋯⋯一大早就出門,不知道去哪了。」
聽了光的話,楊海嚥下最後一口餅,愣了愣。
伊角上次來中國棋院的時候,就提到過他這位長得很像樂平的院生朋友。而楊海第一次見到和谷義高,是在去年北斗盃的會場,當時邀請他來中國棋院學習,說要把他和樂平並排看看,多少有開玩笑的成分;但那孩子很認真地應下了,還說要存了錢再和伊角一起來。
今年看到他作爲日本隊的三將出戰北斗盃,在歡迎會上寒暄了幾句。
「伊角學長原本也想來觀戰的,可惜他⋯⋯黃金週在札幌還有別的日程。」聽和谷訕訕地說,「他應該已經和您講過,我們今年夏天會來中國棋院叨擾,到時還請您多指教!」
健談的十七歲少年,又像刻板印象的日本人一樣有禮貌。一直把同為雲南出身的樂平當弟弟看待,所以見到和谷也會覺得親切。這些天裡聊得多了,更覺得他是個很好相處的人。即使語言不通,也會靠打手勢加上説英語和趙石嘮嗑,有他在場的時候,好像連伊角都變得比兩年前開朗了很多⋯⋯
難以想象這樣兩個人能為了什麼事吵得劍拔弩張的樣子。
楊海摸著下巴思索了一會,問光道:
「那要不,進藤君,作為昨天指導棋的回禮,你幫我個忙?」
昨天為了撰寫計畫書在宿舍宅了一上午,下午又回家一趟。上次和伊角他們碰面還是前天晚上吃沙縣小吃的時候。
「話說楊海先生,一直想問,北斗盃中國隊人選是怎麼定的?也會專門在全國進行預選嗎?」和谷夾了一顆蒸餃放在自己盤子裡。
「沒有,這方面倒是和韓國一樣,棋院直接評定賽績,在全國選了表現最佳的十八歲以下的棋手。」
「原來如此。」
「欸,說到這個,伊角,你這麼強,怎麽一直沒有參加?」
「啊。」伊角的筷子一頓,「因為去年我就已經十九歲了⋯⋯」
「這樣啊。還以爲你也差不多是那個範圍來著。」楊海拍了拍伊角的肩膀,「唉,這些棋賽真是,年齡卡得太死了。我其實也很想去,可惜超齡了一點點,就只能替他們當保姆啦。」
「楊海先生今年是⋯⋯?」
「二十六了。」
和谷盯著桌上的醬油瓶和醋瓶,最後倒了醬油。
「說起來,這兩天也沒有見到陸力和王世振,是和樂平一樣回家了嗎?」伊角喝了一口冰紅茶。
「王世振是回上海過暑假,不過陸力從下半年開始就要在深圳棋院工作了。」
「深圳?」
「是因為徐彰元老師簽約了深圳隊,他是彰元老師的學生。」
「彰元老師,是韓國人吧?」
「嗯,不過編制上他已經不在韓國棋院了,所以能以自由棋士的身份加入深圳隊,參加海外的商業比賽。」
和谷看向伊角,「那就是像塔矢行洋大師一樣。」
「中韓棋院之間的交流很多,中國各地的棋院之間也有交換項目,棋手可以根據自己的職業規劃遞交申請,來選擇想待的隊伍。」
伊角低頭想了想,「有過日本的棋手轉籍來中國棋院的先例嗎?」
「日本啊⋯⋯」楊海望了望天花板,「塔矢老師是先在日本宣佈引退後才來的,以職業棋手的身份直接加入中國棋院的日本人,好像真的還沒有。日本的棋手似乎不太願意離開日本棋院呢。」
「是氛圍不一樣吧。中韓的大型國際比賽和國內聯賽都很頻繁,競爭更激烈,平時以各自的隊伍為歸屬,很有挑戰性。」
「喔?伊角你會這麼認為啊。」他似乎已經了解得很清楚。
「嗯,不過這樣的環境下,連樂平那種年紀的孩子都有失業焦慮了。」
「他和你說的?這小鬼頭,剛定上段的時候整天只想著玩,現在終於認真起來了?」
「是啊,之前聼他説如果這個賽季成績再不好,沒有隊伍簽約的話,就只能下放去補習班給業餘學棋的人當老師。可是他才十三歲呀,未成年的孩子也不能去當老師吧。」
「哈哈,説起來,你還真是擅長對付小孩子啊。」
就算是陸力從北京轉到深圳,其實也是從去年就開始準備,前前後後跑了很多趟;伊角這麼一板一眼的人,要從日本棋院轉籍,更不可能是隨口一問的事。楊海雖然有聽出他的話外之音,卻也不覺得他一定會選擇來中國就業。
至於和谷,他聽到伊角那樣說之後就安靜下來,沒再搭過話,現在想想,確實有些不對勁。
想起自己也是在大概這個年紀的時候,參加了去韓國棋院進修的交換項目,那時他住的還是低段棋手的三人間,放假回來和室友講了許多在那邊的見聞。
第一次出國,南韓的經濟和文化讓他一個雲南山區長大的年輕人眼花繚亂,韓國棋院的氛圍也不似想象中的冷漠,大家好像都樂意和他這個説著蹩脚韓語的外來者交流,並用圍棋一較高下。
「韓國棋院其實對外國人挺開放的,語言不是問題,好像也有交換進修之後留在那兒的中國人。」
「喂,我説楊海,你該不會是想去給韓國人下棋了吧?」
室友是個心直口快的北京本地人,一聽他這麽説就急了。
「哎不是不是⋯⋯我也沒這意思。」
其實在韓國的那段時間也不是沒受到過歧視與偏見。那是1997年的事,即使蘇聯解體,中美建交,香港回歸,冷戰作為世界大戰的回音還是在東亞遺留下很多痕跡。韓國民間對中國的印象不一定好,反之亦然。
日本人的話,好像都不太關心政治,可若說和谷是聽了伊角的話,因為相似的民族感情而生氣,倒也不是不能理解。無論如何,還是得找個機會讓他們說清楚才好——
主打涮羊肉的火鍋店,分明是只要待在裡面、聞到那樣的香味就會心情愉快的地方。然而在一片熱鬧的嘈雜聲中,只有楊海這一桌的氣壓很低,冷氣在頭頂上呼呼地吹,火鍋熱得比都別桌慢。
「喔〜水開了。現在就可以放肉進去了嗎?」問話的時間,光已經用公筷夾起一大把羊肉卷。
上午和進藤商量好,讓他晚上叫和谷來打邊爐,沒提伊角也會在。
現在看著光在一片寂靜中旁若無人地往鍋裡放食物、撈起來、蘸醬、送進嘴裡,耳邊全是他吃飯的聲音,楊海努力抑制嘴角的抽動。
唉,孩子還在長身體,大概真的是餓了吧!
「嘛,夏天就是該吃這種東西嘛。」舀起一瓢丸子,裝作若無其事地問:「伊角啊,這幾天住得怎麽樣?和兩年前相比感覺有什麽變化?」
「氣氛還是很輕鬆,和兩年前一樣覺得很自在。」伊角也很自然地笑道,「雖然現在很多人都回家了,這些天在練習室也認識了不少新面孔呢。」
「上半年確實有很多新人被選拔來棋院,宿舍都快不夠用了。我一個人住雙人間的日子怕是要到頭了啊。」
「年輕的強手真的很多,看來圍棋在這邊推廣得很好。」
「哈哈哈,畢竟我們北京隊成績好嘛!不過還是頭一回聽人說在中國棋院過得很『自在』欸。」
和谷朝這邊瞟了一眼。
「就是⋯⋯」伊角低下頭想了想,「好像沒有那麼多需要應對的場合。好像只需要下棋、研究怎麼下好棋,就夠了。」
「——哈,所以這就是你想留在中國的理由?」
光是在午後的護城河邊找到和谷的。
聽了楊海的提議,他拿著看不懂的地圖邁出棋院大門,像沒頭蒼蠅一樣在附近轉了一圈,才想起應該給和谷發郵件問他在哪。
沒想到那家伙這次居然秒回:「我在玉蜓公園。」
「玉蜓公園在哪啊?」
有一隻手搭上光的左肩,「就在你背後。」
「啊啊啊啊——嚇死我了!」
看見光像個袋鼠一樣跳起來,脖子上那條他們曾經在古著店同時看上卻被光霸占的哥吉拉周邊項鏈都甩到背後去,和谷瞬间覺得心情好了不少。
「你怎麽跑這兒來了?伊角學長呢?」
「還在練習室吧。話説你們今天早上怎麽了?」
「沒什麽,在圍棋上有點意見不合罷了。」
「喔〜這不是挺常見的嘛。那晚上去吃火鍋嗎?楊海先生説要請客。」
確實是在圍棋的問題上意見不合,可並不是和圍棋直接相關。真正研討圍棋的時候,和谷並不是固執己見的人,可是——
「伊角學長,爲什麽突然問了轉籍的事?」
「因爲之前就有想過要不要留在中國棋院。」
「之前?」
「嗯,大概是從年初的時候開始的吧。」
前天從沙县小吃回到旅店,聽伊角這麼說的時候,一種很熟悉的心情湧回來。
兩年前,進藤突然不再下棋了,那傢伙那麼強,進步那麼快,卻可以說放棄就放棄。
和谷一直對人際的事情非常自信,進藤出了那麼大的事,卻什麼都沒跟他講,明明二人已經屬於親密的朋友。
現在連伊角也——
「年初?可是你才在中國待過多久?」
「⋯⋯之前住在這裡的兩個月已經足夠了解很多事了。」
「那你知道轉籍意味著什麽嗎?」
伊角深吸一口氣。「我當然想過。」
「——那你是決定了?爲什麽?怎麼可以這麽輕易?」
伊角沉默了一下,與和谷對視一眼,又移開目光。
「我也説不清楚,只是覺得我不適合再這樣下去。」
「什麼叫你也説不清楚?」
之後事態就失去了控制,和谷現在仔細想來,他們吵的内容其實都很廢話,幾乎都是情緒化的抬槓。伊角不願坦承以待,他也無法說服自己去接受這個事實。
沒道理去干涉他人的職業規劃,可他到底私心地不希望伊角離開。
親身經歷了北斗盃,整整兩週的特訓,認真遵循了制定的戰術,比賽時也超常發揮,下出了不會後悔的棋,可即使兩局都贏了,還是感受到了强烈的不甘心。
看著日本隊第二次墊底,網路上的言論和國內媒體的措辭都一樣刺眼,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日本的圍棋距離中韓有多遠。
這不是靠他一個人的努力,甚至不是靠贏下一次北斗盃就能扭轉的局面。需要有更强的人在,需要所有人一起朝著那個方向努力,才能從内部改變日本圍棋既定的環境。
他希望越智和社能在,他希望進藤能在,自然也希望伊角能在。
於是在護城河邊的柳樹下,和谷答應了光的邀請。
他不是沒想到伊角也會出現,只是不想再聽到他說起要離開日本這樣的話了。
「欸?什麼?!」光像突然醒過來一樣擡起頭,「伊角學長要留在這裡?!」
熟悉的破鑼嗓子又響起來,楊海四下瞧了瞧,幸好火鍋店裡已經夠吵,只有附近幾桌人短暫地看向他們。
「是啊,」話是對著光說,和谷的眼睛卻一瞬不瞬地盯著伊角,「這個人前天突然自己說的,那會兒才知道,已經盤算了半年都沒告訴我。」
「你⋯⋯非要在這時候和進藤提這件事嗎?」伊角無奈地看著他,「吵了一天還不夠?」
和谷坐直起來,手掌壓在桌沿上,「所以你是認真的?真的已經決定了?」
「也還——」
「棋院那邊又要怎麼辦?」
聞言,伊角移開目光,想了想。
「去年底的時候,棋院有對今年和中國的交換項目進行篩選,不過年齡上限還是壓得很低。大概這種名額就是會留給更年輕的人吧。
「還想轉籍過來的話,就只有給理事會遞辭呈,然後由中國方面接手——」
「我問的才不是這個!」和谷手裡的可樂罐敲在桌上,「你就這麼不喜歡待在日本?」
「——不,不是說不喜歡在日本。只是,我可能不擅長吧,很多圍棋之外的事情。」
伊角的視綫順著烟霧飄到別處,也不知道在看哪裡。
「圍棋之外?」
「嗞——嗞——」
放在桌面上的黑色夏普翻蓋機忽然震動起來。
「啊,那個,是我的郵件。」光灰溜溜地把手機拽到桌下看,見是亮回覆:「你們玩得怎麼樣?已經有和那邊的棋手對局了嗎?聽說中國棋院的競爭很激烈。」
「⋯⋯而且感覺,」聽伊角接著說,「日本棋院就算沒有我,也還有很多有實力的年輕棋手,大家都是比我優秀很多的人。」
「那你的意思是,」和谷氣不過,一下拍桌子站了起來,「中國棋院的棋手就沒有實力了?!」
他的聲音嚇得光手一抖,把沒編輯完的「是很激烈」這四個字發了出去。
「殴⋯⋯」
又要被這傢伙唸不帶標點不落款沒頭沒尾了,要不還是先靜音吧。
「喂,我才不是——」
「嘛、嘛——你們都先別激動。」
楊海起身把和谷按回了座位上。他終於大致明白了他們在吵個什麽東西。
「其實啊,我以前也去韓國進修過很長一段時間,也差點要留在那邊呢⋯⋯」
剛剛還在對峙的兩道目光齊刷刷投過來。光重新拿起筷子看著鍋裡翻滾的肉。
「因為當時韓國的圍棋特別強,而且沒有人在意國籍或者出身,只要好好下棋,就能得到認可。我剛到的時候,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語言完全不通,更不認識什麽人,但遇見的人也都很友善,交到不少朋友,還學會了韓語。
「可即便是這樣,我最後還是決定回來。原因很簡單,就因為我爸媽還在中國。」
伊角很驚訝地看著他,「楊海先生⋯⋯」
「畢竟我老家太遠了,即使在北京都很難經常去看望他們,根本沒有直飛的航線,更別説從首爾了。所以在這兒安定下來之後,就把他們也接到這邊住,方便有個照應。
「嘛,」楊海喝了一口酸梅湯,笑道,「大概對日本人來說會比較難理解吧,『寸草春暉』,什麼的。」
光忽然抬起頭來。
「——誰か言う 寸草の心、
三春の暉に報い得んと。」
「啊?」和谷皺起眉,露出極為困惑的表情,「剛剛那個是什麼?」
「是講父母之恩的漢詩吧?楊海先生剛才說的。」
「呃、對。」對著光,楊海流露出一絲狐疑,又很快正直地看向和谷,「就是這樣。」
「父母嗎⋯⋯」
伊角低下頭,看向自己的手。
好像真的很久沒回家了。
從小時候起,父母就一直很理解他學圍棋的選擇。即使後來幾次都與入段失之交臂,他們也從沒要求自己回去上學或者找別的工作。甚至是突然說要在中國多待兩個月的時候,父親也只是問:「那這段時間的旅費怎麼辦?需要匯過去嗎?」
對於一個單職工的普通家庭來説,孩子很早就決定要學圍棋,放棄升學,參加每年只有三個名額的考試,打算以這種常被視爲中老年人怡情娛樂的活動為職業,依靠和人對弈來維持生計,這應該是很難以接受的事吧。
「小慎,不要太有壓力,休學的事情讓媽媽來操心就好了,你專心上課吧。對了,明天的早飯想吃什麼?」
可他們就是一直無條件地信任著自己。
等到終於考上職業,有一份穩定收入,也恰好是快要成年的年紀,於是順理成章地搬出來獨立生活,算是給還在唸書的兩個弟弟騰出了房間,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越來越零碎和短暫。
「好像確實,我也沒有辦法就這樣離開他們⋯⋯」
在異國强大的對手之間,真正地開始懷疑自己的棋能否支撐自己的時候,接起電話,是父親穩重的聲音給了他重新面對挑戰的信心。
比起僅僅是因爲到了該自力更生的年紀就不得不放棄夢想的人,他真的已經很幸福了。
楊海端詳著伊角和和谷的表情,「總之,是否在一個地方生活的原因可以很簡單。特別是對於棋手來說,只要有棋盤和棋子,在哪裡下棋,也沒有決定性的區別。」停頓了一下,「畢竟,圍棋本身才是自己的錨點。」
和谷向後靠在椅背上。氣泡在鍋中破裂,白霧升到頭頂的燈光裡。
圍棋才是自己的錨點嗎⋯⋯也只有像楊海先生這樣,對「自己的棋」已經有了概念、又足夠强大的棋手,才能夠説出這種話。
「伊角學長確實在竜星戰拔得頭籌之後,由於有那樣的實力,不論是在中國棋院還是日本棋院就職都沒有關係了吧。」拿起可樂喝了一口,「別說是竜星戰了,我現在最好的成績也只是阿含·桐山盃快棋賽的一回戰就出局了。」
明明森下老師對自己有那麽高的期望,卻只能用這種表現交代。
「哈,就因為有這樣的格差在,所以根本理解不了呢。想離開日本的人的心情。」
「其實我多少能理解呢!」
光嚥下嘴裏的丸子,突然說。
「總是待在一個地方打轉的話就是會看不清自己的目標。換個環境或許突然就⋯⋯」
「來來來,進藤君,嘗嘗這個,煮老了就不好吃了。」楊海從鍋裡夾起一堆食物塞進光的碗裡,「你在日本絕對吃不到的東西。」
「喔,是什麽?」
「是牛的胃。」
「⋯⋯可我覺得和谷能取得這些榮譽是遲早的事。」伊角說,「我跟你下過那麽多棋,是最瞭解你的棋的人之一,北斗盃的兩局、今年阿含·桐山盃預選的幾局我都有看,何況你那麼年輕,我學棋也比你早,這只是經驗的問題罷了。」
「呃⋯⋯」
雖然知道這是伊角學長忽略話中的諷刺,在真心好意安慰他⋯⋯可在場的不就還有一個年齡比他小,學棋時間比他短,更沒「經驗」,還已經打進三大頭銜循環圈的人——現在正津津有味地吃著某种内脏,辣椒粉像不要錢一樣地蘸,看著都覺得舌頭發麻。
其實很佩服伊角學長,在院生最後一年的職業考試失利之後,會選擇去中國進修,一待就是兩個月。
雖然不清楚那次考試到底發生了什麽,但如果因此而受到打擊、以一敗之差落選的是自己,在十九歲的年紀,又要面對那種程度的壓力,或許很難再重新振作起來了。
作爲曾經的同學和現在的同事,伊角他,棋下得好,個性又穩重,待人接物都很隨和,在院生的後輩裡風評也好。認真又自律,總是有新的目標,甚至在準備前來進修的這一年裡,還為了能和中國的棋手們自由交流而學習了中文⋯⋯
——也就是這樣的伊角學長,才能那麼輕描淡寫地說想離開自己的母國,去另一片沒有背景和牽掛的土地尋求發展,還説是因爲「日本棋院不需要他」。
「而且,和谷還有許多我不具備的才能。」伊角繼續道,「沒有成為職業多久,在處理人際上已經比我成熟很多。常常覺得,如果不是因為你,就不會認識那麼多下棋的朋友。當初能加入九星會也是多虧了森下老師的引薦,才讓我有交流圍棋的好去處。所以說⋯⋯」
「伊角學長⋯⋯?」
聞言,和谷有些驚訝地看過去。
「啊啊,其實從新初段聯賽的時候就意識到了。每次面對媒體都會特別緊張,也不會說那些場面話,直到現在也沒有長進。
「在中國棋院,我曾經向楊海先生學習到在對局中調整心態的方法,可是除了圍棋之外,我真的有很多不擅長的事。比起棋賽,反而是這些工作帶來的壓力更大。」
原來是這樣嗎⋯⋯
這麼說來,以前確實有聽伊角講過這些事。不過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遇到棘手的營業場合,職業棋手們私下也都會互相抱怨幾句,和谷并沒有太放在心上,也從未想過伊角因爲這樣的原因就會有想要離開日本的念頭。
今年四月通過了北斗杯的預選,確認成爲出戰選手時,和谷很興奮地給伊角去電,伊角還説要去北京觀戰,可這個計劃又被突如其來的工作打亂,而黃金週後從札幌回來的伊角狀態似乎也不太好——
「伊角學長已經開始喝酒了啊?」仔細一想也是,伊角的生日在四月。
「嗯,前幾天在札幌就喝了,」伊角把手裡的青島啤酒放在出租屋的矮几上,苦笑一下,「可惜都不是什麽很好的回憶。」
在自己的百般追問下,伊角才説清楚那些天到底發生了什麽。
是在文化廳主辦的圍棋交流會上,下指導棋時他不小心碰倒了水杯,濺到一個官員的西裝,就被要求在棋盤上與對方下五子棋,輸了之後又被灌了很多酒,趁他喝醉,還問了很多私人問題來調侃他。
圍棋經常在這些政商界的社交場合出現,就和茶道、書法、日本畫一樣是拉攏民心的文化噱頭,至於職業棋手在這種工作裡,面對的是否是真正了解圍棋、想要交流圍棋的人,并不是很重要,能達到宣傳和拉贊助的目的就行。
下五子棋的要求可能只是個惡劣的玩笑,其實換做是自己的話,只要找個認識的負責人,好好賠不是,打個圓場,把對方哄服帖就可以走了,根本沒必要浪費時間。只是伊角學長太認真了,又是耳根子很軟的個性,才無法拒絕這樣的刁難。
這些年來跟著森下老師出入各種場合,和谷早就學會了用平常心來看待這些事。
「和圍棋的實力根本沒有關係⋯⋯已經二十歲了啊,我,真的好沒用。」
「——才沒有這種事呢!那種東西,愛怎樣怎樣吧。你棋下得這麼好,根本不用在意這些小事。」
唉,看來以後真的要在這方面多注意伊角學長才好。
這麼想著,和谷的視線又不自覺地落在光身上。
進藤⋯⋯?還是算了吧,雖然也是天然系的樣子,可那傢伙下五子棋是真的很强。
「不,是我不好⋯⋯因為這麼點事就想著靠離開日本來逃避。明明是和谷可以做得很好的事,只有我⋯⋯」
「伊角學長!」和谷突然抓住他的手,「別這麼說了,都是我⋯⋯是我還不夠強!所以才在無所謂的地方顯得有點長處。」
「是我⋯⋯而且我不該把不成熟的想法說出來,讓你擔心了。」
「伊角學長⋯⋯」
「和谷⋯⋯」
「哈哈哈哈哈!」
身旁突然爆發出一陣笑聲,讓很多視綫都聚集過來。
「抱歉抱歉⋯⋯」原來是楊海,他一手扶著額頭,笑得眼淚都要出來了。
「我說,你們一個個的,謙虛也得有個限度啊!」
三人齊齊看向楊海,連光都暫停了放魚滑的動作。
「一位是史上最年輕的竜星戰優勝,一位剛拿了北斗盃兩勝,還是森下茂男的關門弟子,明明都是前途無量的年輕人,居然在這兒挑自己的刺兒。
「唉,有時候真覺得日本人,就是心思太細了吧?」
捏著下巴思考了一下,楊海突然越過火鍋裡翻滾的魚滑看著光。
「嗯⋯⋯所以進藤君,論壇上說的,你是混血的傳言其實是真的對不對?」
「啊?」
這場風波就這樣結束了,2003年的北京之行,和谷和伊角好像曾面臨過這樣重大的友情危機,好像又沒有。
伊角居然曾考慮過要去中國生活,他後來也許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即使面對很多人講話還是會緊張,主業之餘卻也開始出席一些圍棋講座。
而光從此對火鍋的印象,也莫名地和遙遠的未來聯繫在了一起。
——唯一可以確認的是,伊角學長的酒量,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很讓人擔心的水平。
tbc.
[1] 植入棋魂官周香氛的廣告。光的味道是芒果,亮的味道是茉莉。
[2] 2003年進行的是第58期本因坊頭銜戰,挑戰者是緒方。於此同時進行的光和亮參與的循環賽對局是為取得2004年第59期的挑戰權。也是因此他們沒有參加第二屆北斗盃。
[3] 「塔矢Jr.」。
[4] 一些雲南特產鮮花餅。
[5] 北京已經沒有崇文區和宣武區這兩個名稱了,2010年崇文併入東城,宣武併入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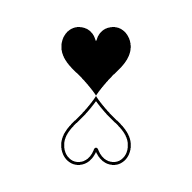
原来在北京吃火锅的经历是在这里啊~2003年的夏休,还没有那么成熟的光,独自出行的经历,在第七章那么惨烈的分手之后阅读这段,真的会有种回望遥远的过去的感觉。那之后大家都各有变化,也依然有不变的东西在。
看到和谷的邮件真的会爆笑🤣尤其是看到“ARE YOU HUMAN TRAFFICKER”的时候,结果在和谷从天坛东路去机场找人堵路上的时候,光已经逛了小半圈北京了,吃了一桶泡面三根火腿肠一块鲜花饼,还下了一盘棋。真是辛苦他了,和伊角还在吵架呢,结果进藤也不是个省心的,为了找他还找伊角写中文邮件。
比起一板一眼的正直小伙伊角,杨海真是很有中国人的特质,比如原作里:不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住我房间的剧情,和这一章里的:不被售票员发现的话也没事、用火锅化解了和谷和伊角的纷争,让人非常喜欢~
哎呀,看原作的时候就超喜欢院生时代这三个人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因为光是三个人的里最小的,这种被他们俩关照的感觉真的很好🥰有种家里的弟弟的感觉。想起在第六章里帮助光和亮的两人,就会打心里觉得有他们在真的很好……
從AO3找過來,想看完結篇啊!一定要HE啊!
完结篇,好长,在奋斗。
哇呜您是不是修文了!我就好比从桃花源出来之后今天找不到入口了QAQ顺便问一下之前就馋嘴的问题吧:冰糕就叫冰糕吗?到底长啥样什么味道(舔嘴角gif)
(ᇂ_ᇂ|||)不仅修文而且是还在修,虽然内容没什么大变动,只是替换了事件顺序让情绪流看起来更正常
这篇怎么这么多好吃的,半夜看得好饿QAQ刚想说前面篇幅里印象深刻的美食还是亮的生日火锅就发现果然收回去了。阿光可可爱爱小动作好多,嘬大一口
终于全部改完热!!这章里就表现了成长中的没那么成熟的光,有点脱线甚至看着有点烦www这样可爱的会让人担心的阿光,亮好像还挺喜欢的?(现在和他谈恋爱的那个已经是正经男人就太苏了,虽然也会习惯性撒娇,骨子里仍是喜剧人,可外在表现来说终归是长成了一副有担当的样子(叹气)所以大亮应该也时常对小光曾经无时无刻不展现出的本质的可爱感到怀念吧!(我猜(就像养的狗狗长成了大型犬,想起它小时候的样子还是会在心里融化❤(←不太恰当但又有点合适的比喻。
傻乎乎直愣愣大概就是阿光的可爱本色吧哈哈哈,看着他成长起来是件很奇妙的事(一些母性泛滥)劳斯很会写“可爱”,变声期的破锣嗓子这种容易被忽视的点我真的笑了好久。顺便冰糕那个,您的描述结合搜索勾起了一些久远的记忆,感觉小时候好像吃过但不确定是否有夹心,回头下单尝尝确认下。
哦哦哦关于冰糕忘记回复您,原材料是奶油杏仁粉,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可以是各种水果/花香口味的,一般是白色方块的外形,淘宝搜上海冰糕就可以看到,现在线下卖这个的比较少了,小时候去城隍庙都会买了吃,一种童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