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線的焦點外,整齊的竪排小字隨著列車有節律的顫動長出重影。
平成二十年[1]的一月二十九日。
無法相信。在報刊亭看了每一家報紙的日期,也只是「知道了」而已,還是無法真的「相信」。
如果這才是現實,自己又怎會如此自然地認為是去年的十二月十四日?
印象裡,今天是二十一歲的生日。早飯吃了味增湯和柴魚風味的厚蛋燒,之後排了點吳清源大師的棋局,中午時媽媽提出開車送自己去棋會所。
「您已經很久沒有開車了,為什麼今天突然⋯⋯?」
「為了晚上小亮過生日,要去買一點東西,正好順路。」
當時她笑著回答。
下午和進藤下棋,收到大家的禮物,以及進藤提出的,「去一個地方」的邀請。
一切都按照生日那天進行,只是,今天並不是他以為的那天。明明是非常有實感的十二月十四日⋯⋯難道媽媽、進藤、市河小姐,所有人都在自己不記得的這段時間裡⋯⋯
不記得的這段時間。
這中間的一個半月,發生了什麼?像光滑地被削去了一樣。只對自己削去了。
問題出在真正的生日那天嗎?好像有某種痛苦的事情⋯⋯
——不行,記不起來。
一月號的《圍棋世界》拿在手裡,隨便翻開在這一頁,指尖已經讓頁邊變得凹凸不平,一個字都沒看進去。
父親的名字顯得很刺眼。
「第1回國際圍棋大師戰 塔矢行洋vs.徐彰元(中國)
「世界最強,塔矢行洋榮冠!
「自戰解說·塔矢行洋九段」。
是一篇專訪,事實上的無可辯駁——可意識裡還覺得父親今晚才會到日本。
進藤⋯⋯也一定在這段消失的時間裡發生了未知的事,這個在身邊一路跟著自己的人。
他就在左手邊,像睡著一樣坐著,只有手指來回絞在一起,無力的肩膀垂得很低,看不清表情。
車廂的窗框裡滑走的景物顯得焦躁。
在大久保停站時,車門灌進來的風將手裡的雜誌往前翻了幾頁,停留在適才瞥到的標題⋯⋯「進藤本因坊・珠玉的詰棋」。
果然是這樣吧。在不記得的日子裡,進藤如常地下棋、接受採訪、為編輯部撰稿,過著一如既往的生活,而他不在其中。
那麼今天的謊言也是——在做給他看,做出今天真的是十二月十四日的樣子。
下棋時的靈感、說要帶他去一個地方的認真、整理圍巾時親暱的動作,這些都是⋯⋯在欺騙嗎?
從在報亭追上他開始,直到上車之前,進藤一直試圖和自己搭話。面對那樣關切、擔憂、緊張的態度,卻無法給予任何回應,他覺得胸口壓著一團腫脹的雲。
電車重新啟動,轉過一個彎。車廂像微微傾斜的紙盒,長長的車尾透過空蕩的走道擺動。
亮想起和光的第一局棋也是在一個十二月。
那年的新年,第一次無法專注於團聚的氣氛,頭腦中塞滿那場無法解釋的相遇,進藤明顯是初學者的手,和讀不透的、高深莫測的棋路。
第二局在一月。到現在也說不清當時的淚水到底是被進藤滿不在乎的態度刺傷的憤怒,是全力以赴卻還是輸給了那樣的人的不甘,是面對前所未見的強大對手的無措,還是對一直以來過分順遂的生活的迷茫。
只知道等擦乾眼淚走出去的時候,適才淋濕他的驟雨已經停歇。
從光考上院生,重新出現在自己視野中的那一刻開始,覺得這個人是為了跟他對弈、追趕他,才繼續下圍棋的。
沒來由地,甚至過分自信地這麼想著。
一個與自己本無關係、毫無相似之處的人,只有圍棋使他們相連。等反應過來時,卻發現已經因為彼此而做出了那麼多改變。
只是,一直到現在,這個人撒謊的技巧還是這麼差啊。
——喉頭有些發緊,低下頭,讓兩側垂下的黑髮包裹住視野。
只想把剛才街上的畫面從腦子裡剔除出去。
不想看到,他無機質的慌亂眼神,不經意皺起的眉毛,硬是扯出來的笑容⋯⋯
明明是很喜歡的臉,卻用這樣難看的表情來對自己說出違心的話。
會心痛。
下車,在改札口再次看到了今天的日期。沈默地一起出了站,本以為會焦急地飛奔回家,可雙腿好像已經麻木。
走過二十一年的路,明明幾乎什麼都沒有變,此時忽然覺得陌生。
院門打開的時候,屋內有腳步聲朝玄關過來。
院裡玉蘭樹的花苞確實比記憶裡更綠了一些,不去留意的話並不會在意到。
是明子打開了門。「——小亮?進藤君?」
她似乎很快猜到發生了什麼。
迴廊裡出現了陽光。灰塵在光線中漂浮,從暗處消失。木地板的條紋和障子的陰影在眼前畫出迷宮。他們跟著明子走到客廳。
「媽媽,是生日那天的事嗎?」
「是一場車禍。」
接過明子手裡的檔案袋,亮跪坐在矮几前,緩緩旋開白色的棉線。
「緒方先生載你回去的時候,在四ツ谷3丁目的交叉點,撞上了違章行駛的卡車⋯⋯」
十二月十五日的幾份剪報貼滿兩張白紙,放在檔案袋的最內側。
事故現場被黃色警戒線圍起來,白色的集裝箱貨車橫在路中間,車燈還亮著,碎玻璃和金屬殘片在底盤的車架右側撒了一地,道旁的一根電線桿倒在駕駛艙上。
紅色的保時捷跑車側翻在大約五米遠的地方,車頭凹陷,引擎蓋彈起。
肇事者和當事人的姓名及身份信息都被撰寫者隱去,可能由於是發生在鬧市區繁華路段的交通事故,又致使當日部分區域的交通甚至供電狀況都受到影響,所以才會進行如此篇幅的報導。
「那緒方先生和⋯⋯那位司機,他們怎麼樣了?」亮有些焦急地問。
「都平安無事,緒方君只是輕傷的撕脫性骨折。」
「是嗎。那就好。」
鬆了口氣,目光來到檔案裡的一張X光片,漆黑的底色上,白色的腦組織切面像被束縛在頭顱裡長不開的花朵。
「小亮的外傷,其實並不嚴重,沒有動很大的手術。但是⋯⋯」明子有些猶豫,「顳葉內側的海馬體受傷,有影響到長時記憶的功能——」
「也就是說這天之前的事情都還記得,但每晚睡著之後,當天的記憶就會消失?」
這樣一來就解釋得通了。
「⋯⋯是的。」
病歷的字跡有些難以辨認,對於能夠看清的醫學名詞也沒有多少實感。
穹窿細胞功能正常、海馬旁皮質撕脫、中顳葉記憶系統受損。
明明是在說他的事。
怎麼會。
「真的⋯⋯有呢,縫合的傷疤。」
循著字面的描述摸到了外傷的創口,頭髮下面的一塊皮膚凸起一道一指寬的痕跡;已經不會痛。可這種觸感卻在清醒地向他傳達著他「知道」卻不「記得」的痛苦。
「⋯⋯媽媽,我想到醫院和醫生談談,聽他親自告訴我病情,可以嗎?」
「小亮已經聽過很多次了,」明子低下頭,「在住院的時候。」
「可是——」
「明子夫人,請帶塔矢去吧。」光在這時插話道,「正好,我也想聽聽,最新的情況。」
藍灰的天色慢慢籠罩下來,細雨斷斷續續地飄落。
坐在車的後排,明子開車很注意,只有輕微的晃動。
「這個,」亮把檔案袋遞給光,「你看吧。
「反正我也記不住。」
光望向他,抬手接過紙袋,抽出最上面的剪報。目光透過金色的額髮,認真地注視。
所以,從十二月十四日到今天,現在在眼前的是自己曾經記住又忘掉的四十七天後的進藤。
意外地,並沒有明顯的疏離感。
以十二月十四日為座標原點,這之前的記憶確實存在於腦海之中。
看著車外一晃而過的熟悉街區,想到進藤最後一次試圖向自己表明心意的場景。
那是十一月中旬的一個下午。他剛剛接受完編輯部的採訪,去四樓的自動販賣機前排隊,想買一罐綠茶。
前段時間,名人戰與天元戰的棋局交錯在一起,三天前剛成功從緒方先生手裡奪取名人頭銜,從熱海的對局地點回到了東京。
上一次去熱海還是在七月份合宿的時候。
進藤喜歡拉著他摻和年輕棋手們的社交圈,相熟的同樣是院生畢業的和谷義高七段好像也是很擅長組織活動的人。
時隔四個月,面對同一座城市的同一處景觀,在同一棵棕櫚樹下依稀辨識出記憶裡的顏色,想起七月帶著潮氣的熱風,慢慢地長舒一口氣。
那時是盛夏,一群年輕人鬧哄哄地早上四點多就爬起來,去沒有人的沙灘上看日出。
漁船還沒有回來,海鷗三三兩兩時飛時落,水滴似的月亮仍掛在天邊,東方白色的太陽緩緩昇起,淺藍的清晨浸透溫暖的金,薄薄的潮水一層一層畫出新的海岸線。
「塔矢!原來在這裡啊。」在海浪聲裡抬起頭,看見熟悉的身影逆著晨光走過來,手裡的水桶「颯」地放在面前的沙地上,水從邊緣搖晃著灑出來滲進沙子裡。
「這個幫我看著一下!」
「嗯?」水桶裡有幾尾小魚,「你們這麼早就開始釣了嗎?」
「是啊,要趁完全漲潮之前。」進藤回頭看了一眼,又轉過來,「你呢?在這裡做什麼?」
亮指了指地上揮舞著鉗子的黃白相間的小生物,大小懸殊的兩隻鉗子使牠走起路來一搖一擺。
「來看這個螃蟹洞。」
這隻招潮蟹正在奮力地挖掘,濕沙子在周圍掀了一圈。
常居都市,不太見到純粹的自然風光,便對這隻小小的、認真的甲殼類產生了好奇。一點點泛著細小泡沫的潮水淌上來,滑過兩人赤裸的腳背。
等浪花退去,那一小圈沙子、細密的腳印和臥沙的痕跡溶進深金色的水漬裡,不復所蹤。
「——這樣,就只有我們知道牠來過。」
整理了下被風吹亂的碎髮,亮循著海浪的蹤跡,瞇起眼睛望向遠處。
朝陽在水色的眸子裡閃爍。
「⋯⋯塔矢!」進藤在這時突然握住了他的右手。
緊張地對視,眼前的人深吸了一口氣。
「其實,我一直有想對你說的,如今在這個世上,也許只有你才會明白的事。」
大概是自己露出了過分驚訝的表情吧,進藤突然有些侷促,很快又低下頭移開了目光。
「而且我已經喜——」
「救命!來人啊!!越智、越智他溺水了!!!」
女孩高亢的聲音傳遍了沙灘。
循著聲音望過去,幾十米遠的地方,奈瀨站在及腰的海水裡用力揮手,得到他們的注意後便開始往遠離海岸線的地方游。隱約看見她身後有個人影在一道一道的海浪之間掙扎。
「欸⋯⋯可惡啊!」進藤喊了一聲,便轉頭往海岸的方向跑,「我去看看!」語氣對於這個場景來說好像過於憤恨了。
他也急忙跟上。
「——越智!奈瀨!不要緊吧?」
「哎喲,好沉啊!」等來到事發地,擅長游泳的奈瀨已經把越智拖到了沙灘上。「應該沒事,人還醒著。呼,幸好我及時發現。」
事情也驚動了海之家的老闆娘,幾人在她的招待下坐著休息了片刻,越智也緩過神來,吃了點甜食。
好像只是抽筋而已,他自己阻止了他們叫救護車。
萬幸那天沒有人受傷,越智和救了他的奈瀨,他們都平安無事。
只是⋯⋯
每次,好像每次要發生什麼的時候,就會被打斷?
秋天在京都的時候,還有九月二十日,直覺告訴他,那個燭光晚餐也是為了營造一些氣氛。
——「喜歡」、「喜歡你」、「喜歡上你」?那時,進藤是想對他這麼說的吧?
想像著進藤的嗓音,補全了這句淹沒在晨間海風裡的話,站在棋院安靜的走廊裡,反覆咀嚼著這個漸漸遠去的,燥熱而沈寂的夏天。
「啊!」
右邊臉頰突然被什麼東西冰了一下,嚇了一跳。
「是我啦。」回過頭,看見光望著他笑,說著把冰涼的綠茶從他臉上拿開。「現在有空嗎,塔矢名人?」
「不許這麼叫。」趕緊收起了好臉色。「怎麼了?」
「我在藏書室發現了有趣的東西,快來看。」
從光手裡接過還滴著冷凝水的綠茶,有些猶豫地跟著來到藏書室門口,看他從口袋裡拿出鑰匙,熟練地開了門。
除非有特定的棋譜想要研究,或者有工作需要,亮很少去藏書室,畢竟每次都需要執勤的管理人員開門。
這裡除了日本棋院過往的期刊和著作,還完好地保存了一些昭和之前的圍棋出版物和古籍,其中有許多古舊的棋譜還未經整理,需要辨析真偽、確定對弈者和對弈的場合,再加上現代的註解才能成為對業餘愛好者來說更易懂的讀物,於是某些職業棋手也會和出版部協力來完成這些工作。
而進藤看起來一直有這方面的興趣。
空氣裡充滿著乾燥的陳舊纖維的味道,細小的灰塵沙沙作響。
「就是這個。」
光拿起桌面上的一張棋譜切頁的影印件遞給他。
「——是秀策和『那個人』下的一局。」
亮掃了一眼,紙上寫著「安政二年・玄庵・本因坊秀策自筆」,看起來是秀策平日自己撰寫的棋譜。
黑先開啟無憂角佈局,白棋佔了星、小目,再分頭破黑棋大勢。掛角、二間高夾,黑棋穩健地下出試探的一手,白棋置之不理。黑守角後跳出,雙方模樣漸成,只好打入白棋的空地,開啟了中盤的混戰,大龍被步步進逼,察覺此戰不利便開始搶佔實地,白當頭一鎮,採用棄子互利的手段來封住腹地,黑見形勢不妙打入破空,佈下陷阱企圖殺子做活,可惜白棋一眼看穿,妙手頻出,黑龍做活無望,只得中盤投子。
——「那個人」?是指譜上那個與平明秀麗的秀策流迥然不同的人?而秀策並沒有記錄對手的名諱,一個身分不明的、攻勢張力極強的高手⋯⋯有些似曾相識的局面,一時分不清是親歷,還是見過的他人的對局。
「等等,」在光又要說什麼的時候打斷了他,亮低頭端詳著手中的棋譜,將鬢邊的髮絲捋到耳後。
「我有⋯⋯見過另一張風格相似的棋譜。應該是,在第三排書架的最上面一層沒錯。」
有一件不得不和進藤確認的事。
踩著喀喀作響的不鏽鋼台階慢慢爬上去,光在下面扶著。
剛才擺放的時候梯子應該再往左一點的,不過稍微踮起腳應該可以夠到——
「欸——?」
突然失去平衡的感覺。
「塔矢!小心!」
還沒反應過來就摔到了地上。
——不對,比起地面,這個觸感顯然更柔軟些。
抬起頭,不意外地看見了光的臉,金色的碎髮散亂地搭在額頭。
慌忙地撞上那雙琥珀色的眼睛,像很近地望著某種星體一樣,幾乎覺得眩暈。
模糊地聽見鋁罐滾動的聲音,是綠茶的味道——
真離譜啊,拿著開封的飲料進入滿是印刷品的地方已經夠沒有常識了,竟然還灑了出來——可是,為什麼,現在完全不想移開注意力。
「沒事⋯⋯吧。」
彼此的呼吸糾纏在一起,和心跳一起佔據了全部的聽覺。眼睛看著光的嘴唇微動,話語的聲音逐漸從視線脫離。
下意識地揪緊了光胸前襯衫的布料,手指碰到下面結實而溫暖的觸感。
彷彿重新嗅到今夏遺憾的海風。
完全無暇回應他的話,腦子裡只顧得上在意那兩片淡粉色的、乾燥柔軟的唇瓣,和四周包裹著的,逐漸取代了海的記憶的,此刻從光身上傳來的淺淡香水味。
默許的、過於近的距離。小心地、慢慢地低頭,閉上眼——
想吻他。
現在最想做的事,是去吻他。
不想再拖延。這個想法一出現,就被佔據了全部的思維。
「年輕人呀⋯⋯」蒼老尖細的聲音突然從門口響起。
「要小心一點。拿書用的梯子下面有個鎖,下次要記得鎖上啊。」皮鞋在地板上一步一步踏出門外。「嚯、嚯、嚯。」
直到他人的調笑把知覺拉回了現實。
「哇啊啊啊啊桑原老師——」
光好像被嚇了一大跳,亮也匆忙從他身上爬起。
身體還有些眷戀離遠了的體溫。
——可惜已經不會再有這樣的場景了。這便是記憶中他們的最後一次錯過。
其實應該慶幸那時桑原老師並沒有追究灑在地上的綠茶才對?
銀色的SUV平穩地駛入了醫院的地下停車場。
跟著穿白大褂、戴眼鏡的大約四十多歲的男人來到腦神經科,亮按門診的要求先去放射科做核磁共振,明子通知了緒方和塔矢行洋,留在診室等候。
「失陪了,我出去透透氣。」
消毒水味、不知哪裡來的尖銳噪音和除此之外過分的安靜讓光坐立不安。
走廊裡飄蕩著灰白的、凝重的味道。光站在電梯前,盯著金屬門上自己模糊的倒影。
剛才面對明子夫人的微笑,有些無法呼吸。
每個人都做著該做的事,是自己執意要帶塔矢出去,才會變成這樣,可她沒有表現出半點責怪。
想要用一種溫善的方式把塔矢帶回這個真實的世界,一直隱隱有這樣的念頭,可從現實考慮,這對已經失憶的塔矢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要讓他面對殘酷的真實,就會無法避免地⋯⋯親手傷害了他。
自以為是的溫柔,如今看來只是一種可笑的自大。意識到這點,開始覺得痛苦;在不幸已經發生後,這份想要交流的渴望,仍是出於他的一廂情願吧。
「叮——」
倒影從中間裂開,一個白色的身影從四方的燈光裡大步走出,在他面前突兀地停下——
眨了眨眼,抬起頭。「緒方先生——」
「這就是你所謂的『解決辦法』?」
該來的訓斥終於來了。
在門口撞到狂熱的棋迷以致於真相被全盤托出,這種事確實沒想到,也無法事先預測——但現在明顯不是這麼去解釋的時候。
「就算他明天會忘掉,他所失去的本來可以安然度過的今天,要如何彌補?如果被人謠傳出去,你又能替他擋下任何媒體的壓力?」
是啊,如此無力的自己,事實上什麼都沒能做到。
「玩弄他、傷害他,欺騙他,自鳴得意、得寸進尺。」
沒錯,罵得一點都沒錯。
「十二月十四日之前也好,之後也好,亮是那麼真心地在意你。」
塔矢⋯⋯
「進藤,你知道你根本不配嗎。」
緒方的話在腦海中迴響。沈默在空曠的走廊裡蔓延。
盡頭傳來輪子在大理石地面滾動的聲音。
一名護理師推著盛放醫療器械的推車經過他們身邊,疑惑又小心地看了一眼,便快步走了。
見光沒有任何反駁的意思,緒方也安靜下來,低頭去摸菸盒,意識到是在禁菸的場所,頓了一下,又放回去,單手插回西裝口袋裡,皺眉看向遠處。
雨大概停了,白色的走廊反射著遠端流進來的純白的天光。
緒方倚在牆上,一側浸在濃烈的光線裡,灰白的影子從另一側肩上垂下來。
光聽見男人長嘆了一口氣。
「⋯⋯那天轉彎的時候,亮就坐在副駕駛,」低啞的聲音再次緩緩穿透刺眼的沉寂,「我,明明知道這點,卻還是下意識地往右打方向盤。
「他一直像信任塔矢老師一樣信任我,可親手葬送了他的未來的,是我啊。
「哈,真是。如今再跟你說這樣的話,大概也只能讓自己好受一點罷了。」
光慢慢睜大了眼睛,這才抬起頭注視這個男人的身影。
在生死關頭做出的自保行為,是任何人、任何生物最本能的反應。應該是無可追責的才對。
可身為唯二的當事者,心裡卻一直壓著沈重的愧疚。
緒方先生⋯⋯
「這個給你,拿著。」
「呃,這是——?」
緒方從西裝內側左邊口袋裡取出、放在手心裡遞給他的,是兩隻唐紙疊的紙鶴。翅膀和尾巴有褶皺的印跡,又被重新展平;摺痕上有些褪色,內側卻保持著原本的鮮豔的紅,似乎沒有被打開過。
「當時我也暈過去,是在救護車上清醒的時候,才發現在手裡的⋯⋯你給他的東西。是時候物歸原主。」
小心地接過,光下意識地輕輕將它們的翅膀展開,重新捲成折好時立起的樣子。
「和原來,一模一樣呢⋯⋯緒方先生——」
「哼,濫情的話就免了。我看掃描的結果差不多快出來,你也該回去陪著。」
「——那緒方先生你?」
「多聽一遍他的事,於我無益。」
圍坐在診室的辦公桌前,掃描成像的結果顯示在醫生身側的屏幕上。
「從這樣的腦部圖像來看,暫時還沒有恢復的跡象。」醫生看著亮說,「顳葉在車禍的撞擊中受損相對嚴重,因此阻止了在睡眠時將短時記憶轉化為長時記憶的能力。」
之前在前台的時候,護士也明顯認得亮,知道他的主治醫生是誰,登記本上他的那一頁還貼了一條黃色的標籤,面前的主治醫生應當也是如此⋯⋯
「也就是常說的『順向性健忘』。」
醫生觀察著他的表情,繼續道:「這種病基本不可逆,能夠保持現狀、不更加惡化已是萬幸。理論上可以自行痊癒,只是目前還從沒有過這樣的病例出現。」
亮平靜地聽著,輕輕點了點頭。
「不過,你能夠完整地擁有一整天的記憶,已經是較好的情況了。」
「較好⋯⋯嗎?」
醫生調整了姿勢,向後靠著椅背。
「克萊夫・威靈是英國的一位音樂家,他有和你一樣的病情,甚至只能擁有最多三十秒的短時記憶,相當於每三十秒就會『醒來』一次。在這種情況下,還堅持寫了二十多年的日記,每一條都是『我真的、真的醒了』,至今他仍然在嘗試記錄下自己『第一次醒來』的時間。」
「這,聽上去還真是辛苦呢⋯⋯」亮苦笑道。
「嗯,看來你的幽默感並沒有問題,」醫生雙手交疊,點了點頭,「感情的中樞,是由大腦的另一個區域控制的。
「威靈先生也是,現在已經八十歲了,還能進行演奏和指揮。
「可能因為音樂的藝術就是這樣基於感情和直覺的東西。」
亮忽然覺得肩膀上一熱。是光的手搭在他肩上輕輕按了一下。
「塔矢⋯⋯」
熟悉的溫度讓他很想回頭確認光的表情,可心裡仍有些芥蒂。
——自己現在對進藤抱有的感情是車禍前記憶的遺物?還是當下實際的感受?
已經分不清這兩者,感到虛幻,又有些空洞。
而且,聽見他的聲音,又想起今天搪塞自己的樣子。
這些言辭和他在過去的某些時刻真正想從光口中聽到的愛語交織在一起,越發顯得矛盾。
其實比起無望的戀慕,更不想面對的是,光的回應和體恤帶著憐憫性的欺騙,這樣極有可能的現實吧?
診室外適時地傳來久違的腳步聲,恰好打碎他的疑慮。
亮看了眼明子,回望診室的門。
把手被轉動,門開了。
塔矢行洋穿著西裝站在門口。
是記憶裡三個月沒有見面的、今晚為了給自己慶祝生日而連夜返家的父親。
而這張臉明顯比印象中蒼老了很多。
和身邊所有人一樣,為了還原「生日」這天的事件,他每天白天都要離開家,還在晚上帶著行李裝作剛剛歸來——
「——爸爸!」
亮這才放任自己離開座位,衝進了那個堅實的懷抱。
等回到塔矢邸的時候,太陽已經落下,零散的星星在街燈的空隙裡閃爍。
光跟著走入院內,來到和居的門口。
「你到家了,我也該回去。」他輕聲說,「那我們按照原樣,明天『再見』?」
「嗯,明天見吧。」
光回頭,準備去和塔矢夫婦與緒方先生告別。
「等一下,進藤!」亮卻在他走出幾步後叫住了他,語氣有些急切,「你今天本來說,想帶我去一個地方的,那是哪裡?」
那是⋯⋯爺爺家的倉庫。
原本打算坐河合先生的計程車過去的,帶他去閣樓上看看那個棋盤,以便更自然地托出佐為的事,和自己的心意。
但現在演變成這樣,又面對著塔矢老師、明子夫人和緒方先生——
「已經不重要了。」光搖了搖頭。又補充道:「你沒事就好。」
「那⋯⋯我有話要對你說。還有,想要你為我做的事。」
亮抬起眼。
光意識到這是今天下午真相被撞破之後,他們第一次視線相對。
亮的眼睛紅紅的。
也許是適才和行洋在車上的談話讓他哭過?
「⋯⋯明天,跟我講講你最近下的、最新的棋吧?不要讓我們的時間只停留在過去。」
可亮此時望向他的目光就像一片星空,其中看不見半點頹喪。而他是中心的、唯一的月亮。
「無論透過何種方法,能夠看到你的圍棋的成長,我一定會很高興的——」
看著這樣的亮,光一時不解地睜大了眼。
分明才知道這個病不會痊癒,知曉「明天」可能是永遠不會到來的遙遠的概念了。
可明白了這一切的塔矢,他仍然⋯⋯
面前的人低下頭,耳尖被髮絲蓋住。
「還有生日禮物的事。可以是一束桔梗嗎?」
視線落在他衛衣胸前的藍紫色徽章。
「我很喜歡桔梗花。它會讓我想起你。」
站在屋前,和亮的目光交匯,一如過去來這裡作客時的任何一個離別。
「⋯⋯我知道了。」
這樣的熟悉感像一根木刺扎在心臟裡,讓每下心跳都更痛。
「那麼,晚安。」
「晚安。」
回身,那個身影消失在溫暖的燈光中。
雨後的夜晚無風,濕冷的空氣鑽進皮膚底下。
「進藤君,」塔矢行洋本來和緒方一起立在院門邊談論著什麼,見他走近,便邀請他道,「有空的話,一起來喝一杯吧。」
—————
這個時間來居酒屋消費的大多是上班族,四周瀰漫著微甜的酒味和杯盤相碰的聲響,炙烤肉類的白煙在日光燈周圍暈開一圈。
對這樣的邀請稍微有些意外。
第一次和塔矢行洋見面,是在棋院三樓,沒開燈的走廊裡。一點也不愉快的記憶,先是把佐為對自己說的話講出聲來,被當眾帶走唸了一頓,出門時和佐為拌嘴沒想起看路,還撞上了名人。
那時絕對不會想到能像現在這樣坐在一起,面前一紮朝日啤酒配一碟毛豆,談笑聲和招呼聲在四周此起彼伏。
「緒方君,你也很久沒有來過這裡了。」
點過菜後,行洋挑起話頭。
「上次一起來,還是在老師去中國前吧。」
「嗯。」
啤酒泡在杯口湧動、破碎,廚房傳來炸物下鍋的聲音。
「剛搬到這邊的時候,這間店也才開業不久,沒什麼人。第一次帶你來,你可還沒到喝酒的年紀。」
緒方夾著毛豆的筷子頓了一下,「哈,您說蘋果醋的那次。」
「當時也是冬天,記得是為了慶祝你拿到新人王?」
「對。」想起往事,緒方笑笑,抬手鬆了鬆領帶結,「可小亮拿下平成十五年[2]那屆新人王的時候您只帶他去吃了必勝客的披薩?」
「那是小亮自己提議的。」行洋低頭轉了轉酒杯,笑著看了光一眼,「他說那不是什麼太大的事。」
「哈哈哈,畢竟年代不同了。」
一群大學生模樣的人浩浩蕩蕩地進來,門口的鈴鐺熱烈地響起。
店員上菜的時候,緒方接過他手中的開瓶器,新斟了一瓶啤酒。
「說來,進藤,你沒有參加過新人王戰?」
「啊,是。」
「現在再想也沒機會咯。」杯口厚厚的泡沫一點點沈下去,「第一個拿到的頭銜就是05年的應氏盃[3]?和亮一樣,很喜歡直奔主題啊。」
「嘛⋯⋯算是吧?」面對緒方的調侃,光拿著玻璃杯,杯裡的酒還剩一半多。
行洋這時也跟著點了點頭。
「呵呵,你們都算趕上了好時候。」
緒方轉過去給他的杯子添滿。
「老師出道的時候還幾乎沒有為新人設立的棋戰?」
「是這樣,那時的低段者確實很難有這樣的機會,不過日本圍棋已經改變了很多,現在的東京本院還是七十年代才建成的呢[4]。」
「那您可以說是白手起家了。第一個榮譽就是名人。」
「啊啊⋯⋯」行洋應了一聲,視線越過光背後,「好像就從那時開始,習慣了常年不著家的生活。」他抿了一口酒,「塔矢家以前的確沒有下棋的人。我是有一次去京都出差,在鹿苑寺結識了教我圍棋的住持。也算機緣巧合。」
原來是從塔矢老師這一輩才開始接觸圍棋啊。
僅僅看著現在的亮,在市區鬧中取靜的古老和居長大,一絲不苟地承襲五冠王的父親的事業,不久前剛成為史上最年輕的名人,完全像是從圍棋的世家出身。
塔矢門下也是,比起其他的圍棋研討會和團體,更多了一種成員間親近的聯繫,是很傳統的宗門,總給人這樣的感覺。
差點要以為他們家的頭銜都是世襲的。
「不過,剛入段的時候是真的只會下棋,還不太懂圍棋界的事,面對大人物和記者也會緊張,多虧很多前輩和同期朋友的照顧。」行洋夾了一莢毛豆,笑道,「日程經常排得很滿,明子她⋯⋯也有段時間忙著關照在美國的親人。就是緒方君住在家裡學棋的那幾年吧?
「你陪著小亮哄他睡覺的次數大概比我們做父母的都多。」
「哈哈哈,每天要給還在牙牙學語的亮講棋,這也是很有趣的挑戰啊。」
光還從沒見過這兩個男人輕鬆地談論往事,放聲大笑的樣子。隔了兩張桌子,剛落座的學生們也爆發出誇張的笑聲,笑得發抖的手端著搖搖欲墜的酒杯相碰。空氣裡灰白的煙霧繞著他們飄到天花板,模糊了那些笑臉和牆上時鐘的盤面。
「小亮⋯⋯也和別的孩子不一樣,可能就是因為這個,他不太在意時節和團聚。」
這倒是沒錯,光依稀記起四年前那個氤氳著白霧的冬夜——
塔矢真的是,只要有棋,有人陪他下棋,就會很開心。
執拗、倔強、骨子裡要強,又任性,看起來不近人情,其實很簡單通透。
手在桌下握緊。
真是,已經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才好⋯⋯
「——但塔矢門下如今的前景,是您親自建立起來的。」
聽緒方這麼說,行洋又笑,輕輕地搖頭。
「都過去了啊。你們能有現在的成就,我也已經很滿足。」
喝了一口,忽然問道:「說來,進藤君也是出於自己的興趣,才開始學圍棋的?」
眼前掠過和佐為的相遇、最初的對局,和在兒童圍棋大賽所目睹的場景。
「啊啊⋯⋯是從十二歲的冬天開始的吧。」
那時,在佐為的身影之下,看著尚無法完全理解的棋局,單純地想要讓亮臉上無比動容的表情能和自己有關。
他輕輕放下杯子,把杯墊擺正。
「只是看見別的孩子都那麼認真,就會想要自己下。」
兒時的自己被塔矢名人下棋的動作和神情所震撼,似懂非懂地模仿他的手形,彷彿看到了未來的影子。亮身上也有著類似的鋒銳氣勢。
而如今,面前的男人似乎顯得更加從容而和藹,或許是一直在周遊各地探索新的圍棋的緣故,這樣的生活也稍微改變了他。
「時間過得真快啊。」行洋低聲歎道。「本因坊之後,你有什麼打算嗎?」
「之後,嗎⋯⋯其實覺得現在的我,還沒完全找到屬於自己的棋,距離我所知的最高的境界也尚有很長的路。」
扇子就放在椅背上的外套裡,向後靠的時候會微微硌著。
「獲得本因坊只是完成了一項執念,是一個開始。」說著抬起頭,「至於眼下的目標,就是先守住這個頭銜了。」
緒方拿起啤酒瓶給行洋斟滿,剩餘的倒進面前的酒杯。光也拿過桌角的開瓶器為自己打開今晚的第三瓶朝日。店員胳膊下面夾著托盤匆匆走過,順便單手收了桌上的空瓶。
「進藤。」行洋沉吟片刻,突然望著他,「你如果去到更高的位置,會對現在這樣週而復始的生活感到乏味吧。」
光幾乎覺得他在微笑。
緒方愣了下,看了他們一眼,隨後若無其事地吃著手裡的燒鳥串。
「⋯⋯其實關於這點,在參與進來的那一刻,就已經有這樣的覺悟了。」
對於亮的意外,不僅僅是自己,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無法承受長時間的循環。也正是因此,必須讓亮也擁有真正的明天。除此之外已經別無他法。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放棄。」
哈⋯⋯這麼想來,好像每次瀕臨絕望的時候,都會先從亮那裡,聽到充滿希望的話。
「喔?」緒方放下簽子拿起酒杯,未等行洋回話,就先側著頭問他,「對以後的事,你就這麼有信心。」
與其說「有信心」,不如說是「不思悔改」。
光微笑,將筷子擱在瓷架上,又轉而靠上椅背做出思考的樣子。
「⋯⋯其實,塔矢的棋也不是每天都相同,也許下棋的『直感』不屬於需要被『記住』的東西。至少我每次都要全力以赴。」
金色的酒液裡浮出模糊的倒影。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仍會是對手。」
—————
淺酌結束,邁出店門。等道別的時候,月亮已經昇至東京上空,白光朦朧地溶在雲層裡。
緒方看著光遠去的背影,最終停住了準備拿菸盒的手。腳下的石板路還有些潮濕,映出兩側店鋪的燈火。
明天重新開始。
自行車的燈光從眼角閃過,水花落在腳邊。
也許可以對進藤做出的改變稍加放任,至少從亮會有的反應來看,這遠算不上一件壞事。
真是堅強啊。
被仔細看護起來的日子也好,得知真相的今日也罷。
「——有樂町!」
「高田馬場。」
「目黑!」
轉彎的時候,兩三個拎著酒瓶的醉鬼冒出來,報著山手線的站名從身邊搖搖晃晃過去。有個人還把紅色的領帶綁到了頭上,揮舞的手臂差點打到他[5]。
「啊哈哈哈哈獃子,說了日暮里,當然還、嗝、還有西日暮里啊!」
「又是你輸了!快喝吧。」
「可惡啊!才來東京半年,我哪、記得住這麼多——噸噸噸⋯⋯」
商店街外面明亮如白晝,車聲抹掉了買醉的上班族們的聲音。燈箱裡的海報和花裡胡哨的霓虹燈交錯著滾動。
像今天這樣的情況說不定今後還會往復,成為「支線」裡獨特的一環。
要時常叨擾的話,或許該抽空去和醫院的人打聲招呼才對?
胸口有點悶⋯⋯
紅燈。人還真是多啊,這都幾點了。
緒方覺得自己開始討厭起紅色來。
碰撞時翻滾暈眩的鮮紅,碎成片狀沒能救起的脆弱的唐紅,和煩擾散亂不成人形的豔紅都是⋯⋯
嘛,不能再想了,這兩個人的事。
要忘掉這一切曾發生過才行。
深色的汽車停在跟前,有個小男孩抱著一隻大金毛,坐在車裡看他們一群成年男子黑壓壓地過馬路。
嗯?這麼想來,好像也該把車開去加油了。
要不明天再順路去買一對新的孔雀魚來養吧。
適當地順應時節來做出改變。應當也不是什麼壞事。
留下魚缸的冷色燈光,這麼想著,躺倒在床上。
然而緒方沒想到的是,進藤從第二天開始就沒來棋院了。
他失蹤了整整半個月。
tbc.
[1] 西曆二〇〇八年。
[2] 西曆二〇〇三年。
[3] 二〇〇八年時,新人王戰的參賽資格為年齡二十五歲以下,棋力七段以下。光於二〇〇五年拿到了應氏盃的國際賽冠軍,按照當時的升段制度直升了九段,這之後便無法再參加新人王戰。
[4] 原作各場館中出場率最高的位於千代田區五番町市ヶ谷站的日本棋院會館是1971年建成的。
[5] 是第一章出現的那個不謹慎上班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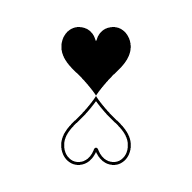
總覺得白河夜船里的光和亮,在心裡都是很有勇氣,也很堅定的。每一天都會失去記憶的話,就好像每一天都會死去,困在朝生暮死的循環里無法逃脫。但是,如果和光約好了未來,是不是就是確信他會在明天等着自己呢。所以他會說出:“不要讓我們的時間停留在過去”的願望。一直很喜歡二位之間的那種“等待”,在職業的世界裡等待着光的亮,等待着光把sai的秘密告訴自己的亮,和在白河夜船里,一直在“明天”等待着亮的光。
對我來說,白河夜船里的光就好像黑暗中的希望一樣,總覺得只要他還在等待着亮,總會在這個循環之中找到希望。只要那個關於明天的約定還在,所以即使今天就會死去,也沒有關係……會不禁有這樣的想法呢。
說起來,光的每次告白都會被打斷啊……而且12月14日的那天,沒有被記住,所以亮的記憶里最後的一次留在了棋院的資料室TT
哈哈越智溺水這件事讓我忍不住笑出聲來,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