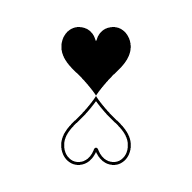Notes
⚠️用下半身写的。
⚠️各种预警(有点说不上来那些专业名词(挠头。
⚠️未成年请务必不要观看。
眼前是一片純白色。對進藤光來說再熟悉不過的顏色之一。
棋盤上的一隅、病房、喪事,親近卻沒有任何重量的衣袂。
不,不對。
輕飄飄像一層霧氣一樣蓋在臉上,可是那確實存在。鼻尖上頂著羽毛一樣瘙癢,伸手去抓,卻摸到了一個很實在的頗有體積的東西,好像還是有點熟悉的形狀⋯⋯
「啊!」
有硬物掉在地上的聲音,隨後左側的重量消失,自己似乎正是躺著的姿勢,指尖反手劃到乾燥的床單。
身邊的人好像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又重新支著床沿靠近,有柔軟的髮絲垂下來,帶著熟悉的香波氣味。
「還沒有醒嗎?手就這麼不安分,真是的。所以説這種事就是不行的吧⋯⋯」
「嗯⋯⋯亮。」抓住這個聲音的主人的手,「已經醒了。嘶,頭好痛⋯⋯不是晚上嗎,為什麼燈要開這麼亮的⋯⋯呃,所以這裡是⋯⋯欸欸欸欸欸塔矢?!!」
「幹什麼?」修長的五指從自己掌心中不留情面地收回,看見亮退後一步,抱起雙臂站在床前,一雙秀氣的眉毛顰起,似乎有些不耐,被他自上而下地睥睨,心中大感不妙,但比起這個⋯⋯
「——你你你,這是什麼打扮!!」
光知道自己的臉現在紅到不行,因為睜眼看到的是身著一席婚紗的戀人——織繡蕾絲邊的領花襯托著形狀好看的鎖骨,層疊的襯裙拖尾勾勒出腰臀的線條⋯⋯與華美繁複的裙擺形成對比的是上身輕薄的鏤空,一道曲線狀的深V從胸口開到腰腹,只有胸前的紅暈被白薔薇刺繡的布料若隱若現地遮蓋,餘下部分的白紗則會透出膚色,一直連接到下半身的三角區,順著腹股溝的陰影藏匿進襯裙堆疊的褶皺裡⋯⋯
「所以說,你失憶了嗎?今天是我們婚禮的日子啊!」
白色的長手套在胸前抱緊,好像使得乳肉中間的溝壑被擠壓得更深了點⋯⋯
「什什什什麼婚、婚禮?!!今天是我⋯⋯塔矢⋯⋯啊噗——」
感到身體裡有兩股熱流直衝下腹和頭頂,看著這樣的亮,發現自己毫無疑問地起了反應,同時看見胸口的純白布料瞬間沾上幾滴鮮紅。
「——欸,進藤?!沒事吧?」亮的聲音從嚴厲轉為慌張,趕緊從桌上同樣裝飾有白色蕾絲和刺繡薔薇的紙巾盒裡抽出兩張遞過來,「所以你、真的不記得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昨天剛結束頭銜戰的第三場,成田機場回來的路上⋯⋯塞車⋯⋯你也有棋賽,可還是等我到很晚,熱了晚飯吃、一起洗了澡⋯⋯但什麼都沒來得及做啊,都太累了就是。才搬到一起住,想做的話也隨時都⋯⋯已經是這樣穩定的關係了,不過離結婚還⋯⋯欸,等等,塔矢,先提醒我下今年是哪年?」
「令和5年,二◯二三。」亮的眼神轉變為擔憂,「我說進藤,你該不會是、喝酒喝傻了?我就說緒方先生今天有點過分⋯⋯」
「記憶喪失⋯⋯嗎。」令和又是個什麼年號?
「但今天一整天都在婚禮現場的,這你總該想起來了吧?本來說好作為職業棋手的婚禮,要用一局娛樂性質的表演賽作為開場白,結果你太緊張,第一手直接把棋子拍到格子裡⋯⋯雖然娛樂性質是得到了體現;交換戒指的時候你握著我的手一直在抖,好幾次戴不進去;最後說祝詞還因為『十五年的地下戀情實在是太久了』這句哭得很厲害⋯⋯」
「喂喂怎麼我幹的淨是些糗事啊?」光看了看亮,觸及身體時又心虛地移開視線,「而且你⋯⋯穿成這樣和我下棋?」真是能想到最惡劣的盤外戰了⋯⋯
「之前又不是沒見過這身,而且你下棋的時候不是可以很⋯⋯不為所動嘛。」
「——那前提是我從一開始就有進入專注的狀態啦!!」
「不管怎樣,重要的是我們終於,在大家的祝福下結婚了⋯⋯」
亮笑起來,撿起落在地上的手機,重新跪坐到床邊,湊上前在光的額頭上親了一口。
「今天的你,穿婚服也很好看⋯⋯」得到亮的誇讚,剛想低頭去看一眼自己穿了什麼,又聽他說:
「——今後也請多指教,我法律上的丈夫。」
腦筋一抽,面對突如其來無法理清的困惑,進藤光忽然覺得思考的優先級需要調整一下。
「已經很晚了,還說要你陪我的話可能會有點任性⋯⋯」臉上浮現出羞赧的神色,亮不自覺地伸手去把玩胸前墜著的那顆鴿子蛋,「但還是希望能把儀式給⋯⋯哇啊!」
話還沒說完,整個人就被推倒在柔軟的枕間,身周騰起清雅的白薔薇熏香。
「剛才我睡著的時候,就一直在看這個?」光的視線落在亮打開的白色翻蓋手機的檢索頁面上。
「『新婚之夜的H』、『對丈夫才能做的晨起的侍奉』、『建議婚後再實踐的接吻方法』——這些是要臨時看了才明白怎麼做的東西嗎?」耳邊同時響起光充滿慾念的低吟,「還有你剛才說的,儀式?」
「就是⋯⋯」心跳聲變得劇烈,看見身前的人目光在白絲襪和同色的吊襪帶處流連,感到光正隔著白手套和襯裙的布料撫摸自己的腰胯,可那下面是⋯⋯
「只是一起做一下、和平時一樣的事,但有一點⋯⋯嗯啊⋯⋯!」
「へぇ、這是什麼?」被折磨了一天的地方忽地落入光的手中,看見他的眼裡閃過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