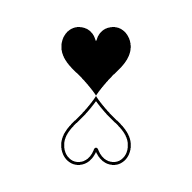告白(こくはく)
「喂喂,進藤,馬上到你的成人日了,雖然沒有提前慶祝,但放心啦,酒都備好了,儀式結束之後叫上伊角他們絕對要找你喝個爽!說起來,週一你準備穿什麼啊,和別人一樣租一套羽織袴嗎?老實說我去年太高興了,畢竟人生就一次成人式嘛,下血本給自己買了第一套和服,這不是就穿了一次,而且咱們倆的身形差不多,借給你小子也不是不行。」
「和谷,你不說我都把成人日給忘了!那就——」
「你这傢伙真是什麼都能忘哦?虧得我還想著把衣服借給你。」
「呀呀,這不是去年跟你們玩得太高興,好像自己也過了成人式一樣嘛!謝謝你想著我,不過說實話,和服這種麻煩的東西我還是穿不來,老老實實穿西裝就得了。」
「害,挺像你嘛,成人日穿西服什麼的。不過你這小子也真是沒品,日本男兒就要穿羽織袴才像個樣子!那說好了,到時候過來一起喝酒哦?記得多叫上點人來!」
「嗯,好像有棋院的人也是要一起參加今年成人式,我再叫上明明。到時見了!」
千代田區這一年的成人儀式選址在皇居外苑。 進藤光到得很早,一方面是因為成人之日而興奮,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夠等待塔矢亮到來,卻沒想到要等的人已經在那裡了。雖然早就知道塔矢穿和服好看,也見過不少次,但他還是忍不住停下了腳步。
櫻花樹還未長出葉芽,只有松柏常綠,映襯著湛藍的晴空。桜田門前聚集了不少來參加成人式的年輕人,女孩子們穿著各式繽紛的振袖,少年們的服飾點襯在其中就顯得深沈了許多;他們大多是成群結伴來的,熱切地談論彼此的服裝、將會看到的表演、儀式結束後的安排,高高地舉起相機和身邊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合影。
塔矢亮站在右側的兩株柳樹之間。不同於元日時樸素典雅的單色套裝,他今天所著的紋付羽織上半是純淨的月白色,順滑的青絲垂落至背脊中央,而下半延伸出的一片墨色恰好在髮梢處暈染開,銀線混織羽二重像蕩漾的湖水反射著陽光;胸前背後共三處金色的矢絣紋樣,袖邊和衣襬以京友禪風格繪有古雅柔和的松竹梅圖案;內搭是茜色小袖和乳白色襦袢,腰間繫一條菱紋鼠灰色角帶,其下是黒銀縱紋縞袴,白色足袋和下馱。
他正與面前幾個穿著鮮豔振袖的女孩說話,其中一人拿著相機,好像想要與他合影,旁邊的幾個女孩子見狀也拿出手機。
「請問您是一個人來的嗎?」
「您也是學生嗎?是哪個學校的?明治?理科大?」
「如果不介意的話,儀式結束之後要不要和我們去迪士尼?」
「可以交換一下電郵地址嗎?」
「喂——塔矢。」
有些招架不住接二連三的熱情問話,突然聽到熟悉的呼喚,塔矢亮回過頭。
父母過完年假就啟程回上海了,此後又恢復了每天用郵件交流的習慣。日前,母親曾在信中提道:「小亮,成人禮當天記得穿媽媽準備好的衣服哦,就放在更衣室整理和服的櫃子第一層。可能會有點華麗吧,但一生一次難得的日子,年輕人果然還是要穿明快些的顏色才好,像進藤君那樣。」
本以為進藤光如平日裡一樣會穿得很顯眼,又想到可能要一起合影,難得的日子不想與他格格不入,也就遵從了母親的安排,結果這個人今天卻是一身簡潔的深灰色西裝、黑色馬甲配黑色樂福鞋,黑白豎紋襯衫的扣子一反常態地好好繫著,絳色領帶與口袋裡的方巾和手中的扇子相得益彰。
「你是不是記錯集合地點了呀?」進藤光從背後搭上塔矢亮的肩膀,「已經改到另一個門了,快跟我來。」
「欸?啊,好⋯⋯」
原本在他肩上的手滑落到小臂,最後牢牢握在腕上。就這樣被進藤光抓著穿過人群,快要走到坂下門時才終於停下來;這裡離電車站稍遠,算不上清淨,但人總是少了一些。
在皇居前廣場對面的路邊站定,塔矢亮才說:「剛才,謝謝了。」
光沒有接話,反是指著走來的方向,眼睛一瞬不瞬地看著他問:「剛才那是被棋迷認出來了嗎?裏三層外三層的。」
「⋯⋯應該不是吧,只是想要聊天合影的學生而已。」
停頓了一下,才聽到對方回答:「你還真是招女孩子喜歡啊。」
進藤光說出這句話時的表情和平時開玩笑並不一樣,他扭過頭,微微皺著眉,眼神飄到了身旁大片黃綠的草坪上,明明那上面什麼都沒有;他雙手插在西裝褲口袋裡,使得外套的下擺皺起來,衣襟敞開露出薄綢緞條紋裏子和馬甲平滑服貼的腰線。
塔矢亮也順勢望向那片剛剛長出新芽的草地,低下頭藏住了心裏的情緒。背後的長髮從肩頭滑落,露出一小截白皙的後頸。心下有些不愍:進藤光看起來不太開心,是因為自己嗎?可是自己做錯了什麼嗎?又是突如其來的氣氛變化,這個人總是會在奇怪的時候變得深沈、嚴肅甚至陰鬱,就像他詭譎的棋路一樣,對局時總在微妙的地方出現的關鍵手;他的一切都讓人捉摸不透。想到這,塔矢亮心裡昇起一種莫名的失落與無力。
他們誰也沒有提出回到桜田門。身後不時傳來路過的年輕男女激動的談話聲、平絹與綢緞摩擦的聲音、木屐踏在柏油路上微弱的響聲,而清晰的只有身邊的人的呼吸、遠處的水流和擦身而過的微風。
原本以為在室外可以不必正坐,卻不曾想到宫内庁的工作人員十分貼心地現場分發了坐墊。今年參加區成人式的男生不多,大家都坐在一起,幾個人相互小聲地抱怨。進藤光下棋的時候不超過一刻鐘就會改成盤腿坐,從院生時代開始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多少長進,倒不是他不可以堅持更久,只是若正坐著,一旦開始專注於棋局就會忘記坐姿的事情,結果就是一局終了半天站不起來。而現在沒有圍棋讓他轉移注意力,市長在專門搭建的台上致詞,剛說到慷慨激昂處,他的脚已經開始隱隱發麻了。其他人看起來也不好過,在墊子上動來動去,有些甚至已經盤起腿,繃著臉偷偷揉著變麻的地方。
不用看也知道塔矢亮一定還一動不動;這個人的正式棋賽他看過無數次——不論對局進行多久,都如同一幅畫像一樣端坐著。此時,長髮貼著羽織從他挺直的脊背下垂,衣襬在身後折起,他雙手交疊放在大腿上,眼睛平視著前方。微風吹過,衣袖輕輕鼓動了幾下,一縷長髮從耳後滑到胸前。
觀看射禮的時候,大部分人都已經放棄了正坐。身為職業棋士,進藤光自認為還可以堅持一段時間,卻沒有想到表演長得很,他百無聊賴地開始東張西望,看到遠遠地從桜田門的方向走過來幾個熟悉的身影。進藤光定神望了望:和谷走在前面,身後跟著伊角和奈瀨。他本來跟和谷在電話裡說想要約明明,但她和三谷也是今年成年,兩人就讀的學校會組織一起在澀谷區參加儀式,而晚上還要和她的同學朋友們慶祝,所以只好等下次再聚。與藤崎明的通話結束後,他想起了曾經圍棋社認識的朋友們——筒井學長上高中之後就很忙了,之前找他出來玩的時候也因為課業繁重而推辭;加賀在那次聯賽之後就專心於將棋,後來似乎去幫忙家裡的生意了;金子成績一直很好,中考之後不經常聯繫,但後來得知她考上了御茶水女子大學,正在攻讀心理學……而最終只有他留在了圍棋的世界裡。曾經也想過將來成人之日要聚在一起相互祝福,但這麼多年過去,他不得不承認,作為職業棋士的自己和走上各自道路的大家,在心境上或許已經完全不同了。
「怎麼樣啊,成年的感覺?」儀式終於結束之後,和谷拍著進藤光的肩膀問道。
「你小子,剛剛看著我那麼辛苦還在那邊笑,可給我等著!」
和谷和進藤光不知輕重地打鬧著,他看見進藤身後跟著走來一個衣著鮮亮的人,想著這大概就是他說起的棋院的同齡人,卻不曾想到——
「塔矢⋯⋯亮?!」
「——是?」塔矢亮聞言瞪大眼睛一臉疑惑地看著和谷。
天下紅雨了?塔矢亮居然會參加棋院組織的集體活動——而且這個人也有穿成這樣的時候嘛!和谷心道。仔細打量之下,只覺得如此華麗的和服刺痛了他貧窮的雙眼。但——既然「其他人」只有塔矢,為什麼當時在電話裡不能直接講出來?不是說他和塔矢亮有多熟,這個名字在圍棋界還有誰不認識嗎?尤其是進藤和塔矢看起來是私交甚篤的樣子⋯⋯雖然早就不再像院生時期那樣無理取鬧地討厭這個人,但還是不明白進藤如何和他相處得這麼好,從進藤剛到棋院的時候說一些塔矢為了他做過多少事情、視他為勁敵之類的話,到後來他們兩個在比賽上互相只關注彼此的樣子,甚至和自己聊天的時候都常常說起塔矢亮,可自己還是對他知之甚少,明裏暗裏總覺得這個人跟他們不是一個世界的。而且,知道這兩人秉性的,任誰都會驚訝他們之間頻繁的往來吧,實在太奇怪了!連帶著有時會感到進藤都不是自己認識的那個人了⋯⋯
伊角慎一郎察覺到氣氛的變化,不動聲色地向前挪了一點,說道:「塔矢君也一起來慶祝吧?」
塔矢亮愣了一下;進藤並沒有向他知會過之後的安排。「不了,我——」
「當然咯!」進藤光搶過他的話,「我跟和谷講電話的時候不是說過棋院還有其他人要來嘛。」
和谷和伊角相互看了一眼。
「吶,這樣的話,」奈瀨明日美突然說,「難得一生只有一次的紀念日,你們也有好好打扮,不如一起來拍張照吧。」說著從包裡拿出了拍立得。
二人被推搡著走到最近的櫻花樹下。乍暖還寒的日子裡,樹上都是光禿禿的,剛冒頭的葉芽在周圍常綠松柏的映襯下,倒也是別樣的風景。進藤光看了看身邊的人——和谷以前對塔矢有過一些微妙的抵觸情緒,剛剛似乎也對於他的出現感到詫異,而自己明明聽見了他的拒絕,還是硬要把他拉過來,也沒問過他的意見;在成人之日這樣的時間點,嘴上說著一起「慶祝」,其實只是自己一心想要把他帶在身邊吧,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要告訴他⋯⋯
「來,說『茄子』——」
回過神來,聽見按下快門的聲音,進藤光搶先一步跑過去看拍出來的照片。等待顯像的十幾秒時間顯得格外漫長。
「啊,不行,我都沒在看鏡頭!」他接過照片說,「再拍一張吧,這張我拿就好了。」
照片裡,塔矢亮的笑容如同早春的第一瓣櫻花,與平時不同的柔美氣質搭配這身裝扮像是上巳節的雛人形;而自己在一旁深情地望著他,臉上的神色是自己都從未見過的樣子。
要去的居酒屋在銀座後面的築地市場,離皇居外苑不遠。他們走在路上的時候,進藤光一直拿著那張正方形的小照片翻來覆去地看;塔矢亮見狀也瞧了瞧自己的那張——照片上兩個年輕人長身玉立,面對鏡頭微笑著;進藤一身筆挺的西服,右手執扇,與自己的羽織竟也意外地相配,不得不承認是很帥,可也不至於看這麼久吧?他有這麼自戀的嗎?而和谷他們似乎習慣了他做各種奇怪的事情,神色自若地彼此聊著天。彷彿又是只有自己被排除在他的朋友圈外——剛才聽和谷話裡的意思,進藤光好像告訴了他「棋院還有其他人」,只是說了「其他人」而沒有提到他「塔矢亮」,也沒有提前通知自己儀式結束之後要一起慶祝,那又為什麼現在硬是拉著自己來?這麼沒頭沒尾的,是覺得同為棋院的人,在大家面前不邀請自己過意不去而臨時起意?明明不需要這樣的,不需要顧及他的感受⋯⋯人不會為失去不曾得到的東西而煩惱,不是嗎?思及此,長出了一口氣。揮去腦海裏無來由的煩悶,塔矢亮這才留意到周圍景色的變化。
不知不覺間來到了目的地所在的街區,他不曉得東京都心三區還有這樣的地方——又高又長的大棚房,停在巨大廣場上的卡車,戴著圍裙、頭巾、手套在各處忙碌的人們;沿路小店售賣各式各樣奇特的食物,店面可以有桌椅,也可以僅僅是一個招牌、一間廚房和一個櫃臺,客人們圍在旁邊,用手端著吃得津津有味。廚房朝向街道,砧板上有鮮活的掙扎跳動的海產、帶著血的肉,這番景象看得他神色一凜——自己通常很少關注食物的來源。
記得有一次進藤光來家裡下棋到很晚,便決定留宿,於是他拿出冰箱裡的鯛魚刺身加上紫蘇葉、紅姜和明蝦天婦羅做了蓋飯。吃了一口之後,進藤光突然問起這個魚是從哪裡買的。
「這不是你家附近超市裡鯛魚的味道。」
他於是隨口答道:「好像是前幾天藤澤紀基九段來訪時帶的伴手禮。」
而進藤似乎意外地非常關心這些事情。他突然開始講將真鯛做成刺身的「活締法」,要先從什麼地方扎魚腦、破壞掉腮、切斷魚尾放血、再插入金屬絲捅穿整個脊柱,這樣才能讓魚肉吃起來像活的一樣——自己當時想必是聽得臉色慘白,他便撓撓頭尷尬地笑了笑:「看來日本人對魚的同理心是很差勁啊。」
真是不明白這個人怎麼會把這種事記得如此清楚。
進藤光意識到塔矢亮一路上相當安靜。他們沒有走進海鮮市場的棚內,那裡盡是海水和魚蝦的鹹味,地面都像船上的甲板一樣潮濕;即使這樣,路上依然充滿著伙計的吆喝聲、人們的談笑聲和街邊各種小吃混合在一起的氣味。塔矢一定沒有來過這種地方吧——於是他轉頭看了一眼身邊。
這身鮮亮的衣著在灰色的街區顯得尤為扎眼,又有衣服主人的氣質容貌加持,不時引人側目,但塔矢亮似乎不是很在意。他的眼神在街道左右的店面之間來回跳躍,又要分出心思來看路,於是走得時慢時快,甚至手提著巾著一直懸在衣襟前面都不自知。進藤光看著眼前人的可愛舉動,不由地出神,忽然想起了之前帶他去吃拉麵的場景。
那次是去他熟悉的名為『道玄坂』的拉麵店。經歷了上次的N記漢堡之後,他也不問塔矢有沒有吃過拉麵了,確認沒有絕對不吃的東西之後,直接幫他點了和自己一樣的一碗。拉麵店熬煮骨湯的肉味很大,塔矢明顯不是很習慣,看著面前灑滿香蔥的一大碗麵也有些猶豫,像是不知從何下口。
「喂,老闆娘,有沒有多餘的頭繩麻煩借一下?」
聞言塔矢亮愣了愣,接過來的時候輕輕地說「謝謝」。
把頭髮束起來確實讓他更能夠接受這種需要低下頭吃一大碗的食物,但在進藤光已經把湯都喝完了的時候,塔矢亮才吃了一半。他看了一眼對面人的空碗,一言不發地把剩下的一半面吃完。
「不想喝湯的話也沒關係啊。」看著塔矢面對眼前的濃湯微微皺眉,湯面上漂著一層上好的背脂。
結果因為自己的這一句話,塔矢亮把那碗湯也喝得見了底。
真是拿這個人一點辦法也沒有。
名为「海坊主」的居酒屋在這個時間正逐漸熱鬧起來;和谷與老闆似乎很熟,提前包下了二樓的鶴之間,寒暄幾句之後帶著他們上去。
「喔,越智,阿福,本田!」和谷把背包裡和手裡提著的一大堆酒全都放在了和室的矮桌上,對先到的三人打了招呼。越智和福井還是未成年,只好在一群喝酒的「大人」中間喝果汁和汽水。
「你帶得也太多了啊,和谷!」奈瀨一邊把亂七八糟的酒瓶擺整齊一邊抱怨著,「還讓我們提了一路。」
「哎呀,不帶多一點怎麼把他們灌醉嘛!」
「呵,話不要說得太早,誰灌醉誰還不一定。」
越智說罷,瞥見跟在進藤光身後的人,推了推眼鏡,看了和谷一眼。
儘管今天是兩個人的成人禮,但主角似乎只是進藤光而已,他熟絡地與眾人寒暄著,有來有回,不一會氣氛就被炒得很熱烈。大家吃烤海鮮自助的時候,塔矢亮給自己單獨點了一份散壽司。進藤光看著他行為拘謹,不時用好奇的眼神觀察他們,還要執意做出認真吃自己碗裡的飯的樣子,一邊覺得可愛,一邊莫名地感到難受。
白晝依然很短,天色漸暗的時候,成年人們已經差不多喝得七葷八素了。本田和伊角一起坐在榻榻米上手舞足蹈地聊天,奈瀨還算清醒,和福井在陽台上喝起了汽水;塔矢亮半睜著眼一言不發地小口喝著至少第五瓶宇治茶梅酒,進藤光自己也感覺輕飄飄的,有些擔心地看著他——雖然說成年這一天就是應該喝到盡興,但以塔矢的性格,放任自己喝乾四瓶梅子酒還是讓人驚訝⋯⋯不過偶尔一次也沒有關係吧。
进藤這傢伙,从刚才开始就不時地偷看塔矢亮——看著坐在正中從頭到尾像年糕一樣黏在一起,又沒怎麼講話,氣氛詭異的兩人,和谷眼皮一跳,忿忿然拎著一瓶新的久保田挪到越智旁邊,而越智在看自己昨晚在一柳棋聖的研究会下的棋譜。
「吶——」和谷擰開酒瓶蓋子丟到地上,「你有沒有覺得,那兩個人莫名其妙的。」
越智推了推眼鏡,並沒有回答。確實是很莫名其妙呢,從進藤光帶著塔矢亮跟他們一起吃自助喝酒——不對,從進藤這傢伙剛考上院生嚷嚷著自己在塔矢亮眼裏獨一無二的時候開始,就一直很莫名其妙了。他以前不明白這小子有什麼好關注的,後來才發覺進藤光這個人真的很可怕。
「你說,」和谷對著瓶子喝了一大口,「進藤這傢伙剛來棋院的時候,下成那副破爛德性,還有臉皮說塔矢亮把自己當對手,大家都以為他說大話⋯⋯」他又喝了一口,酒瓶險些從手裡滑出去,「結果呢?結果不到一年,這臭小子像突然變了個人一樣⋯⋯」
進步神速的棋力使他躋身圍棋界最受矚目的年輕一代,尤其是這兩年的出色表現,年前NHK杯期間圍棋周刊的專訪標題還將二人稱作「日本棋院的雙子星」,而塔矢亮也確實在公開場合將他稱為自己的對手,眼裡只有進藤光——
「那時候塔矢連這傢伙輸了的棋局,都要抓著他的對手問進藤光下得怎麼樣!不過重點倒也不是下棋的事⋯⋯」
啊,原來說了半天都沒有到重點嗎。越智從棋譜中抬頭,掃視了一眼桌上成排的波子汽水,推了推眼鏡,拿起葡萄味的喝了一口。
「這兩個傢伙啊,」和谷伸長手臂把酒瓶「咚」一聲放在地上,像是發表重要的推理一樣,摸著下巴低著頭說,「應該說是『曖昧』嗎⋯⋯你看,表面上的相處很不坦率,就進藤這種粗神經而言太奇怪了,互相又一副知己的樣子⋯⋯總覺得私下的關係有點不一般呢。」
「——喂,塔矢!」只聽進藤光突然喊道。
和谷遂從自言自語中抬起頭來望過去;伊角和本田停止了敘舊,像剛剛醒過來一樣來回打量著屋裏的四個人;奈瀨也從陽台探頭進來。
「你振作一點!」進藤光從塔矢亮手裡搶過快要見底的酒瓶,抓著他的肩膀。
後者想掙脫他的手,卻被牢牢地按在原地。
「唔,放手⋯⋯我說放手!不要⋯⋯不要你,別管我。」湊近聽見塔矢亮有些咬字不清的聲音,毫無邏輯的拒絕的話語斷斷續續傳入耳中,聽了好一會才識別出他在說什麼。進藤光見狀歎了口氣,「這傢伙應該喝多了,我還是先把人送回去吧。」
在門口互相道別後,越智上了自家的車,和谷正好順路便也跟著一起離開;奈瀨和福井給其餘的人叫了出租車。
進藤光一邊把亮塞進後座,一邊告訴司機塔矢家的地址。
還不到五點,太陽已經開始西沈,天邊在高樓背後泛起紅暈,漸長的影子染上了金色。
他從來沒有見過塔矢亮喝醉的樣子。那張素來冷淡的臉染上日落時的雲霞的顏色,線條似乎都柔和起來,他的眼睛輕輕闔上,顫動的睫毛在眼底隨著車窗外光線的移動而投下變幻的陰影。頭靠在他肩膀上,幾縷長髮垂落在他臉頰旁邊。進藤光將這些髮絲撥開,輕聲說,「稍微側著點,不然脖子會扭到。」他仔細調整肩膀的位置來讓塔矢靠得舒服些,而後者只是發出一點悶悶的聲音,沒有動也沒有睜眼。
原來喝多了之後會這麼聽話啊,他笑著想道。
司機停在塔矢家門口。從院門到玄關這一小段路上,微涼的風讓進藤光幾乎完全清醒了。
手從背後滑到他腰側——塔矢亮好像還沒回神,迷迷糊糊的不知目光聚焦在何處。取出鑰匙開門,帶著他到臥室的也完全沒有反抗。進藤光扶著他坐下,熟練地打開櫃門拿出枕頭和被子在地上擺好。
不知道那一身層層疊疊的和服要怎麼脱,於是進藤光只好小心地將人直接放在床舖上。起身關上門窗,打開地暖,又不忘去廚房燒上一壺熱水準備泡蜂蜜來給人醒酒。做好這一切後回到房間,他在塔矢身旁坐下,將自己的西服外套連同馬甲一起脫下來放在地上,鬆了鬆領帶,解開了襯衫領口的三顆扣子。早上拍的照片放在外套內側,他將它取出來又看了看,順手收進了襯衫的口袋裡。須臾間,耳邊傳來眼前人平緩的呼吸聲。可能是躺在熟悉的被褥上,塔矢已經睡著了。聯想起這一日發生的種種,他微微出神。
「還真是個混蛋啊我。」看著那人的睡顏——潮紅的臉頰,長髮在枕頭上鋪散開,胸口隨著呼吸起伏,進藤光喃喃道,「明明已經對你⋯⋯好多次想要說卻沒有說出來,過去這麼久了,還是什麼也沒有⋯⋯」他歎了口氣,「原本一大早就想要告訴你的,但看到你被別人圍著,突然就覺得很⋯⋯沒想到他們先來了,也一直沒找到機會,該怎麼辦,為什麼總是⋯⋯」
他埋頭將手指插進額前的頭髮裡握緊。
然後突然感到手腕被握住,他嚇了一跳,本能地想要躲開。
「進藤?」
塔矢亮半坐著,被子被掀開一半搭在小腿上。他臉很紅,頭髮有些凌亂,聲音還是嘶啞的,好在神色與適才相比清醒了許多,大概是酒勁過了。
剛才半夢半醒之間聽到一點這個人的自言自語,卻聽不懂在說什麼,好像是很痛苦的事情。怎麼會呢⋯⋯一起吃飯的時候記得還是很開心的樣子⋯⋯
「塔矢⋯⋯」進藤光抬起頭看著他,嘴唇動了動,卻沒有說出什麼,最終只是笑了笑,「那個⋯⋯你在居酒屋喝醉了,我剛把你送回來。抱歉啊,今天本來是想跟你⋯⋯」,他突然收起笑容,神色複雜,表情在臉上劇烈變化著,頓了好幾秒之後才像是終於下定決心:「塔矢,今天原本有一件事想要你幫忙,也只有你能為我做。」說著,側身從西裝口袋裡拿出了一個像釘書機一樣的東西。
「這是⋯⋯」
「幫我打耳洞好嗎?」
「欸?」驚訝得連頭痛都減輕了——剛才聽進藤光語氣沈重,欲言又止,說得像是關係到一生的大事一樣,居然是打耳洞——應該是成年的紀念嗎?這種不同於傳統的舉動果然很像他。只是,為什麼這種事情說是只有他能做?通常不是會去美容院找專業人士⋯⋯
「好像還挺簡單的,」像是看出了他的疑惑,進藤把手裡的工具遞給他,「這邊有說明書——」
「等一下,要去拿酒精棉。」真是胡來,他起身走到櫃子旁,一邊打開藥箱一邊想,這種東西居然就這麼放在衣服口袋裡,得好好消毒才行。
回身將整個耳釘槍仔細地用酒精擦過一遍,塔矢亮才跪回進藤光身前,由著他握住自己的手,把事先放入的耳釘針按在左耳耳垂的位置。
「呼——就這裡了,按吧。」
雖然是像釘書機一方便,但針刺破皮肉應該還是會很痛。他猶豫了一下,閉著眼睛按了下去。
沒有聽到任何表示疼痛的聲音,他睜開眼,將工具拿開,看到一枚紫色的圓形耳釘。是和他扇子的流蘇一樣的顏色。
「嘶——網上很多人說不太痛,都是騙人的嘛!」
塔矢亮從藥箱裡拿了消炎藥。「先別動。」說著用棉籤蘸了一點塗在耳洞周圍,又輕吹了幾口氣來幫助散熱。做好之後,他想問進藤光為什麼突然讓自己為他打了這個耳釘,又覺得或許就只是因為成人日而已,問了反而感到多餘;抬眼卻看見對面的人用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小心翼翼地盯著自己,和剛才請他幫忙時一樣,眼睛裡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沈重和痛苦。
又來了⋯⋯
「謝謝你,塔矢——」沈默許久,他最終說,「既然你酒已經醒了,那就好好休息吧,我也該回去了。」長長的金色碎髮遮住了神情,他說著拿起地上的衣服走向門口。
就只有這樣嗎?
剛要邁出房間,進藤光突然聽見身後衣料掀起的聲音,緊接著下一秒就被抓住肩膀轉過來,塔矢亮拽著他鬆開的領帶用力拉向自己,距離近得能感受到彼此灼熱的呼吸,睫毛抖動著,他驚奇地發現那雙清澈的眼睛裡有憤怒的水光在閃爍——
「進藤光——你到底把我當成什麼了!不是說有想要對我說的話嗎,不是都等了一整天嗎⋯⋯那就告訴我啊!」
震驚之餘腦中空白了一瞬——他第一次看到塔矢亮這麼失控。攥著他領帶的手用力到骨節發白,身體在顫抖。須臾,他聽見淚水滴落在地面的聲音,一滴、兩滴,逐漸像斷線的珠鏈,像大雨傾盆。
「說什麼『為什麼總是這樣』,我也很想知道為什麼總是讓我見到你,為什麼一切事情都會回到你身上,為什麼不清楚你在想什麼,又隨時隨地都會想起你——從第一次下棋开始就讓我心神不寧,可到現在我在你身邊還是像個陌生人,不了解你的朋友,不熟悉你喜歡去的地方,沒有吃過你平常吃的東西⋯⋯都這樣了,為什麼還要讓我們的生活產生交集,為什麼不能僅僅做棋盤上的對手,這樣不是會對大家都好嗎!至少你會感到輕鬆點吧,少了一個不合群的人,不用顧忌他的習慣和感受,這樣一來,你的事情不用跟我說也——」他突然停下來,鬆開了手,放回胸口處攢緊了那裡的布料,他的手指已經被眼淚浸透,「只要你開心,我也就⋯⋯滿足了吧⋯⋯就連喜歡上你的事情也是——」
「塔矢?」喜歡⋯⋯他?進藤光睜大了眼睛,手裡還僵硬地拿著西裝外套和馬甲;他想回握住他的手,只覺得這兩件東西無處安放。
靜謐的空氣,箭在弦上的氣氛讓塔矢亮的酒完全醒了。自己剛剛都說了什麼啊。以進藤的個性,會覺得無理取鬧吧,會輕視自己,覺得厭惡,然後從此分道揚鑣——也罷,這樣就能夠徹底地和這個人回到最初棋盤上的關係了。還好是喝醉酒之後說的,否則大概率會被當成瘋子,塔矢亮在心裡苦笑了一下,向後退了幾步,放開自己的衣襟,用手背擋住下半張臉,轉過身走到床鋪旁邊坐下。
「抱歉拖住你,要走的話,就走吧。」察覺到進藤沒有動靜,他輕輕地說。
他聽著自己不均勻的呼吸和酒精遺留下來的躁動的心跳,閉上眼睛,未乾的淚水滴在手心裡。明明通向庭院的門窗都緊閉著,他卻感到冷;這個過度安靜的立方體空間讓他覺得既擁擠又渺小。
「塔矢⋯⋯」進藤將手裡的衣服放在一邊,慢慢地朝他走過來,在他身後很近的地方跪下。「我,其實對你⋯⋯」
——為什麼,在剛才說了那樣的話之後?塔矢亮想轉身看他的表情,又不敢去面對。果然一開始說出那些話的時候就不該抱著任何期待吧,分明一大半都是氣話,好像自己指望從對方那裏得到什麼安慰⋯⋯
「因為我⋯⋯想對你說的話太多了,不僅是對你的感情,其他的事也——!」他換了一個姿勢盤腿坐下,「我不知道你會怎麼想,我害怕會⋯⋯我害怕你會覺得噁心,害怕讓你失望,害怕你會從此躲著我,落到連對局都不能的境地,害怕剛才那些⋯⋯是你藉著酒勁胡亂說的,酒醒之後就會後悔,然後忘掉——」他甚至忘記了換氣,越說聲音越小,「可是⋯⋯我也喜歡你啊,塔矢,一直都⋯⋯可能從最初開始,就喜歡著你了!」
身後的人停頓了很久,像是在等待答覆,又像是放棄了所有的希望。塔矢亮在回頭之前,聽到他說:「對不起。」
他的印象裡,除了在北斗杯以半目輸給高永夏時那次出奇劇烈的情緒波動之外,進藤光再也沒有流過眼淚。棋局的輸贏也好,身邊人的聚散也好,他偶爾流露出憂鬱的神情,卻似乎沒有因為什麼事情哭過。他都快要忘記這個人哭泣的樣子——淚水在這張臉上顯得極不相配,像是被強加上去,要從那雙愛笑的琥珀色眼睛裡逃離一樣,大顆、大顆地滑過臉頰,沿著下頜的線條滴落。他低下頭,明亮的金髮遮住了雙眼,嘴唇保持著微張的口型,肩膀輕輕地顫抖。
「對不起。」他用氣音重複道。
有很多次因為這個人感到生氣、失望、不甘心,有很多次在心裡責怪過他,也說過絕交的話,卻在真正聽到這句道歉的時候感到心酸。
他想阻止眼前人的眼淚,又不知如何開口,只好抬起手撫摸上對方耳後的皮膚,「這裏⋯⋯還痛嗎?」說話時,明明覺得已經整理好情緒,卻還是感到自己溫熱的眼淚順著嘴角流到舌上變得微涼,鹹鹹的。
進藤光看著他。氤氳的水汽讓他睜大的眼睛像剔透而脆弱的玻璃,打濕的睫毛貼在一起,眼角染上晚霞一樣的紅色,淚水自顧自地從臉頰上流過,如同墜落的星河。他慢慢地握住了塔矢亮的手。
「我沒事的。」他扯出一個微笑,「你⋯⋯別哭了。」伸出右手將塔矢臉頰旁邊的碎髮別到耳後,用手指接住那從眼角墜落的淚珠。塔矢垂下眼,睫毛輕觸他的指尖。
「進藤⋯⋯」
「你不原諒我也沒關係,我對你做過那麼多混蛋的事,也不懂該怎麼喜歡一個人,我只是想要你一直在我身邊,想得到你的注意,想從你的眼睛裡看見我,想成為對你來說獨一無二的人,因為這也是你在我心裡的位置——」他後知後覺地要將手收回去,卻被塔矢輕輕抓住手腕。
「笨蛋。」塔矢低下頭。
「⋯⋯欸?」
「你是笨蛋嗎,進藤。」視線重新相對。「我不是都⋯⋯不是說了喜歡你嗎。」
進藤光抱住他的時候,像是對待一件精緻的花器。他身上留著淡淡的清酒的味道,頭髮扎得他臉頰有些癢,身體熱得像爐中的火。進藤將臉埋在他肩窩,嗅到長髮下散發出的溫暖體香,呼吸灑在那一片光滑柔軟的皮膚上,細膩得不像是真實的觸感。環在塔矢背後的手逐漸滑到腰間——他還是這麼瘦,進藤光想——指尖隱約摸到凸起的脊骨,腰側有一點軟肉;他感到懷中的人微微顫了一下。
鬆開手的時候,塔矢偏過頭,幾縷碎髮滑落到眼前,紅暈像秋天的楓葉在水面的倒影,從雙頰流向耳根和頸側,他無意識地輕咬著下唇內側,眼神游移在遠處的地面。
於是他小心地撫摸塔矢的臉,讓那雙眼睛看著自己。
他感覺到進藤手心上的繭,也許是打球或者騎車留下的,會比棋繭硬一些。他清晰地看到對方琥珀色虹膜上細小的山川一樣的紋路,漆黑的瞳孔逐漸放大,其中只有自己的倒影。金髮與青絲交錯在一起,額頭幾乎相貼,彼此的吐息近在咫尺。
「真的⋯⋯可以嗎,塔矢?」他聽見進藤問。
「嗯——」自己大概永遠都拿這個人沒辦法了吧。
続く。
End Notes
這裏寫到的築地市場現在已經沒了:(((((((( 商家和貨物都於2018年遷址到江東區豐洲;東京都政府本打算將原地址用作停車場供2020奧運會期間使用,然後因為眾所週知的原因也沒有用上。
因為我國內的家樓下有個早市也沒了,而且是全城最後一個,所以寫的時候更有一種難受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