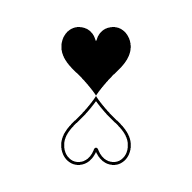初雪(はつゆき)
Notes
(20歲)2007年1月1日
整整四年過去了,他才逐漸明晰自己一直以來對塔矢亮的感情。
四年間發生了很多事。他們頻繁地在賽場相遇,在棋會所相約,大部分時間裡依然只有圍棋將他們的生活連在一起,似乎沒有什麼改變,然直到某一刻開始,進藤光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離開他了。一名棋士與強勁的對手對弈時固然會感到興奮,但每當坐在塔矢面前,他心底還有一種幾乎噴湧而出的情緒,像是有實體一樣讓他的胸腔發痛——因為他是自己的第一個對手才尤顯特別嗎?儘管那時真正執棋的是佐為,塔矢亮所敬畏和追逐的也是佐為,但他眼裡倒映出的卻是自己。北島先生有好幾次大罵過進藤光下棋時只知道瞪著棋盤、屏蔽周遭的一切,「小亮老師可是一直關注著你的反應啊,臭小子!」——該說是他精神太過集中還是心太大呢。他那時才發覺,確實,每個人下棋時都有獨特的小習慣,比如越智完成長考之後的一手時總會推一下眼鏡,座間王座遇到棘手的棋路便會咬扇子,森下老師則會用食指和中指夾著棋子反覆摩挲。而塔矢,雖然進藤光不曾抬眼,仍能留意到他在下完每一手後鎖定在自己身上的目光,那種真摯而帶有攻擊性的、塔矢亮對弈期間限定的眼神——讓他感到戰慄、興奮、喜悅,進而想要他只用這樣的眼神看著自己,永遠。
八年前,他不曾想過他們會走到今天。他一度認為自己與佐為的相遇是陰差陽錯,與塔矢亮的相識也是由於佐為的一廂情願,而這些看似的巧合讓他开始追逐他们的背影,走上围棋的道路——如果現在的自己都全然由這些巧合造就,那麼這還能稱之為巧合嗎,還是應該稱為「命中註定」?這奇妙的緣果可能於那時就在心中生根發芽,又歷經幾年的瘋長變得越發不可控制——如今他甚至能從各種場合中一眼認出塔矢亮,哪怕只是一個很遠的背影,一點他身上的氣味,他頭髮的顏色和光澤,經常穿的那些衣服的一角;而他僅僅是每一次出現就會讓他開心,讓他離不開眼,又不敢明目張膽地去看。他試圖看起來自然地用各種方式得到和他相處的機會,即使只是一起走一小段路,一句話都不說,他也會在之後獨自回憶很久,想著他走路的動作,微不可察的小習慣,在自己身邊的溫度,呼吸的聲音。他盡力地向塔矢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一起參賽的時候很早就入場為了讓他看見自己認真備戰的狀態,約好的見面一定要等塔矢到地方之後才騎著單車停在他面前,在見到塔矢之前還提前猜測他會穿什麼以找出一身顏色相配的衣服,甚至每次下棋時(自以為)帥氣的落子動作都是洗手間裡對著鏡子不斷地練習的結果;塔矢當然從來不會表現出在意的樣子,但進藤光依然執著地要得到他的欣賞,不服輸地想要讓他對自己有像自己對他一樣的感情。
已經不滿足於做他「一生的對手」,這讓自己都感到莫名的恐懼。
從四年前開始,他每個元日都去明治神宫;藤崎明喜歡那裡的氣氛,空閒的話會陪他去。他們並不是每次都碰巧能夠遇到塔矢家,而進藤光一邊覺得希望落空,一邊卻覺得慶幸——他畢竟不知道他對於塔矢亮來說是什麼。
所以這是所謂的「喜歡」嗎?
他聽過棋院裡的院生們午休時談論自己喜歡的人,也看到過小說和電影裡對於「喜歡」的描述,但他看不到他們的心,他想將這些擁有「喜歡」的心拿來和自己的比對,他想知道塔矢亮對於自己為什麼如此重要,他需要明白自己隱藏著的到底是什麼。
于是他照例去了明治神宫;今年藤崎明沒有來,她與她的家人在一起。
他仍然是在大鳥居前看到塔矢亮;他穿著與四年前相似的羽織,顏色深了一些,背影逐漸與他父親重合。塔矢老師在見面時從未提起過佐為,進藤光也逐漸意識到他其實是一個很溫和的人,只是不常表露出情緒,儘管引退之後的生活似乎使他放鬆了一些。但每次面對他的時候,進藤光總有一種悲傷的感覺——佐為已經離開,並且可能再也不會回來了,現今他唯一存在過的痕跡,就是自己的棋——他下意識用拇指撫摸著手中的扇子。
塔矢亮發覺他的眼神突然變了,手也握緊了他一直帶著的五骨蝙蝠扇。又在想什麼了吧。自從開始跟他下棋以來,進藤光偶爾露出有心事的樣子,但像他這樣開朗直率的人,會是什麼事呢?
塔矢明子還是一樣熱情。她相當自然地邀請進藤光和他們一家人一起去參拜,順便會見塔矢老師的棋友們;塔矢亮看著他,陽光在他的眼睛裡閃爍。他們來得早,參道並不擁擠;看著進藤光和母親一路上有說有笑,塔矢亮想起幾年前進藤和長輩們講話時努力注意自己的用語、連話都不會說的樣子,轉過頭去觀察路邊的古樹以使自己不至於笑出來。
這四年間,他們逐漸地從僅僅是棋盤上的對手變成可以坐在長椅上聊天、可以一起去散步的,或許能夠定義為「朋友」的關係,儘管他仍然明確地感受到進藤與他相處的方式和與和谷、社他們相處時很不一樣。他們其實經常發生一些算不上爭吵的口角,相互指摘、諷刺、挑釁,然後又像無事發生一樣回到圍棋上來。他不願意在進藤光面前露出缺點或者脆弱的一面,他知道這很幼稚,但他莫名地不想被他關心,因為不知該如何面對。
有一次他們在棋會所下棋到忘記吃午飯,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接近黃昏。「好餓啊——」進藤光一邊將棋子收進棋盒一邊抱怨,「去外食嗎,塔矢?」
他確實也餓了,想了想,家裡父母都不在,今天也沒什麼心情下廚,於是他點了點頭。
進藤光像是清楚要去哪的樣子;他想問,又不願意被看出來對這周圍的餐館根本不熟悉,於是直到他們在一家快餐門口站定,店面的紅色霓虹燈牌上標著巨大的黃色「N」。
「漢堡可以嗎?」進藤光回頭問道。
「漢堡⋯⋯」
進藤挑起一邊眉毛看著他,「喂,你知道漢堡的吧?」
「當然知道!」他大聲說,「你以為什麼啊!」
「真假啊⋯⋯」進藤皺了皺眉,「那你吃過的吧?」
沒有。「那是當然的吧!」他更大聲地回答,「怎麼會有人沒吃過漢堡!」
進藤插著兜懷疑地打量了他幾眼,「你說的哦。」然後轉身推開了店門。
事實上,他很快就被揭穿了。在他悄悄問「這裡是不是可以吃到那種叫『薯條』的東西的時候,進藤以一種介於「你是認真的嗎」和「我就知道」之間的眼神盯著他。
「你還要吃什麼?」
他不想承認,燈箱上菜單裡的食物他幾乎都不認識。「啊⋯⋯我想要那個有玩具的。」
「有玩具的?!」
「嗯⋯⋯對。」
「啊,那個,不好意思,之前的這些都不要了,麻煩換成兩個開心快樂套餐!——你要什麼玩具啊?」
按照燈箱上說明的意思,應該是有兩組玩具可以選吧。有一組是一些顏色鮮豔、穿著奇特的玩偶,看起來非常有趣,但旁邊寫了很多個名字,他不確定那些叫什麼;進藤光一定對這些東西很熟悉,他不想顯得自己什麼都不知道。另一組是一些普通的小掛件或者小擺設一樣的東西,每個都有字母代號。「就要A吧。」
「玩具麻煩要——」看清A是什麼之後,進藤光瞪大了眼睛看著他,「A嗎?碎花圖案那個嗎?!」
「啊,嗯⋯⋯怎麼了嗎?」
「真拿你沒辦法。」進藤光歎了口氣,「我的玩具也給你,再選一個吧。」
他其實很好奇那些玩偶都是什麼樣的,嘴上卻還是說:「那就C好了。」
不出意外地收到了第二個質疑的眼神。
「你要喝什麼?」
「啊⋯⋯」平時除了白水,喝的最多的就是茶或茶飲料,剛才聽到進藤光說「可樂」,但他聽說那種東西對身體不好。
進藤光瞥了一眼身後排得長長的隊伍。「你快一點啦!」
「啊,進藤,要不你幫我選吧。」每個人第一次來這裡點餐的時候都會耽誤這麼久的嗎?
在進藤向店員道歉了兩三次,翻了幾個白眼,又像教書先生一樣給他講了一遍食物要自己在櫃臺取、並且要自己拿到自己選的座位上、吃完也要自己倒掉垃圾之後,歎了一口氣,把一個托盤塞給他,自己端著另一個走向靠窗的四人桌。
——停下,塔矢亮,停下。還是不要繼續回憶吃漢堡的過程比較好。那次甚至是進藤光請的客。
回到家後,他將那兩個玩具擺在書架上,是一個彩色手繪碎花圖案的梅花形壓克力吊飾和一枚印有簡筆花鳥畫的圓形別章;這是進藤光第一次送給他東西。作為棋士,哪怕是最欣賞的對手也不怎麼會互相贈送東西的。所以說,自己在進藤的生活裡是有一些在對手之上的重要性的嗎?欣喜之餘,心中有些悵然——經過了那頓飯,進藤大概再不會願意和他一起去餐館了;如果自己從一開始就說沒有吃過漢堡,一定會被笑話很久,不過也不至於這麼麻煩進藤了吧。
然而幾天之後,他又被邀請去道玄坂的一間拉麵店,而進藤沒有再問他有沒有吃過拉麵。
「來得早的話,連手水舍都不排隊了啊。」明子的話打斷了他的思緒。
他站在泉水前低頭看著自己的手。他有些慶幸留了長髮,眼角餘光被遮擋住給了他莫名的安全感。進藤光洗過杓柄,將杓放回原處,轉過頭時正好看到塔矢亮直起身,袖子從手臂上滑落。他的臉隱藏在長髮後面,剛從嘴邊離開的手指上的泉水在稀疏的陽光下閃爍,自指尖流入掌心;一滴水珠從他的下頜落到池中。
拝殿前依然是人頭攢動。他們跟著隊伍一點一點往前挪,明子挽著丈夫的手臂,不時轉頭去看兩個年輕人是否在旁邊。塔矢亮看著父母的背影,這樣有一步沒一步地前進方式讓人很累,但他從小到大也算是習慣了,而進藤光則還是每次都會抱怨一句,好像說出來就不會累了一樣。人真的很多,他們的肩膀幾乎要碰到一起——他很少這麼認真、這麼近地看著進藤;一直以來大部分時間都在關注他的棋的變化,這時才突然發覺,身旁的人已經比他高了一些,金髮在他眼角像樹葉間的陽光一閃一閃,他稍微偏頭就能看到那線條清晰的下頜和緊閉的嘴唇,就像每次集中精神下棋時一樣。這樣的進藤真的很⋯⋯帥氣,塔矢亮突然想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隱約意識到自己對進藤的感情不同於通常所說的「朋友」,又不知道有哪裏不同;進藤是除了父母之外他最想親近的人,在進藤身邊的時候可以很放鬆,可以讓他看到更接近真實的自己的一面,就算被嘲笑或發生爭吵也都沒有多少惡意,而且和進藤一起度過的閒暇時光似乎讓他明白了人們常說的「生活的樂趣」。他也知道進藤有很多其他可以一起玩的人,而且似乎下意識地把自己和他們區分開——倒不是說他有多介意,只是這不免讓他對進藤的陪伴的期待和留戀顯得任性而自私,如此時常會陷入自我厭惡⋯⋯
想到這,突然發現進藤不知為何竟也在看著他。
「開心點嘛!」他在他耳邊小聲說,咧開嘴笑起來,呼出的白汽在眼前散開,「一路上都板著臉,這是二十歲的新年的第一天欸!」
真的像太陽一樣,這樣的笑容。「嗯,」塔矢亮望著他的眼睛,「一會兒去抽籤吧。」
參拜結束的時候,蘆原恰好發來消息說他們一行人已經參拜完,正在御苑休息。「那我們兩個先過去了,」明子拉著塔矢行洋對亮和進藤光笑了笑,「每次都讓他們等,真過意不去。」
目送塔矢夫婦離開之後,進藤光突然拉起亮的手腕,敏捷地從人群中間穿過去。
「幹什麼——」
他們在寫著「御神籤」大字的攤位前面停下來。
「啊——還是排了這麼多人。」進藤光插著腰歎氣道。
手腕上被進藤握過的地方熱熱的,像是他還沒有鬆開一樣。塔矢亮悄悄低頭看了一眼,進藤剛才用了一點力氣,那裡留下了一道淺淺的白印。而進藤剛剛還在抱怨要排隊,現在又恢復了開心的表情,雙手插在衣兜裏,看著巫女給前面的人分發號碼,目光跟著他們到籤箱前面。
「第一次在明治神宫抽籤欸⋯⋯」終於排到他們的時候,進藤小聲說道。
巫女解釋了大御心的含義以及如何抽取之後,他們從各自號碼對應的抽屜裡取出了自己的籤。
「塔矢,上面都是古文,這寫的是什麼意思?」進藤光湊過來,把自己的籤給他看,順便看了看他手裡的。
「先不要站在這裡看,會擋住後面的人。」說著走到一旁的空地上。
「我說,」進藤光像看著天書一樣盯著手中的紙,也不看路就跟著他走過來,「剛才還有外國人在排隊,他們要怎麼知道寫了什麼啊?」
「這裡的御神籤有英文的版本,是專門給不講日語的人準備的。」
「欸?英文不是更難了嘛——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進藤光站在他斜後方,身體幾乎貼著他的肩膀,呼吸將他耳側的頭髮吹起來一點。塔矢亮看著伸到他面前的詩籤;進藤抽到的是明治天皇的第九首。
他頓了一下,提醒道:「背面有註解。」
「哎呀,你告訴我就好了嘛——難道說你也看不懂?」
「不要在神前大聲說話。」塔矢亮往旁邊躲開了一點,進藤的嗓門讓他鼓膜發痛——而且真的太近了,他感到自己的臉和耳朵在變熱,這好奇怪——
「哎,知道啦。」進藤光不耐煩地把頭从他的肩膀上移開,「所以你到底懂不懂啊?」
「嗯?啊,這寫的是:『得遇良機,不應趨於人後,該進則進。』大概是說時機到了的話,該前進就要前進,不能總是跟在別人後面。」塔矢亮悄悄瞥了一眼旁邊的人,只見他眉頭微皺,異常安靜地聽著,「你看看背面。」
進藤光聽話地將紙翻過來。
「這前半段也是古文欸,這四個是漢字的俗語嗎——這裡是『社會自遙遠祖先時代,由人們的合作而造就了今天的文明』⋯⋯」他唸道,「『有責任要敢當』⋯⋯」他將手指抵在下巴上,「很模糊的意思啊。」
「是為了能夠適合更多的人吧。」
「你的是什麼?」進藤光又靠過來。
「還是先快去御苑吧,大家一定都等很久了。」
即使是初詣的日子,御苑還是顯得相當僻靜。一半的樹木只剩下枝幹,修剪過的灌木像一群棕紅色的刺蝟,草坪覆蓋著金黃的枯草,菖蒲田還是一片空蕩蕩的泥土;遊客大多參拜完就離開了,有閒暇的本地人才會來這邊。
進藤光跟在塔矢亮身後沿著半圓形柵欄隔出的步道慢慢走著。
初次來神宫參拜的時候曾路過這裡,那天藤崎明和他們一起,走著走著突然說:「聽說這條路是天皇為了能讓皇太后多散步而修建的,真是很浪漫啊。」
「是啊。」塔矢亮微笑道,「天皇還為皇太后栽種了菖蒲田,現在看不到什麼,但五月下雨的時候會非常美。」
「好期待能夠來看一看。說起來,菖蒲好像是有『像從神秘的人那裡收到的神秘的信一樣一生都會加以珍惜愛護』的意思?」
「唔,我也聽過類似的說法,好像是出典自《拾遺愚草》。相比常見的『愉快的消息』、『相信你』和『溫柔的心』之類的花語,藤崎小姐所說的更加詩意呢。」
「真的很讓人嚮往啊,這樣的愛。」
御苑裡面人煙稀少,樹木阻隔了外面的聲音。五月的菖蒲花⋯⋯真希望能夠和塔矢一起看一次,進藤光當時在旁邊聽著他們的對話,突然想。他忍不住看了塔矢亮一眼。他還是很認真地走路,視線朝著前方,整齊的髮絲隨著腳步輕輕搖晃。
除了當時他的身形會稚氣些、頭髮會短些之外,完全和現在一模一樣。時間像是在塔矢亮身上定格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優雅、專注、克制,連走路都像在下一局棋。而進藤光還是沒有和他來看梅雨季節的菖蒲花。
「一生都會加以珍惜愛護⋯⋯」他回想著藤崎明說的話。
「怎麼了?」塔矢亮聽到他唸了一句什麼,慢下腳步回頭。
「嗯?啊,沒什麼。」
「不要總是說『沒什麼』啊!」塔矢突然抬高了聲音,然後又抱歉地低下頭,說道:「我是說,如果心裏有什麼事情的話,可以講出來?雖然——」
「哎呀,不要擔心啦,自言自語而已。」說出來才會更奇怪吧。
他們一路來到了釣魚台,才看到塔矢老師等人邊望著湖面邊閒聊。
「來了啊,塔矢碁聖。」緒方十段先注意到他們,嘴角翹起來,金絲眼鏡的反射的白光遮住了他的眼睛。
突然改變的稱呼讓亮感到有些錯愕;心道緒方老師還是不改愛捉弄人的個性,尤其是這樣的社交場合。
「早上好,抱歉讓各位久等了。」
剛剛結束的碁聖戰五番勝負,鏖戰之後終於贏下了自己職業生涯的第一個頭銜——但早春的名人戰卻在循環賽的選手權決勝局敗於緒方,還是留下了些許遺憾;挑戰賽的結果則是緒方十段擊敗了時任森下名人,在三十六歲時取得了三冠王的成績。
「可是亮君最想要的果然還是名人吧——我等著你哦。以及追在亮身後的某人,」緒方的鏡片反光閃到了進藤的眼睛,「也要加油了。」
真假,這都能扯到自己?進藤光聞言瞪大了眼睛,驚訝之餘還起了一陣雞皮疙瘩。緒方老師也太愛調侃人了,隨著自己升上高段不可避免地跟他在各種場合相遇,又每每聽他說一些好像意有所指的話,总感到不明就里只是臊得慌。尤其這幾個月來更是變本加厲,莫不是因為關鍵的第五年連任頭銜失敗,到手的名譽碁聖飛了而在遷怒?可那明明是輸給塔矢,又不是輸給他⋯⋯哇,真叫人怕了這個老狐狸。
「進藤的話,」塔矢亮突然急切地說,不悅地皺著眉,眼裡滿是認真,「他以自己的節奏努力著,在沒看過他的每一局棋之前,不要輕視他。」
進藤光的世界隨著周遭的空氣在這一瞬間安靜下來,時間彷彿停住;塔矢的話在他腦子裡無數遍地放大。這個人總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表現出對自己的袒護,和圍棋有關的或是無關的,不知道他是否有發現——他努力向別人解釋他對自己的認可的樣子讓他心裏那種湧動的感情像是被點燃的煙火,他說出的這些話讓他覺得自己有了無限的動力和信心去追逐一切想要達到的目標——甚至那個被稱之為「永遠」的答案。
可棋院貴公子偶爾不同尋常的發言,會只是出於對勁敵的佔有慾嗎?也許是他單方面自作多情在這裡熱血了半天也說不定。
不過,去年失之交臂的本因坊頭銜挑戰權,今年一定——
回程路上,塔矢明子提議讓進藤光來家裡坐坐,正好元日晚間大家都會來拜訪。以往受邀去塔矢家都是以下棋為由;這次進藤光當然很樂意地答應了,暗喜之餘又有些緊張。
塔矢亮和父母先坐車回去了,他自己便騎著單車在附近兜兜轉轉,順路在超市買了一大袋蜜柑作為伴手禮,到達的時候已經過了中午。
塔矢家院門左右各擺著一棵古樸的門松。
明子走出來迎接;進藤光問過好,將手中的蜜柑遞給她。「進藤君真是太客氣了。」她笑著接過來,又說道:「小亮正好喜歡蜜柑,他一定會很開心的。」
塔矢亮喜歡蜜柑嗎?他一下想起自己四年前寫在繪馬上的願望。那天和塔矢走在參道上的時候,他一直在想自己除了圍棋之外根本不了解他;知道塔矢腸胃不好,但就連吃飯這種小事情,他都看不出這個人的喜惡,塔矢總是會出於禮節把所有端給他的東西都吃完,不管喜不喜歡都說好吃,眉頭都不會皺一下,而進藤光也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他不想吃就可以不吃——於是那時拿著塔矢給他的筆,沒想太多就寫下「想知道那個人喜歡吃什麼」。
哎呀,所以等了這麼久才實現願望,一定是因為當時既沒有寫清楚想要了解的對象,又沒有寫上自己的名字吧!要找個時間去還願才行。
明子將蜜柑在炬燵上整齊地擺起來。「小亮從小最喜歡酸酸甜甜的東西了,」她微笑著說,「每到過年的時候都能吃好多蜜柑,像蘋果糖、腌梅之類的也很喜歡。後來我和丈夫經常出遠門,小亮也不怎麼和同齡人玩,吃的東西好像就沒怎麼變過。不過這孩子一直很讓人省心,有什麼事也不會說⋯⋯在遇到進藤君之後,我啊,越來越覺得進藤君其實是個很體貼的人;小亮他也是,一提到進藤君話就變多了。平時有這樣的朋友在小亮身邊,我這個做母親的真是很放心,還要感謝進藤君一直以來的照顧呀。」
「哪裏,明子阿姨客氣了,」進藤光也笑起來,「能夠認識塔矢——啊,是說亮君——是我的幸運才對。」
「進藤,你來了。」塔矢亮從房間走出來,心想是時候阻止母親繼續說出像是「感謝進藤一直以來的照顧」這種奇怪的話了——而且他哪有照顧自己!然而看到桌上光帶來的蜜柑時,還是有一瞬間露出像小孩子一樣的驚喜的表情。
「吶,你們玩吧,我去准备晚餐了。」明子輕快地走向廚房。
「咕——」進藤光剛想說些什麼,肚子先發話了——剛剛只顧著閒逛,連午飯都忘了吃,早上雖吃了不少,可好像都被走路和蹬車消耗完了。「呀,」他捂著肚子笑了,「不好意思。」
塔矢亮無奈地搖了搖頭,「離預定的晚飯時間還有很久。」說著跪在被爐前拿起一個蜜柑開始剝。
果實兩邊翠綠的葉子被輕輕摘下,指甲在果皮上劃開一道小口,一滴清澈的汁從被手指壓下掰開的地方滲出來。
「啊,下雪了!」視線聚焦在眼前人的指尖,進藤光偶然透過障子的玻璃窺見依然晴朗的天空中有一些細碎的白色正輕盈地飄落,在庭院的樹梢上留下一點印跡。
聞言,亮不禁轉過頭,午後的陽光在他的全身上籠罩了一層溫暖的金色的紗。
光看著晃了晃神。記得第一次和佐為一起看雪,就是看完塔矢和座間老師的新初段聯賽之後吧。那天在觀戰室裡,窗外是夜幕下飄落的寒冷初雪,而塔矢的棋穿透模糊的屏幕在他心裡烙下炙熱的印記。佐為看著對局,又望向那些雪花,忽然說:「一千年過去了,很多東西都變了,然而有些事物還是不會改變,比如雪景,又比如棋盤上的激戰⋯⋯」那天,他們一直在觀戰室留到棋院熄燈。
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向佐為說著塔矢是值得追趕的目標,說自己能夠進步這麼多還是因為塔矢——這一天,他的一局棋像不滅的星火,燎燒了他心中的原野——佐為並沒有說什麼,但現在回想起來,這番話一定讓他很傷心吧,一心只想著下自己的棋、一心只想著追逐塔矢的自己,不曾顧及身邊這個「幽靈」的感受;在那場雪中,在那之後,他說過要從尹老師、從亮、從所有人的腦海中抹去「佐為」的存在,他說要讓大家記住的是自己,記住「進藤光」這個名字。他天真地以為佐為來了就不會走,會為了能夠下棋而永遠留在他身邊,自己則會在棋盤上青史留名——想著,他像個瘋子一樣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大笑,和空氣打雪仗,雪從佐為身體中間穿過去,落在看不見的遠處的地上。他瞥見佐為想要像自己一樣用手捧起車蓋上的雪,而雪卻紋絲不動。
「小光的頭髮上都是雪,都變白了。」佐為躲過他打出的雪球,一如往常微笑著說,一邊伸出手用袖子當作傘遮在他頭頂,想擋住飄落的雪花。
他擁有這一切,佐為擁有的卻只是圍棋,和唯一能證明他的存在的自己。
五年七個月又二十七天——時間模糊了他們之間最後的嫌隙,似乎如果那些事情不曾發生,進藤光就能夠留住他。千年——時間亦是刻在這個靈魂身上最鮮明的印記,他們的相遇與他漫長的等待相比近乎只存在了一瞬,而他在自己的生命中留下的記憶似也只是如曇花般的一瞬,並在花開花謝之後,成為了無法忘卻的永恆。而佐為去哪了?是成佛轉世,還是作為冤魂被抹滅了存在?或者說,他只是與之前一樣,回到空白的時間牢籠裡獨自下棋嗎?也許棋盤上已經看不見的血跡是他與現世聯通的唯一媒介,被封印在內的他只是靜候著下一個少年的出現,來實現自己執念的神之一手?
在那些近乎瘋魔的、連棋子都拿不起來的日子過去之後,彷彿是出於一種自救,他肖想過佐為會不會對下一個與他相遇的孩子講自己的故事,就像他給自己講虎次郎的故事一樣。那時的佐為——
「他手中還會拿著那把扇子嗎?」
「嗯?」塔矢亮突然抬起頭看著他。
想起那個亦真亦幻的夢境,竟不自知地問出了聲。以前確實答應過要告訴他的吧,其實也一直想告訴他,只是不知道從何講起。
「塔矢,」於是他握緊手中的扇子,身體前傾,望向亮的眼睛,認真地說道,「如果一個人為了遇到你,帶著一把傘在每一個下雪天等待沒有帶傘的人注意到他,等了很久很久;而你被命運選中,接受並習慣了他的庇護和帶給你的晴空,在這樣的安逸下漸漸越走越快、越走越遠⋯⋯你以為他在身邊做你的傘很快樂,并擅自地沈浸在這種快樂裡,直到他離去前都沒能回頭多看一眼他的等待最初的含義——」他深吸一口氣,「這算什麼?」
塔矢亮眨了眨眼,他抬起手指輕輕抵著下頜,就像他每次思考棋路一樣。
「我想,每個人都可以做帶傘的人,也可以是沒有帶傘的人;一個人或許冥冥之中就是為了另一個人而生。等待本身就是一種信任,相信希望見到的人會來,相信心心念念的事情⋯⋯會如願發生。但人又是自私的,尤其是有著想要追逐的夢想的人——」他輕輕搖了搖頭。這個坐在他身旁安靜聽著的人,便是像命中注定一樣突然出現在他眼前,而同為棋士,他也很清楚他們各自的執著;這幾年來日日夜夜,二人共有著所有的努力、辛酸,人如其名,他就像照進生活的一束光,讓自己第一次覺得彷彿可以與一個人分享一切,而不曾啟齒的唯有面對他時自己不知如何自處的那份感情——「沒有兩個人能夠打著一把傘走过所有的雪天,可是即使後來為了各自的信念而分道揚鑣,也會為曾經做過對方的晴天而感恩這次相遇。」他說著說著不自覺地笑了起來,像是意識到什麼,又突然停了一下,轉而看著他道:「如果那個人是你,進藤,他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一定是真的快樂吧。」
整齊的額髮隨著姿勢的改變而向後散開,髮絲擦過因放鬆的表情而微瞇的眼角,是那樣溫柔的眼神,令人心醉——方才的話語像是匯聚了整個春天的明亮和溫暖,融化了他心裏最沈重的秘密,讓他情不自禁想要去相信。佐為⋯⋯在我身邊的時候真的感到快樂,在因為我的自私而消失後,他還會為現在的我感到高興嗎⋯⋯塔矢他,在我身邊的時候,也是快樂的嗎?
窗外的小雪仍在下著,雪花被陽光染上金色,落在樹梢和房頂上化成閃爍的水滴,順著葉尖和屋簷像八音盒的樂聲一樣落下。
「謝謝你,塔矢。」許久後輕輕說道,他頷首,任瀏海遮住了眼睛。
「嗯?這沒什麼。」
亮禮貌地笑了笑,低下頭拿起剛才剝了一半的蜜柑。明豔的橙黃色的薄皮像花瓣一樣翻捲,露出內裏的鮮嫩柔軟的瓤瓣,將它們分開的時候,交錯纏繞的纖細的橘絡從彼此之間斷裂,半透明的脆弱囊衣包裹著晶瑩的果肉。
「啊——」進藤光突然俯身用嘴接過了塔矢亮手裡剛掰下的一瓣蜜柑,不等咽下就囫圇道:「好吃。」
「嗯,欸?」雖然說顧及這個人連午飯都沒有吃,確實有想要給他剝蜜柑的意思,但剝完了拿著整個果肉部分才覺得不妥:幫別人剝好蜜柑後是該整個遞過去嗎?還是一瓣一瓣掰開?——總不能像喂小孩子一樣一口一口地給他吧;可是一邊想著剛才的那些話,手上不知不覺已經掰下了第一瓣。⋯⋯不論如何,母親還在附近,居然就直接用嘴從別人手裡吃東西,簡直是胡鬧——
居然⋯⋯用嘴⋯⋯從我手裡⋯⋯
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的塔矢亮感到整個臉頰都在發燙。「好吃你就自己吃。」他扔下一句話就起身想要逃離這種奇怪的氣氛,沒看到身後的肇事者也滿臉通紅地用手擋住自己的嘴。
又做了不該做的事啊,進藤光在腦子裡自責道。可是剛才的塔矢太⋯⋯太耀眼了,用那種真摯的、期待的、又極為認真的眼神望著他,讓他前所未有地想要靠近這個人,像人類最原始的想要追逐光源的本能。於是一瞬間,有如他身體裡一扇盡力鎖住的門不敵外面的風暴而驟然打開了一樣,並未思索就做出了那種「越界」的舉動——果然自己暗地裡的「喜歡」已经到了極限嗎?
心下泛起苦澀的漣漪,面上卻不顯,進藤光努力控制著表情,換上了平時耍賴的笑容說道,「呀,抱歉啦。」
等門外的腳步漸行漸遠,冷靜下來後反思剛才的事。其實一直以來,他隱約察覺到塔矢可能也是有一點喜歡他的。進藤光也猜不透隱藏在他對自己不尋常的在意和遷就背後的是怎樣的想法,只知道這個人說出的一些話和做出的一些事常常並不是他內心真實的意思,而不熟悉他的人很難看清。至於他適才看著自己的眼神和親近舉動後泛紅的耳根⋯⋯這種情況下生理的反應是不會騙人的,再聯想到他平日裡對自己時而嚴厲、時而溫柔的曖昧不明的態度⋯⋯只是可能連本人都沒有注意到就是了。
嘆了口氣,明明已經無法忍耐,又擔心過分的行為會適得其反——「青春熱血的荷爾蒙迸發進而渴求愛情滋潤的慾念」與「暗戀對象是個鮮有社交不善肢體接觸的圍棋笨蛋」這一事實之間的衝突驟然成為了他進藤光生命中的主要矛盾。像是感受到情路坎坷難行的程度,彷彿身體都被抽乾了力氣,他不禁憤慨地向後一倒,就這麼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和室的地板上。
「⋯⋯但果然還是你剝的好吃嘛。」放棄了思考,他望著門外未停的初雪喃喃道。
晚餐非常豐盛,明子的手藝還是一如既往地無可挑剔。圍棋界很多前輩和塔矢門下的弟子們都來了。進藤光和許多人都認識,在這樣的場合聚在一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些有的沒的,也經常提到他近期棋賽的表現,儘管很開心,但斟酌著用語試圖回應長輩的每一句問話還是讓他感到有些費力。
大家都吃到盡興,開始專心喝酒聊天的時候,進藤光注意到塔矢老師和亮不知何時已經離席了。
「呀,進藤——」倉田厚一身酒味地湊過來,「你不是一直想要我的簽名嘛——」
「啊,沒,不是——」
「這樣大好的日子,就讓我倉田厚滿足你這個願望吧!」說著從西裝口袋裡摸出一支馬克筆就要朝他臉上寫。
「倉、倉田先生!」他一邊擋住伸過來的手臂一邊小心著不碰到桌上的杯盤,餘光瞥見緒方十段在鏡片後面的嘲弄眼神,「謝謝您的好意,您喝太多了,還是不——」
「進藤。稍微跟我來一下。」
「塔矢——?」進藤光聞聲回過頭,藉機趕緊起身,朝向人群說了聲「失禮」,懷著終於得救了的心情走出客廳。
亮帶著他一直走到靠近棋室門口的地方;他毛衣的袖子捲起,手有些紅,大概是剛剛在幫忙清洗碗盤。看著眼前人劫後餘生忽蒙大赦般的誇張表情,他笑道:「喝醉的倉田先生還是很難纏的,緒方先生和芹澤老師也不遑多讓吧,以後還是避著一點好。以及,父親請你去下一盤,如果方便的話。」
「啊?嗯,當然。」
夜幕隔絕在障子之外,客廳的談笑聲也微不可聞,暖色的燈光靜靜地繚繞在棋盤上,於棋子邊緣投下模糊的影子。多少局棋過後,進藤光依然無法忘記在棋會所初次看到塔矢行洋執子時的震撼——第一次用正確的手勢下出屬於自己的棋步時,全身過電一樣的感覺。
「——多謝指教。」
隨著大手合的廢除在年末剛昇上六段,官子之後進藤光預料之中地輸了三目半。但看盤上廝殺之間可圈可點的佈局、双方在中盤進退得宜的應手,這仍是一局好棋。
「小亮對我說過,」塔矢行洋收攏盤上的棋子,突然說,「你的棋裡有另一個人的影子。」
進藤光的手停了一下,棋子落在木盒裡的清脆聲音在他耳邊迴響。太久沒有聽到塔矢老師,聽到任何人提起過那「另一個人」了。
「那個附身在你的棋裡的人,他一直追求的也是高於勝負、甚至高於圍棋本身的東西。」他將棋盒蓋好,倒了一杯茶,沈聲道,「今天與你的對局讓我看到了諸多可能,這便是他選中你的原因吧;相信小亮也會這麼認為。能夠看到遙遠的過去與可期的未來相互融合,是一種緣份。」
「塔矢老師這樣說,我——」進藤光抿了抿唇,鞠躬道,「那個人和我都非常感激。」
耳邊傳來暖爐燒著碳火的噼啪聲。許是雪還在下,從漆黑的夜空落進路燈的光束裡,讓車頂、道路和人們的頭髮蒙上一層白色。
而這幅景象,待明天太陽升起,就會消失不見了吧。
続く。
End Notes
在2007年的元日光亮20歲的時候,這邊設定是他倆其實一樣高,亮在參拜的時候會感覺光比自己高完全是因為光哥早上準備出門搞偶遇時突然想到今天亮一定會穿和服,由於不甘心輸給木屐的高度連忙急中生智給自己墊了內增高!(*文以外預設成堆x)